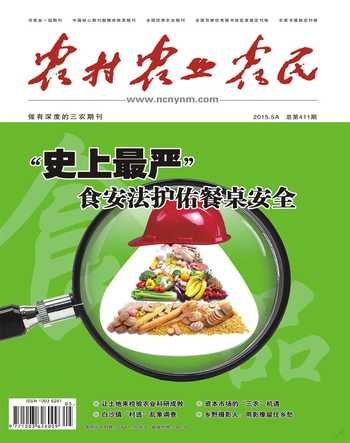鄉野攝影人:用影像留住鄉愁
許亞薇



老一代照相師傅身背外拍機、背景布,騎著自行車在鄉間穿行的形象,早已成為20世紀下半葉鄉村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一座座村莊隱沒于城市,轉瞬間變身高樓大廈的營盤,人們甚至來不及記錄下鄉村變遷的過程。
自2011年開始,攝影家王勇用三年的時間走訪了豫魯蘇皖四省交界處23個縣的24位照相師傅,完成了《村里來了照相的》一書。王勇試圖透過照相師傅的回憶,喚醒人們的鄉村記憶。
書里試圖留住的,正是現實里不可逆轉遠去的。一筆筆繪制的布景、神態炯炯的仿真動物成為博物館里的玩意,曾經風光的照相師傅,只剩下一小部分仍在堅持,大多身在底層,只求生計。
“生意被搶走了”
一位照相師傅,三兩個修片徒弟,一臺便攜照相機,幾十張背景畫布,為數不多的服裝道具,再加上一輛自行車,這是20世紀下半葉鄉村照相館的標準配置。
在王勇走訪的24位照相師傅中,有一位來自山東省菏澤市成武縣。如今,62歲的宋愛民和老伴依舊在艱難地維持著成武縣文亭照相館。算上在國營照相館的經歷,宋愛民已經拍了39年照片。
20世紀80年代末,宋愛民離開了由原成武縣商業局管理的國營東方紅照相館。出于對照相這一活計的熱愛,宋愛民沒有選擇去“賺錢更多”的銀行工作。1989年,在夫妻兩人的張羅下,成武縣文亭照相館靜悄悄地開張了。后來,宋愛民也收過幾個徒弟,“他們學會了,就自己干了,都走了”。
39年來,年年下鄉拍照,宋愛民的腳步遍布成武縣的絕大多數鄉鎮和村莊。著名紀實攝影家晉永權曾說,這些生活在縣城鄉鎮里的照相師傅,當年身背外拍機、背景布,騎著自行車在鄉間穿行的形象,早已成為20世紀下半葉鄉村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
與大多數鄉村照相師傅一樣,宋愛民印象深刻的故事都發生在“走村”照相的過程中。隨著時間的推移,當無數“走村”故事連綴在一起,活脫脫就是變遷中的鄉村。
宋愛民“走村”,拍得最多的是全家福、畢業合影以及各式各樣的證件照。過去照相師傅少,一個縣也沒有幾個,每到春節都是宋愛民最忙的時候。算下來,宋愛民已經有39年沒有在家過春節了,“連中午在家吃一頓團圓飯都沒有過”。
過去一到春節,穿新衣戴新帽,見了親戚朋友就想一起拍個照片留念,現在,人人都可以用手機和相機拍照。原本稀罕的照相師傅不再是神秘的存在。
王勇走訪的23個縣的24位照相師傅,有的已經退休,有的已經轉行,有的還在維持著有些陳舊落后的鄉村照相館。在王勇看來,這些照相師傅的境遇大抵相同,原本風光無限,如今生存在社會底層,只求維持生計。
在今天,除了給老年人拍證件照,到鄉下“走村”給學生拍照片,設備陳舊、技術落后的鄉村照相館日子越來越不好過。
鄉村照相館隱沒和衰落,鄉村照相師傅消失和沉寂,漸漸淡出人們的視野,記憶卻和師傅們拍下的照片一起留存下來。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副院長楊小彥曾說,正是照相館塑造了鄉愁,然后保存了鄉愁,讓鄉愁成為現代中國的一個情感記憶。
消失的手繪布景和仿真動物
照相業不會衰落,照相館也不會衰敗。但是,隨著照相業的發展,那些只屬于過去的道具和技術卻永遠留在了過去。與其他行業一樣,對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徹底打擊了手工生產,機器代替手工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事實。
20世紀80年代,在手藝人李新昌的帶動下,菏澤曹縣安才樓成為全國著名的鄉村照相館布景生產地。與現在講究實景拍攝或者立體布景不同,20世紀下半葉,無論城市還是農村,照相館里用的都是手繪布景。那時候,安才樓的布景發往全國各地的農村,不說近處的安徽、江蘇等省,最遠的銷往了新疆。
如今一走進曹縣安才樓,首先聽到的是吱吱的機器響聲,那是來自日本的噴繪機器發出的聲音。現在,安才樓的生意依舊沒有離開影樓和照相館,原本制作手繪布景的人家跟隨時代的腳步,開始制作噴繪布景和實景,在北京、上海、廣州、鄭州、濟南等城市,安才樓的年輕人開起了照相館布景店。現在,村子里留下的大都是看機器的老一輩,年輕人大多走出村莊聯系業務。
安才樓的手繪布景所剩無幾,王勇花了不少錢在安才樓購買了150余幅大小不一的手繪布景,這些都是機器大生產迅速降臨、手繪布景來不及銷售所剩下的。亭臺、花卉、公園、大廈,這些布景有的色彩艷麗,保存完好,依舊可以使用,但是更多的已經被時光侵蝕。
現在再來看這些鄉村手繪布景,也依舊保留著深深的時代印記。2014年9月的山西平遙國際攝影大展上,王勇沒有展出一張照片,而是選了5幅保存完好的布景掛上墻。“當時現場人山人海,搶著在布景前拍照。”連王勇都沒想到,自己的“裝置展”可以吸引這么多人的注意。中年人和老年人一下子回憶起生活過的鄉村,站在布景前擺出20世紀80年代流行的姿勢;而年輕人懷著好奇心,試圖復制和回歸那個已經逝去的時代。
畫國畫出身的李新昌對畫了近20年的布景有很深的感情,他用文藝的語言表達了自己對手繪布景的留戀:她像風吹遍中華大地,又像雨滋潤這片沃土,像花點綴這個時代,像葉映襯精彩的瞬間。她有無窮的魅力,隨著攝影師的鏡頭將你載入夢幻般境界,使之夢想天成,美夢成真。
與手繪布景一起消失的,還有照相館里常用的仿真動物。在追求真實場景的今天,照相館里的仿真動物已經難覓蹤影。流動照相館的范杰是少數還在使用仿真動物的照相師傅,范杰說,逛廟會的年輕人更愿意跟孔雀和老虎合影,而獅子、熊貓之類的鮮有人問津。
一筆筆繪制的布景、神態炯炯的仿真動物,這些照相裝置慢慢被時代淘汰了。但是,就是這些照相裝置,曾經給人們帶來無窮的心理慰藉,站在這些裝置前拍照留念的瞬間,或心情澎湃,或平和喜樂,留下的照片都已經成為不能忘卻的記憶。
一個時代遠去了
除了回不去的青春,照片所保存的,還有一個個名不見經傳的家庭歷史和家族故事。從探究鄉村照相師傅和照相館的故事開始,王勇有了收集老照片的愛好,那些照片里的人王勇都不認識,但翻看著那些從老鄉手中甚至從舊貨市場淘到的老照片,王勇感嘆道:“照片其實就是逝去的鄉村記憶。”
在老照相師傅的眼里,無論城市化走到哪一步,變化最大的都是村子里的人。
在王勇訪談的24位鄉村照相師傅中,菏澤甄城的范杰最年輕。2001年中專畢業后,范杰沒有從事所學的造酒,而是經營起廟會流動照相館。范杰雖然年紀不大,卻生活在改革開放后發展最快的年代,對整個社會的變化體會頗深。在范杰看來,現在的農村人,無論是在生活上、穿衣打扮上、思想上都有很大的變化。“人的服裝、表情都變了。總的來說生活條件好了。”
這些改變大多是去城市里打工帶來的。在王勇所探訪的豫魯蘇皖四省交界處,村子里少見年輕人的身影,除了年輕人到外地打工,有的一家三代人都離開家鄉外出謀生,不少村莊因此變成“空心村”,沒了人氣。
但是,逢年過節,村子里又會熱鬧起來,年輕人帶著城里人的“習氣”回到家鄉。每年過年時候的河南永城,在芒碭山古廟會上,從城里回來的年輕人聚在一起嬉笑打鬧。與從前“白天機器人,晚上木頭人”的老一輩打工者不同,新一代農民工的生活豐富多彩,他們希望永遠離開家鄉,留在城里。
菏澤單縣的白新春子承父業維持著白家照相館,白家照相館也成了當地唯一從解放前一直開到現在的照相鋪子。回頭看那些留下了的老照片,仿佛置身時光機器。
“那時候,回力鞋、老板褲多時髦啊!”王勇感嘆道。在20世紀90年代初白家照相館給年輕人拍的一張合影里,三個留著三七分“富城頭”的青年腳蹬回力鞋,身穿老板褲,每個人的一只腳同步向一側伸出,照片最右邊的青年上身穿一件牛仔服,右手叉腰,露出了腰間的軍裝褲腰帶。在三個追求時髦和新潮的青年背后,不是高樓大廈,而是綠油油的麥田。今天,照片里三個青年的真實身份已無從考證,但這張略微泛黃的照片呈現的,是一個時代的痕跡。
正如上海美術館原學術部主任、藍空間藝術館館長肖小蘭所說,無論時代如何變遷,中國照相館留下的影像仍舊是今天了解中國人傳統的珍貴視覺文本。照相館鏡頭前人們的一招一式,顯示傳統對他們的影響不亞于時代和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