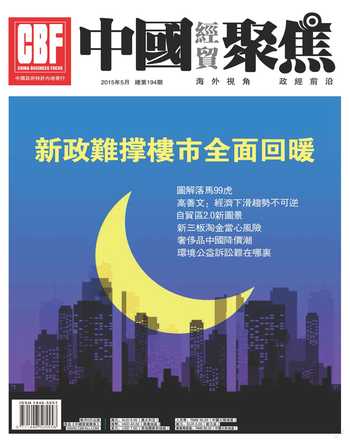愛沙尼亞:小國的崛起
虞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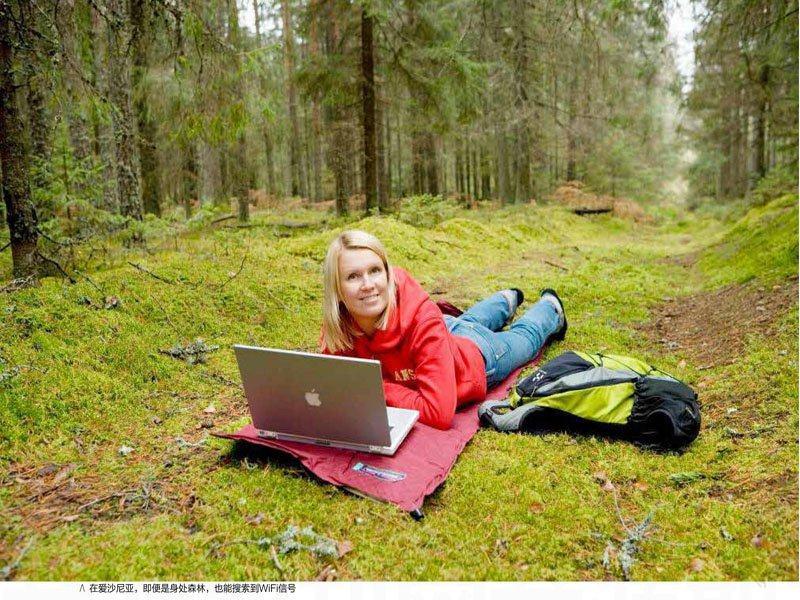
即使無法成為歐洲的“硅谷”,愛沙尼亞也是歐洲的特拉華The RiSe of Estonia
“愛沙尼亞已經從‘圈外踏進了國際舞臺。”
對于這個波羅的海的三國中面積最小的國家,《經濟學人》資深編輯、歐洲政策研究中心(Centrefor European Policy Analysis)高級研究員愛德華·盧卡斯( Edward Lucas)數年前便如此評價,而如今這一點已經得到了世界的認可。
這位英國籍記者曾多次走訪愛沙尼亞,十分鐘情于這個人口僅130萬的波羅的海小國。“我從小鐘愛研究歐洲歷代地圖,尤其是對那些消失在歷史長河的國家興亡原因,這一切對我而言就如同一個個謎底。之后,我拜瀆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 Czesfaw Mitosz)著作《被禁锏的頭腦》( The Captive Mind)之后,更是對愛沙尼亞等波羅的海小國的命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盧卡斯在一次采訪中說。
1989年,身處布拉格的盧卡斯在電車上偶遇了兩位來白愛沙尼亞的T程系學生,并與他們就這個國家的歷史和反暴政運動進行了長達數小時的交談,這加深了他進一步了解這個波羅的海小國的決心。幾年后,盧卡斯如愿地踏足于這個還處于蘇聯統治下的領地,而當時恰逢愛沙尼亞獨立運動。因緣際會,他陸續結識了一些反蘇活動家,其中包括后來成為愛沙尼亞外交部長的徹維密·威里斯特(TrivimiVelliste)。白那以后,盧卡斯便經常往返于英國和愛沙尼亞,多番為這個剛剛獨立的小國獲得國際認可而報道。
盧卡斯與愛沙尼亞的不解之緣,讓他見證了這個國家從一個剛剛脫離蘇聯“禁銅”的小國逐步發展成為一個電子科技強國。而在五個月前,盧卡斯與愛沙尼亞的緣分更進了一步,這位英國記者成為了該同首位外國籍“電子公民”( e-resident)。
2014年12月1日,在首都塔林,愛沙尼亞總統托馬斯.亨德里克.伊爾維斯( Toomas Hendrik Ilves)親白向盧卡斯頒發首張無國界電子居民身份證。
無界電子國度
盧卡斯此前便對愛沙尼亞“數字型”社會抱有濃厚的興趣,對電子身份證帶來的便利性有著極大的認可。在愛沙尼亞,精妙的全國電子身份證系統讓公民可以在網上進行電子銀行交易、購物、簽訂合同、甚至可以用來投票。
“我一直非常榮幸能獲得這個電子身份證,這比獲得獎章什么的重要得多,兇為它既象征著我與愛沙尼亞的長期聯系,同時也是我每天都能用到的東西。”盧卡斯稱。
美國《赫芬頓郵報》(The Huffington Post)報道,盧卡斯獲得的電子身份證包括用于驗證身份的微芯片,以及用來生成數字簽名的瀆卡器。憑借這兩樣東西,無論他身處何處,都能享受愛沙尼亞公民享有的所有電子服務,比如簽署文件、注冊公司、在銀行開賬戶,甚至是在愛沙尼亞的藥店訂購處方藥——當然,這些都是在線進行的。
除此以外,擁有電子身份證就等于擁有了在全歐盟,或任何其他使用電子認證的國家通用的數字簽名。持有者可以用電子身份證在德國買火車票,或發送經過認證、包含加密信息的電子郵件給其他持卡者。
不過,值得提到的一點,獲得電子身份證也不代表人愛沙尼亞籍,無法取得合法居住權。相反,這是第一種由國家發行的超國家數字認證,簡而言之,這是第一次由國家承認人們的網絡身份。
盧卡斯指出,“不能確認身份是互聯網最大的弱點之一,我不知道給我發郵件的是否對方本人……相應的,我也很難證明白己的身份。擁有國家認證的電子身份證意味著,我可以在網上確認白己和他人的身份,還可以在郵件上簽名。”
由于網絡身份得到認可,持有者還可以用認證過的電子簽名執行商業法律文書的活動。美國著名雜志《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便曾撰文報道了一位居住在迪拜,獲得愛沙尼亞電子公民身份的印度人就是通過這種電子簽名在西班牙做生意。
而作為世界上第一個打“無國界電子公民”這張牌的國家,愛沙尼亞冉次備受世界矚目。該同經濟部副秘書長塔維·科特卡( TaaviKotka)稱,政府向全球開放申請愛沙尼亞“電子公民”的政策,推出這種無國界的電子身份證,主要是為了打響國際知名度,吸引數以百萬計的電子公民,和數以萬計的公司投資。每一位申請這種身份證的人只需要支付50歐元左右的費用,就可以和愛沙尼亞境內的公民一樣,擁有生物識別的教據信息。
據媒體報道,在盧卡斯之后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已經有來白55個國家的250多人中請獲得了愛沙尼亞電子公民許可。其中133人來白芬蘭,64人來白俄羅斯,其余的來自拉脫維亞、英國、美國、新西蘭、日本、斯里蘭卡、委內瑞拉和墨西哥。
這個“電子公民”項目負責人卡什帕·柯瑞斯( KasparKorjus)指出,“某種程度上說,電子公民項目雖然起初是政府發起的,但現在,從中請過程到所有的服務都不完全是政府性的了。”柯瑞斯預計到2020年,將有約1000萬人與盧卡斯一樣成為愛沙尼亞電子公民,遠遠超過目前其國內總人口。
從這張薄薄的一張卡上可以看出,這個過去曾先后被瑞典、德國、俄羅斯殖民,在政治上籍籍無名的小國,在短短二十年內已翻身成為了科技信息大國,并如盧卡斯所說的,站在了世界矚目的舞臺上。英國BBC就以“網絡革命先鋒”形容這個國家。而這一切歸功于它不被一隅之地所束,能夠放眼全球( Think Clobally),通過精密的電子網絡系統將這個小國與世界聯系起來。
科技興國
在蘇聯高壓統治半世紀后,1991年,愛沙尼亞宣布獨立,當時的國家一窮二白,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擁有電話線,與外界唯一的通訊工具是藏在外交部長花園里的一部芬蘭手機。當時的內閣由首相馬爾特·拉爾( Mart Laar)領導,成員平均年齡才35歲,而正是在這群年輕人的領導下,愛沙尼亞轉身跳人白由市場經濟。在兩年內以固定匯率化解獨立初年的通脹危機,以單一稅制吸引國際投資人,為經濟政策定調、并推動企業私有化及自由貿易健全貨幣體制。
也許正是由于是小國,轉型才能進行的如此順利。愛沙尼亞前任總統倫納特·梅里( LennartMeri)曾說,大國改革就像大郵輪轉彎,慢又難;小國改革卻像獨木舟轉彎,快又簡單;錯了就調頭,失敗風險低。
同時,蘇聯經濟的前車之鑒也給了新生的愛沙尼亞政府警戒。 “正是經歷了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的錯誤,磨練了一代企業家,同時也讓愛沙尼亞人不得不學習很多事情,同時嘗試新的事務。”面部情緒識別公司Realeyes共同創始人兼CEO米克爾·杰特曼( MihkeIJaatma)說。
在當時產業不發達,資源匱乏的情況,愛沙尼亞只能集中力量發展某些產業,這讓很早選擇了將重心放在最新科技——互聯網上,借此發揮后期優勢。而白南經濟體制的改革讓新創企業可以輕易在短時間內進行登記,推動科技人才進行創業。
同時,愛沙尼亞十分注重教育,從小培養科技人才。由政府資助的虎跳基金會( Tiger LeapFoundation)助力頗大,在不到四年的時間內使愛沙尼亞成為歐洲第一個在每所學校里都實現DSL(數字用戶線路)永久連接的國家。2012年,虎躍基金會又推行程式老虎(ProgeTiiger)這一計劃,將計算機編程引入所有愛沙尼亞入學兒童課程中。通過樂高頭腦風暴機器人Mindstorms及其他學習教材,6歲兒童就開始學習編寫代碼和通過程序開發工具。
在一些國家,計算機編程還只是“學霸”、或是“電腦迷”們的專屬技巧,而在如今愛莎尼亞,這已成為小學生的基本技能。虎躍基金會通過這一課程訓練孩子的邏輯思考、創造力,還有掌握未來世界的溝通語言,讓他們將來可以直接進入編程和軟件開發領域。
而在這個崇尚創新的氛圍中,Skype、Hotmail、以及Kazaa(著名P2P軟件)這些知名網絡服務在愛沙尼亞人手中誕生。尤其是Skype的成功,帶動了科技新創公司的興盛,也為愛沙尼亞創造了一群新的富豪階層,同時也吸引了一批風投眼光投入愛沙尼亞科技領域。
政府也給新創公司大開方便之門,僅需5分鐘,便可通過網絡在該國注冊一家實體公司。行政審批十分簡化,同時政府大力扶持創新“孵化器”,幫助創新者將靈感產業化,其中便包括愛沙尼亞企業協會(Enterpris,e Estonia,成立于2000年,是愛沙尼亞政府給予企業金融資助、政策咨詢、人力培訓的非營利機構),以及門將政府資金投入到有巨大發展潛力的創新項目上的愛沙尼亞發展基金。
愛沙尼亞還專門建立了歐洲創新研究院( EIA),為來白世界各地的“極客”創造一個獨特的創新平臺。政府還建立了塔林科技同區Tehnopol,通過資金扶持的方式幫助創新者建立起他們第一個商業運作模式。在這樣的氛圍中,人才、研究機構和風險企業聚集在一起,引起知識和信息的匯集與交流,成為高技術發展的重要源泉。難怪塔林理工大學副校長阿拉爾·科爾克( Alar Kolk)會稱愛沙尼亞稱世界上最容易將靈感化為現實的地方。
聯合同最新數據顯示,愛沙尼亞的新創業公司數量占全部企業數量的比例達11.67%,全球最高,而相比之下,美國為6.98%,加拿大為6.61%,現在,僅在Tehnopol,便聚集了150家新創科技公司。
盡管愛沙尼亞可能因為其地理因素以及面積太小,與歐洲“硅谷”之稱失之交臂,但是當之無愧是歐洲的特拉華——美國科技企業的發源地。
不知不覺中,愛沙尼亞漸漸走在了創新的前沿。如今,愛沙尼亞已經將上網寫入憲法,成為人民的基本權利,并在全國布網,實現免費無線網絡全覆蓋。即便是身處森林,也能夠暢游網絡。
帶有IC卡的身份證和手機是愛沙尼亞人的兩大信用終端,通過它們人們可以實現白己的全方位電子生活。政府職能也逐步“連網”,通過網站文件系統,內閣會議已變成無紙會議;電子警察、電子政務,網上繳稅、網上選舉等都已經逐步實現。據統計,愛沙尼亞共計向公民提供600項電子服務,向企業提供2400項服務。
不僅如此,政府甚至在籌謀一項“數字連續”( digital continuity)方案,試圖把政府的數字基礎設施備份至云端,這樣即便遭遇外部破壞,也能保持網上職能的正常運作。可以說,小國的大智慧在愛莎尼亞的崛起中體現得淋漓盡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