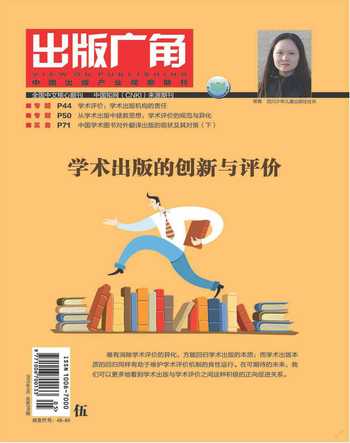數字化傳播下核心期刊評價的實踐困境與現實構建
我們創新現行的定性評價制度,使定性評價能真正起到補充定量評價的作用,更全面彰顯學術期刊質量。
20世紀90年代,隨著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我國學術期刊開始了數字化轉型。目前,大部分學術期刊并未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全數字化出版,但是基本已將紙質期刊刊載的內容進行數字化轉換后,通過大型期刊數據庫進行數字化傳播。數字化傳播改變了人們的閱讀習慣,使期刊網絡數據庫成了讀者獲取文獻資料的首選和主要方式。這種期刊媒介傳播方式和閱讀習慣的轉變促進了文獻的廣泛傳播,也使核心期刊評價體系的指標發生了變化。
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以下簡稱《總覽》)為例,1992年第1版的《總覽》只有被索量、被摘量和被引量三個定量指標,到2011年第6版,定量指標發展為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他引量、被摘率、影響因子、被重要檢索工具收錄、基金論文比和Web下載量等9項。而且隨著大型期刊文獻數據庫建設的不斷完善,核心期刊評價指標的數據基本上實現了由人工統計到完全從數據庫自動獲取。這種指標多樣化和數據來源客觀性的評價方法,理論上是一種較理想的評價手段,目前也被廣泛應用于各系列核心期刊評價中。但是實踐中這種評價方法是否遇到了困境?如果有,又該如何完善?基于此,本文將對數字化傳播下核心期刊(本文研究的“核心期刊評價”的期刊范圍僅限于在我國出版的學術期刊)的評價方法做一透視,這對構建一個科學、合理的核心期刊評價指標體系,以及規范學術評價,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數字化傳播下核心期刊評價的實踐困境
學術期刊是一種內質的精神產品,是通過刊物中的文字、圖片或其組合來表達人們思想、見解和知識的思維成果,其評價是一個相當復雜的系統工程。學術同行本對學術評價最有話語權,但是我國學術期刊數量龐大、學科眾多,如果僅靠學術同行的定性評價,難覓審讀期刊文本的代表性專家;而且受到學術傳統、社會風氣、學術利益、學術體制以及學者學術水準、道德修養等的影響,同行評議的結果往往缺乏科學和公正[1]。而“核心期刊”“來源期刊”等專業評價機構根據各定量評價指標,對相關內容進行測評,這種方法既簡便易行,又能避免定性評價主觀性過強、隨意性過大等問題。但是深入挖掘現行的核心期刊評價模式,發現其存在一些實踐困境。
1.重獎輕罰的指標設計隱沒了學術期刊的形象
期刊形象是指期刊由于辦刊理念、思想內容、審美標準、作者口碑、社會影響以及用稿質量和行業認證等級等在社會上尤其是在作者心目中長期以來所樹立起來的地位和形成的印象[2]。期刊形象既是有形的(如裝幀設計等),又是無形的(如辦刊理念等)。學術期刊是內在質量與外在形式的有機統一,期刊是否按《期刊出版管理規定》出版,如何策劃設置欄目,如何審選論文和編排,如何使各欄目呼應對話等,都體現著編者的理念和智慧,滲透著編者的思想和眼光。但是數字化傳播時代的核心期刊評價缺乏能承載這些功能的指標。比如,期刊的某篇文章違反了出版管理規定,出現重大政治問題,這本將損害期刊的正面形象,但是讀者通過網絡下載該篇文章,無論文章內容是否被引用,都會提高Web下載量指標;如果文中某處出現了政治問題,而其他觀點準確無誤時,并不影響作者對正確內容的引用,當然也會提高被引頻次和影響因子等指標的數值。這種重獎輕罰的指標設計無法對違規的刊物起制裁作用,也隱沒了學術期刊的真實形象。
2.核心期刊的“評價權力”顛倒了作者、期刊與評價機構之間的正常關系
無論是紙質傳播還是數字化傳播,作者永遠是最關鍵的資源。可以說,作者的學識、思想和風格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刊物的價值和質量,沒有作者的文稿,再現代化的出版方式都無法可持續發展。學術期刊是社會學術產品的“物質”載體,是人類傳承學術思想,傳播學術信息,積累學術文化,促進學術創新的重要工具[3]。評價機構用系列評價指標對學術期刊進行的分級和排序,其研究的初衷是為圖書館采購期刊提供指導作用。在這三者關系中,作者是學術成果的源泉,評價機構是服務者,而期刊是連接學術成果和評價機構的中介。
數字化傳播下,評價機構不必閱讀文章的內容,也就是說,不必接觸作者;期刊也僅僅起傳送數據的作用;評價機構只要收到數據后,就可以完全脫離作者和期刊進行學術評價。數字化傳播為核心期刊評價提供了捷徑,同時這種“評價權力”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學者、期刊和評價機構之間的顛倒關系:原本是服務者的評價機構變成了指揮者,對學術最有話語權的作者必須迎合期刊,期刊必須迎合評價機構[1]。于是,應追求內在質量與個性化發展的學術期刊,舍棄了學術服務的根本,一味追求評價指標的數據,甚至不惜為此造假;學者們再也不能遵循學術發展的客觀規律而靜心于學術研究,由此,滋生了學術浮躁情緒,出現了大量學術垃圾。
3.流水線式的量化指標無法全面彰顯學術期刊的學術質量
學術質量是期刊的生命線,學術質量評價自然就成了學術期刊評價的核心。學術質量高的論文往往有較高的學術影響力。真正的學術影響力,只能產生于學術成果的精神生產過程之中,并取決于這個生產過程及其結果是否帶來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從而與這種精神產品的創新性、思想性和規范性成正比[4]。學術評價不是一件簡單的“技術活”,學術成果所體現的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是無法被數學工具所測量的,其蘊含的創新性、思想性及規范性也是難以測量的。特別是社會科學成果評價,其涉及時間(歷史)判斷、性質判斷和價值判斷,這些內容幾乎不可能使用單一的量化標準,而需要時間的積淀和歷史的評價[5]。但是,事實上人們往往更多地從文獻計量學的范疇去解析和定義學術期刊的質量。我國核心期刊的評價指標從問世以來得到了不斷完善與發展,但是縱然這些指標體系設計得再細致與全面,也只是取自期刊及其所發文章的外在形式,很難深入到期刊的學術內容層面進行評價[1]。優秀的期刊必定有鮮明的個性特征和內容創新,在數字化傳播下,那些流水線式的、純技術化的量化指標顯然無法全面彰顯內容“非標準”的學術期刊質量。
二、數字化傳播下核心期刊評價的現實構建
有學者呼喚,學術共同體應該回歸學術評價主體[6]。筆者認為,縱然數字化傳播下學術期刊評價存在諸多缺陷,但是在數字化閱讀已成為普遍甚至唯一的學術論文閱讀方式的今天,如果全然無視出版環境的變化,讓學術評價回歸同行評議,是有失科學的。更何況受到學科專家素質、評價制度和評價環境等的影響,同行評議同樣存在實踐困境。核心期刊評價是一個艱難和漫長的過程,應順應時代的發展,不斷探索一個合乎學術發展規律,真正為學術研究服務的學術期刊評價體系。
1.引入準入測評,重現學術期刊的真實形象
盡管現有的評價體系無法完整反映學術期刊的形象,但是無論什么級別的學術期刊都無法回避期刊數據庫的網絡傳播,否則必將因為影響因子等指標不如同行而影響期刊的可持續發展。基于此,建議引入準入測評制度,這不但能起到獎優罰劣、重現學術期刊形象的作用,同時也節約了核心期刊的評價成本。其具體做法是:以國家憲法、法律、宗教政策、民族政策、《期刊出版管理規定》和辦刊宗旨等為評價標準,按不同的分值,分“合格”“基本合格”“輕微失誤”“一般失誤”“重大失誤”五個等級對期刊進行基本條件測評。文章刊載內容違反政治標準造成重大錯誤;或出現一般政治失誤,出版物已進入市場,產生極壞影響;或刊物違反《期刊出版管理規定》,一號多刊等情節特別嚴重者,列為“重大失誤”,得0分,采取“一票否決”制,取消其參選資格。對其他等級的結果給予不同的分值,構成核心期刊測評總分的一部分。準入測評填補了原有核心期刊評價指標的漏洞,期刊不會因“唯數字”而失去其真實的形象。
2.制約評價機構的“評價權力”,促使學者、期刊與評價機構正常關系的理性回歸
信息技術的發展為核心期刊的“評價權力”提供了技術基礎。從表面上看,是數字化傳播下的期刊評價體制扭曲了學者、期刊與評價機構的正常關系,但我們深入分析,會發現這種顛倒關系的催生土壤其實在于現行科研評價體制。現行科研評價管理往往將科研成果等級化,等級化的標尺就是刊物的級別,特別是能否進入核心期刊。核心期刊直接決定學者的工資待遇、職稱評定、學術聲望和地位等。對期刊而言,核心期刊將制約著來稿數量和質量,進而決定刊物的學術影響力。因此,每一版核心期刊排行榜的發布都會牽動學術界和期刊界每個利益相關者的心。我們不能全盤否認核心期刊在學術評價中的作用,但是,期刊與論文是載體與主體、整體與局部的關系,即使整體代表了較高的學術水平,也不能由此推斷局部的質量高[7]。數字化傳播下,雖然核心期刊評價機構可以脫離作者和期刊進行學術評價,但倘若科研管理部門沒有過度崇拜核心期刊,只將它當輔助和參考作用,就能有效制約核心期刊學術評價權力,學者、期刊與評價機構的正常關系就能得到回歸:評價機構僅僅充當服務者的角色;期刊承擔著對學術思想的傳播工作;學者們遵循學術發展的客觀規律,靜心做好學術研究。
3.構建更合理的定性評價制度,科學評判期刊的學術內容
定量評價與定性評價各有優缺點,故目前核心期刊評價機構大部分采取定量評價與定性評價相結合的方法,試圖準確評價學術期刊的學術質量。理論上看,這種方法應是科學合理的,但是現行的“定性評價”只是評價專家通過網絡審查定量評價產生的核心期刊表中的期刊和排序是否符合客觀實際情況,如不符合,可以對表中期刊和排序進行調整和補充。而且只要具備正高職稱的學者即可申請定性評價專家的身份。也就是說,定性評價專家可以不分學科,不必閱讀到完整的期刊,只是憑著自己對期刊的了解進行主觀判斷,而且定性評價不受任何的監督。理想的定性評價應深入期刊的內容,經過理性的審讀,對期刊的學術質量做出判斷,這種判斷會有比較豐富的表述[1]。
因此,我們創新現行的定性評價制度,使定性評價能真正起到補充定量評價的作用,更全面彰顯學術期刊質量。首先,通過網絡隨機選擇評審專家,評審專家應選擇自己精通學科的期刊,以減少非學術因素對評審的干擾,提高評審結果的準確性;其次,專家進入中國知網數據庫,按“刊名”檢索所要負責評價的期刊(以期刊為單元的傳播,無異于紙質期刊),深入閱讀期刊的內容,撰寫專業的評語和鑒定意見;最后,將專家的信息和定性評價的結果公布于眾,以接受公眾的監督,保證評價的公平公正,加強評價機構和專家的責任意識。
[1]朱劍.量化指標:學術期刊不能承受之輕——評《全國報紙期刊出版質量評估指標體系(試行)》[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1).
[2]恭旭輝.期刊形象價值研究[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3):152.
[3]鄭英隆.學術期刊的社會價值與作用[J].江西社會科學,2005(6):228.
[4]林麗芳.名人論文.影響因子和學術影響力——對學術期刊編風的思考[J]. 福建行政學院學報,2008(4):65.
[5]蔡曙山.我國社會科學評價的若干要素[N].光明日報,2002-08-27.
[6]朱劍.重建學術評價機制的邏輯起點——從“核心期刊” “來源期刊”排行榜談起[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1):10.
[7]林麗芳.論“核心期刊”泛化的負效應及原因[J].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06(12):107.
[8]王素芳.網絡閱讀的發展現狀和前景探析[J].圖書與情報,2004(3):91.
(作者單位:《福建行政學院學報》編輯部。本文系中共福建省委黨校福建行政學院2014年院級一般科研項目,項目號:2014B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