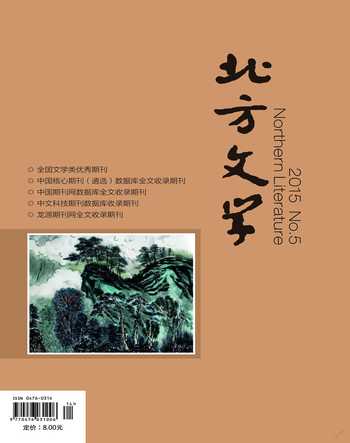欲望與現實的雙重變奏
陳旻
摘 要:本文通過對《長安大道上的騎驢美人》一文的文本細讀,從欲望與現實、存在與虛無的二元對立勾勒現代人被焦慮壓抑的缺失性體驗。并結合巴赫金的狂歡理論,分析作為政治象征的長安大道被顛覆后的戲謔意、諷刺意義。通過這一過程的揭示,反映現代都市生活中人成為物的奴隸與物的人格化所展示的人與物之間的主奴辯證法,并深入反思在物質發達精神萎縮的年代里欲望與現實的雙重變奏。
關鍵詞:《長安大道上的騎驢美人》;物欲;寓言;狂歡
莫言的短篇小說《長安大道上的騎驢美人》講述的故事情節概括起來十分簡單:四月一號這一天,在首都北京長安街附近上班的候七在結束了一天百無聊賴的工作之后準備回家,卻在復興門地鐵站出站的時候目睹了一個奇觀——一個身穿紅裙的絕世美人騎在高大的黑驢上,身旁的是一個執矛仗劍、騎高頭白馬的威武男人。兩人招搖過市,旁若無人,引來長安大道上的民眾圍觀。警察出面維護街道秩序,二人皆對此置若罔聞。正當候七好容易逮到一個機會——周圍再沒有其他人而騎驢美人正在一步之遙時,驢和馬甩下“十幾個糞蛋子”揚長而去,只給候七留下無限的欲望和遐想。
莫言的幾個長篇小說都具有深刻的寓言意義。《豐乳肥臀》是用民間性史詩書寫的戰爭時期的史詩寓言;《檀香刑》是八國聯軍戰爭期間的“民族寓言”;《生死疲勞》是關于農民認祖歸宗的神圣儀式中的家族寓言……本文力圖在文本分析的基礎上展現莫言在現實主義手法的桎梏之外,所運用的大膽、豐富的想象,在這篇小說中所洞悉的社會學、心理學意義上的人、人性。
一、作為現代意義上的寓言小說
根據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中的說法,十八至十九世紀的作家寫作傳統可以分為鏡與燈兩種。“鏡子”作為一種修辭,反映了現實主義作家們按照生活本來的面目描繪生活,融合了較多寫實成分;而燈光作為一種若即若離的手法,在現實的基礎上,摻雜了更多虛構和想象,在勘探人生的精神向度和寓意的復雜性上走得更遠。從模仿到表現,依據艾布拉姆斯的說法,經歷了一個鏡—泉—燈的過程。這也是小說寫作從以摹仿說為基礎的寫真式,到由表現說、諷喻說為基礎的寓言式的過程。
本篇小說很明顯是基于虛構基礎上完成的,這樣的長安大道在現實中永遠不可能發生,故而敘事上具有怪誕或非現實性,符合寓言小說的基本特征。
但是與此同時,這又不單純是一篇想象的狂歡的小說,它把事件發生的背景設置在了北京城,而且是最為繁華的長安大道上,很顯然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在祖國的核心首都,在擺脫了表面真實的寫實主義手法背后,可以窺見作者強烈的現實影射。人們被日常周圍的經驗所圍困,被權力機制所壓抑的無意識狀態都在莫言小說的筆下得以呈現為一系列具有深刻隱喻意義的意象與符號,并且在意象的彌散中重構能指與所指的關系。
在虛構的外表下,隱藏著真實的內容。這則小說表面上看似荒誕不經,而實質上,它是一則關于現代人焦慮與欲望的寓言。在這里,常規的、連續的時間發生了斷裂,長安街也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政治象征的空間。在這里,時間凝固了,長安大道上的人們紛紛陷入駐足翹首,欣賞這道亮麗的風景的狂歡當中。
二、二元對立的辯證法
(一)欲望和現實的沖突
候七與警察之間呈直接的對立關系,這一對矛盾是故事的基本矛盾。如果說候七是欲望世界的邏輯,那么警察則代表了現實世界的法則。警察的出現干擾了夢境的秩序,作為外界力量的強力介入,打破了夢境中原本連續的時間。
拉康指出,“在主體消失的時刻溢落的、即被閹割、被寫入無之后進入能指鏈而形成的來自虛無之物的召喚就是產生欲望的原因。”[1]小說中人們因為平日生活的缺乏激情,只能在波瀾不驚的生活中努力挖掘一線微漠的趣味。在無聊的生活背后,可以觸摸到一份欲望被壓抑的缺失性體驗。開篇面對奚落候七的辦公室小青年,站出來為他說話的女人是一個“穿一條背帶褲、上身特長、雙腿特短”的姑娘,強調她的外貌似乎是與后面騎驢美人的驚艷外表形成一種“美丑對照”的反差。乏味的生活里缺乏美,周圍都是這樣相貌平平的女子,無怪乎見到騎驢美人時眾人那份訝異的驚喜和瘋癲的追逐。
小說中對于候七在騎驢女子出現之前的生活沒有過多的描述,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既沒有情趣,也沒有盼頭可言。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正常時空之外的次元。候七也是個在現實生活中壓抑的人。他感到自己面對美人有非分之想時立刻“對自己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因為“忘了初來北京時……父母諄諄教導候七不要看熱鬧。”在縱情的同時還不忘處處做著減法,可見壓抑之根深蒂固。
本文最后以驢和馬拉出十幾個“糞蛋子”這樣一個嘲諷戲謔的場面作結。“糞蛋子”作為對前面美人所代表的沒好事物的顛覆,可謂具有極強的諷喻和幻滅意義。本文經歷了一個從“現實—欲望—壓抑”最后又回到現實的過程,所以稱之為欲望與現實的雙重變奏。
(二)存在與虛無的一步之遙
小說里騎驢女人雖然無數次逼近現實的界限,但是卻總在微妙的關頭戛然而止。例如眾人翹首企盼她打個噴嚏,因為打了噴嚏說明她是和圍觀群眾一樣的凡人,但她沒有。文中還好幾次描摹了候七與騎驢美人之間僅在一步之遙卻無法企及的事實。美人作為一種欲望的象征始終“猶抱琵琶半遮面”式的活在若即若離的彼岸。小說也多次營造這種理想與現實的平行線無線逼近卻最后分道揚鑣的過程。
即便到了小說末尾,理想和現實也依然沒有達成和解,在歷經千回百轉的追尋后,候七終于等到了一個只剩他和騎驢美人和騎馬男人的機會,本以為咫尺之間就能觸摸到美人的他卻被十幾個糞蛋子狠狠地甩在了身后。夢境與現實始終隔著一層像玻璃紙一樣的介質,若隱若現,卻又始終無法穿破。只能留給候七無限的遐想。
三、長安大道上的狂歡美學
通常意義上而言,長安街曾經是政治運動中群眾游行集會的圣地,目睹了中國近現代革命史的歷程,和民族革命和解放運動的順利完成。長安街上響徹的禮炮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它是政治外事活動的門面和場地,同時它也是多次政治運動和學潮發生的地方。可以說,長安街作為當時成為表達政治愿望和參與政治生活的重要場所,和天安門一道成為首都的政治標志景觀。
根據俄羅斯文藝理論家巴赫金的狂歡理論,民間話語所承載著的思想,與所依附的歡樂形式一起,成為了民間的狂歡節②。長安大道本來是莊嚴的政治象征,在這篇小說里,長安大道卻成為了一切游戲、夢境、荒誕、變形發生的載體警察是權威的象征,是作為欲望的對立面出現的。而騎馬人對于這樣的權威置若罔聞,無疑是一種叫囂式的狂歡,是一種對神圣之物的褻瀆和歪曲,社會被置于一種無序的狀態。
此外,騎驢女人的出現使得原本平靜連續的時間突然被打破,發生了斷裂,發生了陌生化的效果,它將人們引領向常規時間之外的次元。人的潛意識里有自覺或不自覺地把骯臟的、卑鄙的、見不得人的思想遮蔽起來的舉動。在這個斷裂的時空里則不一樣。人們盡情地打量著美人的身姿和五官,賞心悅目,不再需要遮遮掩掩,原本的禮法要求在這里暫時不復存在,現實世界中的卑微感和煎熬感灰飛煙滅。
四、結語
張清華在評價莫言的長篇小說時用的說法是“敘述的極限”,莫言的作品“在敘事上卻稱得上是最富狂歡氣質、最接近“戲劇”的小說”,“他的小說經驗的民族與世界的雙重性,還有他的充滿魔幻色調的敘述、狂歡化的敘事美學……其實都與人類學有著最直接和密切的關系。”③而筆者以為,剝去了高密的厚重色彩和瑰麗宏大的魔幻現實主義外殼,莫言的短篇作品具有穿越時空生生不息的分量。從鄉土、民俗中走出來,他的短篇作品依然不乏對于人性、對于人類普遍生存困境的書寫和探求,依然是關乎靈與肉、情與理等焦灼沖突的辯證寓言。寓言敘事將當代小說從寫真的傳統中解救出來,從宏大歷史敘事中解放出來,停止“主題先行”的大出血。這里,莫言做了一道加法。
注釋:
①[日]福原太平:《拉康:鏡像階段》,王小峰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頁.
②[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六卷),萬海松等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3頁.
③張清華:《敘述的極限——論莫言》,《當代作家評論》2003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