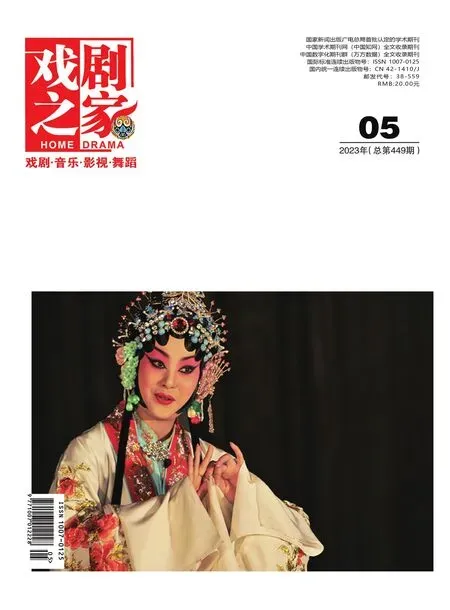京族哈節中儀式舞蹈的研究
——以“進香舞”為例
蒙璐
(廣西外國語學院 廣西 南寧 530222)
京族是我國唯一的海濱少數民族,具有獨特的民族特性,主要居住在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東興市。京族哈節是當地最為隆重的節日,也稱“唱哈節”。哈節的慶祝活動內容很豐富,包含了當地的民間儀式活動、娛樂活動等,是京族人民最重要的節日。
一、“京族哈節”的儀式過程
哈節中的儀式舞蹈是哈節民俗禮儀活動中表演的一種民間儀式舞蹈,也可以說是民間儀式中的身體語言表達,具有獨特的民族特性和文化內涵。關于“京族哈節”有不少民間傳說和故事,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傳說講的是在古代有一位歌仙來到京族三島,以傳歌、授歌為名,動員京族的老百姓起來反抗封建的統治和壓迫。她的歌聲感動和影響了許多百姓,高亢的曲調和輕柔的歌舞受到京族人民的喜愛。后來,京族人民為了紀念她,就建立了“哈亭”,定期在哈亭唱歌、傳歌,并逐漸成為京族的節日習俗。經過近五百年的發展和演變,京族哈節成為京族傳統民族文化的代表。
哈節的祭祀儀式過程分為四個部分。一般在下午,全體京族的鄉親會一起敲鑼打鼓,出發去往海邊迎接白龍鎮海大王,將其接回哈亭,并將家養的豬趕到“哈亭”,繞行三周,留到半夜的時候殺掉。緊接著是第二天的祭神儀式。儀式活動的第三個環節就是唱哈。祭神完畢后,按照年齡高低入席,一般是每4 人、6人或者8 人一席,邊吃、邊聽“哈妹”唱哈,酒席的酒肴大多數由各家自備。唱哈活動要連續進行三天三夜,幾乎是通宵達旦、歌舞不息。最后是送神,整個哈節的節日程序便結束了。在迎神之前還有序幕——大清潔活動。在這一天,全村各家都要派一個人到哈亭參加大掃除,清理雜草、疏通水溝、池塘清淤等,給哈節活動打造干凈整潔的環境。
二、“京族哈節”的儀式舞蹈
京族的哈節舞蹈是在哈節期間進行的民間祭祀舞蹈,也是京族最具有代表性的傳統舞蹈。這類舞蹈通常由女性進行表演,動作細膩別致、柔和圓潤,感情內向含蓄,舞姿甜美端莊,充分體現了京族婦女多勤、溫順的性格和濃郁的民族風格。
(一)儀式舞蹈的組成部分
“京族哈節”的活動由祭祖、鄉飲、社交、娛樂等內容組成。在整個節日活動的四個儀式中,祭神和送神祭祀儀式中都出現了風格鮮明并且占比較大的舞蹈部分,這兩個儀式部分都是通過身體語言來完成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儀式舞蹈在“京族哈節”禮儀活動中的重要性。
哈節最重要的活動就是唱哈。唱哈活動只是唱哈的序幕,從第二天祭神起,唱哈活動正式開始,唱哈分下午和晚上兩段。哈妹們跳著祭祀活動的儀式舞蹈。祭祀儀式活動中出現的舞蹈部分主要包含儀式中的“敬酒舞”“進香舞”“天燈舞”“花棍舞”等,這些與儀式相關的身體動作語言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征。這類儀式舞蹈的創作與表演既具有風格強勁的民族氣質,又具有民族文化傳播價值。
(二)儀式舞蹈與日常生活
儀式舞蹈的形成與發展與京族人民的海洋生活有著密切的聯系。京族人民的日常生活離不開大海,京族人信奉海神。京族人民通過哈節來表達對海神和祖先的感恩和懷念以及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人們借助哈節開展一系列的“求平安、敬神靈、慶豐收、傳文化”活動。
儀式舞蹈是反映京族人民生產生活的舞蹈,內容十分豐富。唱哈詞的主要內容包括民間宗教信仰、京族的歷史傳說、漢族的古典詩詞以及京族人民生活的新面貌等,都是京族人民喜聞樂見的內容,深受京族同胞的歡迎。
(三)儀式舞蹈風格特征形成的歷史原因
京族哈節中的儀式舞蹈是從京族人民的日常生活演變過來的,在民族發展變遷的歷史長河中,不斷消化和吸收各類文化元素,形成了適合本民族的獨特風格。儀式舞蹈中體現出的風格特征不僅是京族人民對自身舞蹈文化的保留和傳承,更是京族歷史文化的藝術體現。
儀式舞蹈風格特征與京族人民的生活環境有關。在過去,京族人民生活在偏僻的海島上,常年在大海上出沒,以捕魚為最主要的生存方式。因此,每到京族男人出海捕魚時,人們都會通過一些傳統民間方式來祈求家人能夠平安歸來。
儀式舞蹈風格特征與京族人民的民族性格有關。這種特定的生活環境和生產方式造成了京族婦女多情、溫順、內秀的性格,這也在舞蹈風格上有所表現。
儀式舞蹈風格特征與京族人民特定的祭祀內容有關。京族人民對海神的敬畏是京族舞蹈風格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進香舞就是在哈亭的中殿進行祭祀時表演,在嚴肅而神圣的氛圍下,嬌柔的“哈妹”所表現出的肢體動作謹慎而虔誠。
三、進香舞在京族哈節中的儀式性
舞蹈作為一種文化現象,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發展,是人們在工作生活中逐漸形成的身體形態和對社會觀念的反映。京族哈節的儀式舞蹈是與京族特有的儀式性緊密相連的,而進香舞在其中就具有重要的表現力和儀式性。
(一)儀式的嚴格性與嚴肅性
在哈節的民間儀式活動上,儀式過程按照嚴格的次序進行,主要角色有禮官、引唱、司鼓、主祭、慢拜司等,儀式由禮官主持。首先是給神上香,禮官要先進行唱儀。然后,引唱隨即和上,司鼓便敲上一陣“哈鼓”。這時,兩名主祭便會捧著香爐,在慢拜司的引領下,行至內殿的神位前,虔誠地給神上香。在行進過程中,“哈妹”(又稱桃姑)就要隨著鼓點,在哈亭的中殿跳進香舞。
進香舞又稱“納例”,由“跳樂”和“進香”兩部分組成,是集歌舞為一體的舞蹈形式,進行舞蹈表演的哈妹邊唱邊舞。“跳樂”的儀式是為了供神仙娛樂,“進香”的儀式是為了敬奉神仙。進香舞是在哈節第一天儀式的最后進行,“桃姑”們會為諸神跳起進香舞。
(二)儀式的民族性與獨特性
鼓是哈節儀式舞蹈的重要組成部分,各儀式舞蹈均有鼓樂伴奏,這些伴奏具有民族特色。舞蹈在熱烈歡快的鼓聲中開始,哈妹唱著《進香歌》,左手持香,右手做“輪指轉花”的動作,將香進行上下左右祭拜,伴隨著民族歌曲,營造出一種如臨仙境的感覺。進香舞動作輕柔、調度流暢,舞蹈動作在煙霧繚繞中顯得如夢似幻,由此表達取悅、感謝及贊美神靈之意,充分表達了京族人民特有的民族氣質與態度。
四、進香舞的藝術觀賞性
進香舞除了作為儀式舞蹈的功能之外,還具有藝術觀賞性。現存民族地區儀式舞蹈具有詩、歌、舞、樂、儀多位一體的形態,其內容與生產、宗教、習俗相互交叉,相較于其他舞蹈,其身體文化內涵傳承具有更強的穩定性和持續性。“京族哈節”祭祀禮儀活動中出現的儀式舞蹈,充分還原和表達了京族人民的生活狀態。儀式舞蹈中的身體動作具有歷史性、民族性和社會性的美學內涵。將儀式舞蹈置于本土文化傳統中,不僅可以深入研究民族特征,還可以研究儀式舞蹈形態和當下儀式舞蹈的變遷。
(一)進香舞獨特的藝術體態
在人類社會還沒有出現語言的時候,舞蹈肢體表達已經成為主要的交流方式。在少數民族的交流中,民間舞蹈是民族性最深刻的反映。進香舞有獨特的動作規律,可以用三個關鍵詞概況:“圓”“柔”“收”。動作的全程都呈現出圓的形狀,展現出舞者的柔美,通過收放自如的舞蹈語言動作進行。進香舞的圓形動作表現出京族女性生產勞動的痕跡。
(二)進香舞柔和的動作語言
舞蹈語言作為人類的交流工具,以“姿勢”作為人類情感和意識的基本符號形式進行傳播,以舞蹈人體構成審美和文化傳播的符號。進香舞的動作連綿起伏,讓觀者有一種酥麻的感覺,體現出柔和含蓄的舞蹈風格,主要動作有“輪指”“轉腕”“擊掌”“手花”“搖臂”。進香舞的基本步法有“三角步”“躬身碎步”等,體現出了女性的柔美。這種柔美來自京族女性的日常生活。京族男人在打漁歸來之后,京族女人通常會在岸邊幫助拉網,拉網的動作就融入了進香舞的舞蹈動作中。
(三)進香舞優美的律動特征
舞蹈動作的律動是舞蹈的風采和神韻能夠延續的重要原因,也最能夠體現出民族的個性與特征。在舞蹈的律動中表現出的民族特性和風格,將民族的地域性和歷史性包含在內。
在進香舞表演中,舞者左手焚香,右手翻轉手指,用優美的律動表達女性的柔美,以此向神靈送去祈禱和祝福。哈族儀式舞蹈是哈族祭祀活動的組成部分,表達的是在莊嚴、肅穆的環境下對神靈的尊重。因此,進香舞的律動就非常講究姿態的優美和動作幅度的大小。
五、將進香舞從儀式舞蹈轉化為舞臺藝術的可行性
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民族風情,每個民族都有各自代表性的民族舞蹈。新的時代背景對民族舞蹈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進香舞作為京族哈節儀式舞蹈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轉化為舞臺藝術的充分條件。怎樣更好地轉化是值得我們研究的重要內容。
(一)堅守進香舞的民族個性與獨立性
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長久歷史發展進程中形成的一種穩定的精神基礎、文化心理與民族意識,反映了特定民族的生存與發展軌跡,展現著獨特的文化價值取向,是其賴以生存發展的根基。因此,我們可以看出進香舞正是憑借著京族人民開放包容的生活姿態與融會貫通的生活智慧,才堅守著民族個性與獨立性。由此生成的民族文化自信是維護民族文化特色的天然保障。進香舞要堅守住民族的個性,在多元文化的沖擊下始終堅持著自己的民族特色,將民族最好的東西保留下來并發展下去。
(二)堅持創造性發展、創新性轉型
民族民間舞蹈雖然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但是在各種時代因素的沖擊下,年輕一代缺乏對其學習的興趣。民族民間舞蹈的活力就在于在傳承中發展、在吸收中升華。進香舞同樣面臨這樣的困境,為了更有效地展現我國豐富的民族文化,有效推動民族民間舞蹈的發展與創新,我們只有堅持創造性發展和創新性轉型,積極拓展進香舞的生存空間,從儀式舞蹈向藝術表演轉型,如此才能實現長足發展。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儀式舞蹈應該在保留原有儀式的基礎上進行提煉,創作更有藝術價值的舞蹈作品。
六、結語
廣西“京族哈節”作為國家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極具傳承和發展的價值。京族儀式舞蹈不僅風格鮮明優美,而且具有很強的民族獨特性。因此,在保持原有性質的基礎上,將祭祀舞蹈精煉得更具有藝術性和傳播價值,具有重要的傳承意義。
通過舞臺藝術呈現的方式,讓國內外更多的人熟悉京族哈節的文化,從而將非遺舞蹈進行廣泛傳播,在保留民族之真的基礎上,加以藝術手法的提升進行創作和編排,做到守正與創新同行,跳出傳統舞蹈的創作理念,融入新思維和多元化的現代手法,力求打造嶄新的京族舞蹈傳播方式,為京族儀式舞蹈的傳播和發展打下良好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