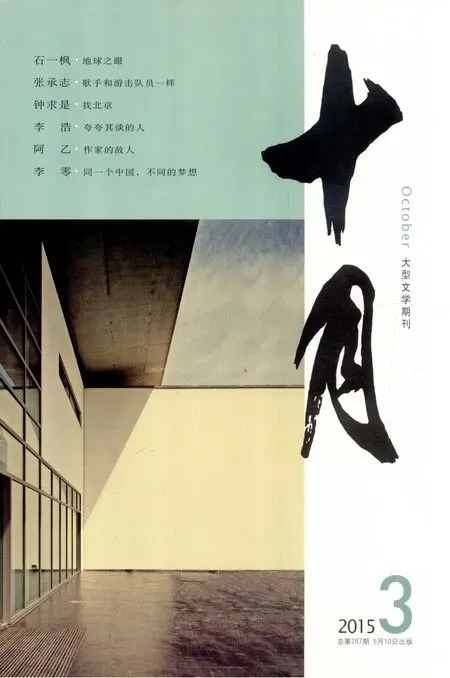主題,主題(評價)
吳玄
某日,我剛吃過午飯,接到雷默電話,他說他要跟我談?wù)勊囊粋€小說構(gòu)思。雷默在電話那頭支支吾吾的,而且還有些底氣不足,好像連早飯也沒吃的樣子。不過,我還是聽清楚了,他要寫的小說是這樣的:父親讓火車給碾死了,火化時,兒子發(fā)現(xiàn)父親少了一條胳膊,少了一條胳膊的父親,在地獄里怎么活啊,所以當兒子的必須替父親找回這條胳膊。肇事火車是山西大同的運煤車,他趕到大同,還真找到了一條腐爛的胳膊,但怎么帶回家成了問題,火車、飛機是有安檢的,肯定是不行的,總之,是歷盡了千辛萬苦,比福克納《我彌留之際》中的運棺材還艱辛,當他終于快要到家了,他累得不行了,坐在地上就睡著了,這時,一群野狗吃掉了他父親的胳膊。絕望之際,最后他剁了自己的一條胳膊,火化給了地下的父親。
聽完雷默的故事,我差點沒把剛吃下的中飯給吐出來。我說,你這個故事恐怕不行吧,第一,不真實,他父親的這條胳膊還在嗎?能找回來嗎?他在大同找到的那條胳膊是他父親的嗎?他如何確定那條胳膊就是他父親的?第二,剁了自己的一條胳膊獻給父親,這個,我不知道別人怎么看,至少,我是不能接受,第三,你為什么要寫這種故事?這不就是二十四孝的翻版嗎?這種故事,除了金庸的武俠小說,誰還會去寫?
半年前,魯迅文學(xué)院在浙江辦了一期作家班,雷默還當了班長。魯院照例要請一些人對學(xué)員的作品進行點評,此類點評,通常是嚴厲的、刺刀見紅的,據(jù)說還很受歡迎,對學(xué)員來說,大概有些類似于少女的初夜,期待,緊張,恐怕還有點痛和對痛的恐懼。湊巧,雷默的小說就分到了我手上,還未點評,他倒是先表態(tài)了,你隨便說,隨便說,隨便怎么說,都沒關(guān)系。一副做好了從容赴死的樣子。他有好幾篇小說,其中一篇叫《追火車的人》,我覺著題目還有點意思,就先看了,才看了個開頭,就覺著這小說怎么那么熟悉,再往下看,原來《追火車的人》就是他在電話中給我講過的故事。雷默還真把它給寫出來了,看來,我的打擊一點也沒有影響他的寫作,更奇怪的是,這個我事先知道的,我覺著幾乎是不可能的故事,當我看完最后一個字,它居然是成立的,所有我認為不可能的在文本中都順理成章地發(fā)生了,真實性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
確實,《追火車的人》對我的閱讀和判斷產(chǎn)生了某種顛覆,也迫使我重新思考小說的某些問題,比如敘事,比如主題,比如真實性,某些作家是不用跟真實性較勁的,真實性就像現(xiàn)實主義的一泡狗屎,堆在敘事的路上,他只要小心一些,一抬腿跨過去就可以了。比如雷默,我發(fā)現(xiàn)他大量采用了民間故事結(jié)構(gòu),不論是《追火車的人》,還是《傻子和玻璃瓶》,剝掉貌似現(xiàn)實的外衣,其實就是兩個民間故事。民間故事往往就在可能與不可能的邊緣,或者干脆就在不可能的地方,開始敘事,它最大的特征不是真實,而是不真實,越不真實才越能顯示此路敘事的才華和想象力,《天方夜譚》就是這樣成經(jīng)典的吧?
但是,思維是一回事,能力又是一回事,同樣是民間故事思維,我以為《傻子和玻璃瓶》并不算很成功,這篇小說,除了玻璃瓶被賦予了一些傻子的心理光芒,故事還是平庸了些,尤其是結(jié)尾,過于平庸,致使那些在文本中已經(jīng)閃爍光芒的玻璃瓶,好像放錯了地方。《追火車的人》可以證明雷默作為小說家的能力,我愿意為他做專家狀寫點評,也是因為這篇小說,在此之前,雷默經(jīng)常只能完成半篇小說,譬如早幾年他視為代表作的《氣味》,前半部的氣味蠻是性感幽微,后半部忽然轉(zhuǎn)到了辦公室的流言蜚語,好像是腦子短路了,把前面苦心經(jīng)營的氣味弄得蕩然無存。但《追火車的人》就不一樣了,雷默似乎得到了神助,或者就是某某靈魂附體,他突然間擁有了一種屬于他個人的敘事能力,他把不可能輕而易舉地變成了可能。
但是,我是否可以就此推斷《追火車的人》就是一篇好小說。我又想起了小說的主題,平時,面對小說,我并不太想得起小說的主題,可是,《追火車的人》逼迫我反復(fù)地想小說的主題,我還是要問,雷默干嗎要去寫二十四孝,它是一個有效的主題嗎?它跟我們當下的生活有關(guān)嗎?它跟我們的心靈有關(guān)嗎?它跟我們的時代有關(guān)嗎?二十四孝是祖宗崇拜留下的心懷叵測的遺產(chǎn),寫得再好又怎樣呢?如果非要寫二十四孝,那也應(yīng)該批判地寫才對吧。大概是我過于警惕二十四孝之類的傳統(tǒng)了,我發(fā)覺我?guī)缀跏潜槐频搅酥餍膳u家的位置上,我是多么希望雷默同志立即回到時代中來,回到生活中來,回到我們中來。
我的希望,在點評的時候,早就表達過了,現(xiàn)在,我又重復(fù)一遍,我覺著自己有點可笑,至于哪點可笑,我也說不清楚。前幾天,雷默在電話中說,他新寫了一個短篇《信》,《收獲》留用了,你也看看。《信》講的是我和一位百歲老人,用行將消失的書信交往的故事,以時代變遷作為背景,顯得開闊而又有些雋永的意境。雷默依稀還保留了民間故事思維的影子,但確實如我所愿,他回到了生活。其實,回到生活并不難,我完全沒有必要大聲疾呼,對雷默來說,民間故事思維,或許才是重要的,這一點,起碼很容易將他與別的作家區(qū)分開來,或許將來他會給小說帶來一點新的什么,誰知道呢。
責任編輯 宗永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