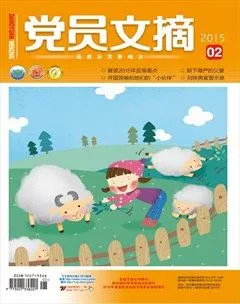當前國際形勢演變的十大特點
徐娟 金瑞
金融危機發生后,國際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呈現出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特點,和平與發展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挑戰。
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面臨深刻調整
世界范圍內的蕭條之后,人們并沒有看到傳說中的蓬勃復蘇,金融危機逐漸轉化為債務危機,在經濟持續低迷的作用下,各國政治和社會也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政府對金融危機舉措不力,民眾對國家治理能力產生懷疑,極端情緒愈演愈烈,最突出的表現是“街頭政治”持續上演,如挪威槍擊案、“占領華爾街”運動、“阿拉伯之春”等事件。
危機不僅損害了原有國際秩序的經濟基礎,而且降低了西方國家外交政策的執行力,更松動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關系。當前,多中心國際秩序已顯現,世界權力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尤其是美國單方面主導國際秩序的能力在削弱,加速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重組。
國際力量對比的舊平衡被打破
危機時代全球原有平衡被打破,導致國際格局正發生深刻變化,傳統西方大國(美歐日)集體下沉,新興國家群體性崛起,其中以金磚四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表現最為亮眼,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但是,原有國際機制的受益者并不愿意接受由此帶來的權力變化,對新興國家表現出強烈的排他性。在維護和重塑之間,雙方尚未找到利益契合點,使得國際體系存在對抗性風險,大國關系走向充滿了不確定性。
全球性的兩極分化加劇
經濟全球化在推動生產力向前發展的同時,也加深了全球的兩極分化,發達國家利用資本、技術優勢,通過不平等的國際貿易控制、盤剝發展中國家,數字鴻溝愈來愈大。隨著科技革命的到來,資本所具有的內在擴張性特質更加顯現,發達國家的優勢地位日益被強化,而原本弱勢的發展中國家越發處于不利地位。
全球性兩極分化必然帶來各國利益和訴求不斷分化,各國為在未來國際秩序中占領制高點而競爭加劇。在這一過程中,傳統的國際規則和觀念受到沖擊,聯合國作為國際權力中心的作用逐步喪失就是例證。一些大國選擇性地解讀國際規則,采取單邊行動引發國家關系緊張,這無疑增加了國家間關系的不確定性,致使地緣政治環境日趨復雜,國際形勢加劇動蕩。
西方國家面臨體制結構調整震蕩
西方國家表現出的經濟衰退、政治動蕩、社會抗議等困境表明,西方正在經歷二戰以來最嚴重的危機。此輪危機把西方國家的制度缺陷和結構性矛盾暴露無遺,而新自由主義、緊縮財政等并未帶領西方走出困境。政府在應對金融危機時,在國家干預和“市場萬能論”中左右搖擺,政治決策的不確定性且相互推諉,造成國家解決問題的能力大大降低。另外,為取悅選民,各政黨開出諸多“口頭支票”,掉入“福利陷阱”的西方對危機治理可以說寸步難行。民主政治制度效率低下,引發民眾對政治體制的質疑。信任危機沖擊社會穩定,社會極端思潮抬頭,此起彼伏的民眾抗議既是民眾表達對就業、移民、醫療、福利等制度的不滿,也是西方社會中產階級萎縮、貧富分化加重的表現,體制矛盾最終釀成體制危機。西方國家的體制機制正面臨巨大的變革壓力。
伊斯蘭國家持續動亂并嚴重外溢
伊斯蘭國家在經歷風暴洗禮后并未走出陰影,中東局勢遠未明朗。全球化密切了中東和世界的聯系,也觸動了伊斯蘭國家政治民主化這一敏感神經。
由于受到地緣政治環境不利因素的影響,伊斯蘭國家的全球化進程是被動的,伊斯蘭傳統文化所受沖擊巨大。由此可見,伊斯蘭國家政局動蕩的前提早已存在,只是社會轉型的訴求一直被外部勢力所壓制,美國中東政策的收縮性調整,為伊斯蘭國家政治社會轉型提供了契機。在“后帝國時代”,政治動員的作用凸顯,“全球政治覺醒”成為催化劑,潛在危機最終發展成為全面動蕩,民主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使得民眾走上街頭,不僅波及整個阿拉伯國家,還產生了外溢效應,甚至擴散到歐美。
海上爭奪與對抗凸顯
陸地資源逐漸枯竭,人類將目光投向了新能源,而深海的油氣資源、可燃冰、海濱砂礦、多金屬結核等,儲量之大遠超當今人類需求。對能源需求的激增促使海洋科技突飛猛進,人類對海洋資源的勘探開發進入新階段,各國不斷上演“藍色圈地”運動,海上競爭愈演愈烈,各種利益矛盾凸顯。
海洋爭端頻繁亮相國際舞臺,南北極爭端、中菲黃巖島爭端、中日釣魚島爭端、韓日島嶼爭端、英阿馬島爭端等輪番上演,國際海洋爭端也逐漸從單純的島嶼歸屬發展成為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劃定,對海底資源的爭奪也從“暗斗”階段上升到“明爭”階段。
生態危機正向社會危機轉化
在當前人類面臨的三重危機中,金融危機是短期危機,在一段時間內可以得到恢復和改善,而生態危機和能源危機是更為嚴重的長期危機。現代工業文明在科技的一路高歌中忽視了生態的有限性,現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使得人類作用于自然的速度、力度、強度不斷加劇,自然災害的發生頻率、危害程度、波及范圍都是空前的,人類對自然的破壞程度已經遠遠超過自然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生態危機若繼續發展,帶來的惡果不僅僅是經濟和生命的損失,而是人類文明的終結。
網絡空間日益成為國家安全的新挑戰
如今,網絡已經嵌入人類的整個社會運行,關乎社會系統能否正常運轉,這意味著網絡賦予了國家安全新內涵,可以說,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2013年的“斯諾登事件”不僅折射了美國的網絡霸權,而且也為各國的國家安全敲響了警鐘,信息正在成為一種新的戰略資源。
作為國家安全博弈的新領域,一旦網絡受到攻擊,其破壞力堪比核武器,因此,網絡被稱為新的“核按鈕”。網絡恐怖主義、網絡犯罪、黑客攻擊等,使國家面臨新的安全困境。同時,網絡改變了國家的安全范式,維護國家安全不再僅僅是增強軍事實力,還要增強國家保護信息和獲取信息的能力。
國際公共認知能力嚴重滯后
氣候變化、非傳統安全、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等全球性問題對全球治理的需求空前高漲,而國際社會對全球治理的供給卻明顯下降。究其原因:一是世界經濟的持續蕭條,使得各國政府無力將更多的資金投入到全球治理中,各國的關注點更多地放在解決國內民眾的利益訴求上,各國政府既無意愿也無能力在全球治理方面有所作為。二是“反全球化”浪潮不絕于耳,而現有國際機制又不能有效解決全球性問題,致使全球治理碎片化,由于主體利益的差異性,使得在行動的認同上很難達成共識,造成治理成本增加。同時,全球化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如社會失衡、貧富差距、資源短缺、環境惡化等,使得全球化的推動者也對全球化猶豫不決,給全球治理體系帶來新挑戰。
國際社會的諸多矛盾
存在激化、失控的危險
國際社會的矛盾源于國家間的利益對抗,當矛盾各方在利益方面的政治關系發生激化,甚至是出乎意料的非常態發展超出內政的心理承受程度,必然會引發內外政治局勢的劇烈變化。隨著人類需求的不斷增長,資源的稀缺性不斷顯現,加大了利益沖突的風險,再加上經濟的不平衡和文化的差異造成國際人權意識的分歧,國家間的戰略互信很難構建。地緣政治變遷、非均勢化發展、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極端宗教勢力壯大、生態環境惡化等因素,都會導致非常態下的利益沖突升級。在國家利益多元化的今天,某一領域的沖突都會牽動其他領域的穩定,引發地區、國家甚至國際社會的全面動蕩。
(殷欣奎薦自2014年12月1日《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