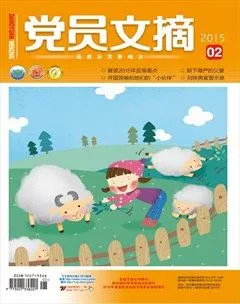親戚為什么不那么親了
黃菲
在我們的生命里,存在著這樣一種人:他們不是你可以放心傾吐心事的人,但關鍵時候卻是你可以托付大事的人;他們總是在互相攀比,總是在背后說長道短,但他們也互相扶持,互相守望,在對方出事時第一時間趕到,出錢出力,出謀劃策;他們盡管有時互相嫌棄,互相指責,但在葬禮上也會為對方悲痛流淚……他們是歡喜冤家,是麻煩制造者,但也正是他們,構筑著我們對這世界最初的眷戀,結成了我們和這世界最天然的親緣——他們是我們的親戚,是我們人生中必不可少的角色。
然而,一個傷感的現實是,不知從什么時候起,我們的親戚越來越少,關系越來越疏遠,曾經讓我們覺得溫暖的親戚,慢慢地沒那么親了。
當我們懷念親戚時
我們在懷念什么
盡管親戚似乎離我們越來越遙遠了,但總有一些時候,我們會懷念親戚。
年輕一輩最懷念的,是“走親戚”的熱鬧和快樂。70后的許多和妻子在杭州工作,老家是安徽的一個小縣城。提起親戚,許多說:“學生時代,最盼的是過年走親戚。除了去外公外婆家,還要去叔叔伯伯姑姑姨媽家。雖然當時大家生活都清苦,但請客那天會做很多好吃的菜。表哥表弟表姐表妹一起玩耍,大人們邊喝酒邊聊天,別提多美了。”
80后的陳曦和許多有著相似的依戀。他說:“小時候,我在姥姥家待的時間最多。姥爺弟兄好幾個,所以我的叔輩舅舅也多,他們的孩子更多,我就有十來個表哥。一放暑假我就去姥姥家,表哥們領著我到河邊捉魚,爬樹上捉知了,每次快開學的時候,我都舍不得離開。后來,隨著姥姥、姥爺相繼過世,親戚們慢慢疏遠了,那些曾經親密的表哥,由于各自天南海北,相聚就更難了。”
父輩們最難忘的,是親戚們互相扶持的情分。60后的老易說:“我兒子考大學那年,我摔斷了腿,半年多沒有去做工,孩子媽媽又不巧生了場大病。收到錄取通知書本來是高興的事,但一家人愁得不知怎么辦才好。親戚們自己手頭也不寬裕,我們也不好開口借。第二天一早,兒子的兩個舅舅和兩個姨媽來了,說他們已經湊齊了學費,還給兒子準備了一個新皮箱,一套新衣服,一雙新皮鞋,說去省城上大學不能太寒酸。”
關于親戚,我們各有故事,各有心思,但有一種情感是共同的,那就是懷念。懷念的,是歡樂親昵的群居生活——逢年過節的團聚是那么熱鬧,和表哥表姐堂兄堂妹一起玩樂的時光是那么歡快;懷念的,是溫暖醇厚的人情味——雖然相互之間也難免有點小磕小碰,但只要哪家遇上了困難,親戚們就一定會及時趕到;懷念的,是溫良和美樸實醇厚的“過去的日子”——大家長幼有序,禮節周全,有借有還,顧全體面。
親戚沒有變,是時代變了
木心曾經寫過一首優美的詩:從前的日色變得慢/車,馬,郵件都慢/一生只夠愛一個人。“從前”是美好而又詩意的。然而,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帶走了“從前”,那田園牧歌般的“過去的日子”成了我們共同的鄉愁。親戚,是鄉愁中一道雋永的風景。
人情淡了,不是親戚變了,不是我們的心變硬了,而是時代變了。木心的那首詩,叫做《從前慢》。是的,從前,我們生活在一個慢時代,而現在,我們生活在一個快時代。這快的時代改變了很多事物,包括我們和親戚的關系。
城市化進程加快了,人口的遷徙變快了,導致大量由宗親血脈形成的關系網逐漸疏離,建筑在小農經濟基礎上、以家族為核心的社會結構受到了巨大沖擊。大量人口的流動,加劇了家族觀念的衰落。長期漂泊在外的流動人口,與家鄉親戚的接觸自然少了,與親戚間的關系必然日漸淡漠。“我們這代獨生子女,父輩大多有兄弟姐妹,幼時過年聚會二三十口人,長大后堂表兄妹各奔東西,幾年難見,就漸漸疏遠了。”在長沙工作的黃斌,老家在山東,現在一個叔叔在上海,一個姑媽在青島,一個姨媽去了新加坡,表兄弟堂兄弟全都相隔甚遠。“俗話說一代親、二代表、三代了,大概是有道理的。”黃斌遺憾地說。
社會發展變快,同時也意味著親戚之間會出現發展的不平衡。發展得好的,上升到了更高的社會階層,發展得慢的,停留在原來的階層。當親戚之間的差異變成了階層與階層的差異,疏離和隔膜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以前的情分固然還在,但真的相處起來,可能雙方都會覺得不夠舒坦自在。
我們的社交方式也更加快捷和多元了。親戚這種最傳統的人際關系是建立在親緣上的,然而,隨著社會變遷,這種社會關系在城市里已經開始逐漸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業緣、利益緣。所以,我們的“朋友圈”里,更多的是同事、領導、客戶、合作伙伴,鮮少有親戚。而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我們最熱衷的交往更多地建立在趣緣,即趣味一致上。我們的交往圈開始慢慢變成一個“價值圈”,親戚漸漸淡出了這個圈。
社會的快速發展,加速了代際之間的差異,這種差異令親情變得不那么可愛了。一方面,中國傳統的熟人社會注重人情、私情的表達,相互了解、打聽各自的情況,常成為典型話語;另一方面,已經習慣生活在陌生人社會中的年輕人,則更注重自身的隱私和個體感受,熟人社會中常見的噓寒問暖、問候打聽,往往會讓他們產生被窺視感而覺得不適。
親戚仍是我們
最親密的關系
毋庸置疑,中國必將會由熟人社會走向陌生人社會,所以,宗族、親戚觀念的式微是一種必然。然而,不管時代的變化怎樣改變著我們和親戚之間的關系,有一樣東西是不會變的——“親戚”的背后,是一脈相傳的親緣關系和倫理秩序,而我們中華民族是重視親情和倫理的。
是的,在網絡上,你有許許多多“親愛的”和“親”,但是,親戚仍然是不可取代的。親戚能滿足你對親密關系的需要,對熱情與關懷的需要,對安全感與信任感的需要。我們和親戚的關系因為摻雜了太多的“俗務”而顯得不那么高雅,但這樣的關系因為浸潤了人氣而有了更堅實的基礎,更加接地氣。你和朋友也許因為一點誤會或者話不投機便有了芥蒂,斷了來往,成了茫茫人海中互不相干的路人,可是親戚,因為和你有著太深的淵源、太多的羈絆,即使有這樣那樣的矛盾,你們的情誼仍在,并伴隨你們一生。
我們無法回到從前。而且,在享受了現代文明帶來的巨大便利之后,不管農耕文明之下的群居生活多么溫情和淳樸,我們也只愿意遠遠地致敬和懷念。可是,總有些什么,是我們應該做、值得做,也能夠做的,那就是,像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一樣,將中國傳統文化中那些美好的、堅貞的、厚重的部分傳承下去。比如,重溫單純的親戚關系,令親戚重新親起來,令家族觀念在下一代心里不至于一片空白。
親戚之間不管差距有多大,對親密情感的渴求是一樣的,對信任感和安全感的需要是一樣的。不要擔心會“高攀”了那些風光顯赫的親戚,再成功的人也需要溫情;不要嫌棄那些愛盤問打聽的親戚,那只是他們表達關心的方式,也是一種親情流露;不要害怕打擾那些忙碌的親戚,一份久違的問候也會令他覺得驚喜和感動。拿出你的真心來,因為真心一定會被感覺,被呼應,被傳遞,會讓你成為親戚這條親情鏈上最結實強韌的一環,一環一環鏈接下去,親情才會源源不斷,生生不息。
(摘自《時代郵刊》2014年12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