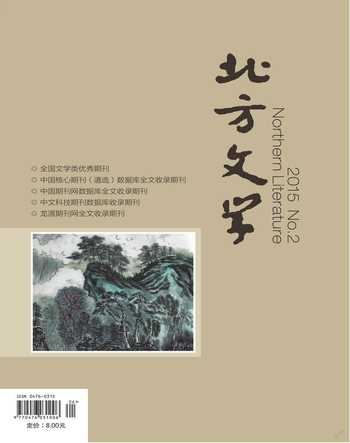訴寫戰斗的靈魂
劉昕
摘 要: 魯迅和昌耀的作品皆具忠于內心、直面現實的氣度,昌耀曾在書信中多次稱贊魯迅的《野草》。本文以昌耀的詩歌、魯迅的散文詩《野草》為例,試從詩歌的孤獨、焦慮、戰斗精神角度,尋找二人藝術氣質的相似性,探究魯迅對昌耀的影響。
關鍵詞: 昌耀;魯迅;孤獨;焦慮;戰斗精神
20世紀中國的主題是變革:五四啟蒙、新中國成立、改革開放。20世紀的文壇在歷史大環境下激流涌動,文學思潮面對變革,消亡與發展共生,引領其前行的文人此時在藝術、人生道路的探索和選擇上尤為重要。魯迅用一叢野草歌唱,昌耀用自由詩體呼喊,他們在時代浪潮中用文字訴說靈魂。
一、社會轉型下的孤獨
文化的氛圍沉悶壓抑,精神的天空一片黯淡,昌耀1986年后的詩文與魯迅《野草》的創作時代有相似之處。其創作均有社會轉型期真實內心的表露,字里行間充斥二人無可遁逃的孤獨之痛。
(一)
“五四”是一個新舊思想交替、價值裂變的時代。國家風雨飄搖、中西方文化撞擊融合,魯迅1918年在《新青年》上發表《狂人日記》正式走上文壇而當五四啟蒙的高潮逐漸褪去,北洋軍閥統治下的北京文化界寂寞荒涼,當權者不斷鎮壓學生運動和新文化運動。
作于此時的《野草》反映魯迅愈積愈深的孤獨之痛,其中不乏表現孤獨感的意象。朔方的雪是孤獨的,如粉如沙、決不粘連;野花園墻外的兩棵棗樹是孤獨的,落盡果子和葉子;與朋友告別、獨自遠行的“我”也是孤獨的,沉沒于只有我的黑暗世界里。
(二)
同樣,1978年中國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轉折點。新時期,歸來詩人群在詩歌內容的歷史反思和藝術個性化方面做出不懈探索。80年代前期舒婷、北島推動朦朧詩新潮,后期第三代詩人自辦期刊,以五花八門的名稱標榜自己的藝術主張,匯成一股后新詩潮。昌耀雖不是潮流的寵兒,但他以22年“囚徒”沉重的生命體驗在西部高原題材的詩作中保持體驗世界的獨特方式和審美自覺,摘得“桂冠詩人”的美譽。90年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全面發展,文化轉型的世紀末期隨之而來。在自由的文化市場中,詩歌的生存環境受到極大挑戰,成為邊緣性的文體,詩人隊伍逐漸分流。同處西部地域的詩人周濤、楊牧等人開始轉向其它方向的創作,昌耀仍頑強地堅守詩歌,但詩集出版的困難、愛情的波折等等使昌耀深感“日暮獨行的悲壯”。
昌耀的詩歌描繪出一位行走在荒原、城市的詩人的孤獨與寂寞。本詩中昌耀對“詩人”定義的辯解,實則是對自己的精神安慰,他此時正在精神暗夜里孤獨前行著,仍默默堅守詩歌的陣線,且他認為這是詩人的職責。
二、矛盾對峙下的焦慮
備受孤獨烘烤的魯迅和昌耀內心積壓著重重矛盾,這些矛盾相互交織,淤積而成一種復雜的社會情緒即焦慮,折射在文學作品的世界里。
(一)
魯迅寫給許廣平的一封信中曾表達內心的矛盾:“或者是人道主義與個人主義這兩種思想的消長起伏罷”,“所以我忽而愛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時候,有時確為別人,有時卻為自己玩玩,有時則竟因為希望生命從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野草》真實坦露出一個矛盾的魯迅,潛伏著作者的緊張和焦慮。
《題辭》“我以這一叢野草,在明與暗,生與死,過去與未來之際,獻于友與仇,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之前作證。”對立詞語的聚合體現魯迅的生命體驗。在殘酷的現實中,魯迅看到社會、民眾的苦難,為知識分子和農民的不幸而悲哀,也對他們的不斗爭、不反抗感到憤怒;他把筆當做匕首、投槍是為叫醒鐵屋子里沉睡的國人,可若叫醒他們只會令其更感痛苦。這一系列對于國家和民族愛恨交織的矛盾思考追本溯源是魯迅要以對歷史意識的拾或棄來拯救中華文明,拯救中國。《好的故事》中有一本古籍《初學記》,這是魯迅筆下歷史的象征物。原本“我”捏著它在朦朧中看見一個好故事,但當我準備凝視故事的細節時,它幾乎墜落。這是歷史意識的滑落,隱含人對歷史意識的遺忘。而當我欲提筆記述好故事時,一絲記憶的碎影都不復存在,我得了失寫的病癥。遺忘導致失寫,倘若保存歷史記憶呢?從魯迅身處的五四時代角度考慮,歷史意識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本身存在病處。
魯迅用夢境描述種種矛盾,用暗夜承載重重焦慮。在夢境中:與現實矛盾的恐怖事物俯摭即是,死火和冰谷共存,狗會講人話,死人會哭。夢是人的意識在現實生活的反映,矛盾的夢一定程度上昭示做夢者現實的矛盾。在暗夜下:我和影告別,而后沉默;我的希望被消耗;我做各種荒誕奇譎的夢卻總被驚醒。這暗夜既是我身處的暗夜,即中華民族的暗夜,又是我內心的灰暗狀況,即個體靈魂的暗夜。當“我”依賴這虛無的夜,苦悶與焦慮的感覺更加真實而深刻。
(二)
同樣的矛盾與焦慮也埋藏在昌耀的內心與詩歌生命中。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不容許一個理想主義者(昌耀)在現實中詩意地棲居。
昌耀慨嘆:“我是一個可笑的‘理想主義者,我崇慕純情,對著以物化為時代的社會環境有天然的排拒心理。”[1]燎原評價,“從本質上說,昌耀是一個懷有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情結的人。”那么昌耀詩歌的理想主義是什么?是“一個為志士仁人認同的大同勝境,富裕、平等、體現社會民族公正、富有人情。”[2]但現實社會卻與大同勝境相差甚遠,因而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困住了這位靈魂歌者。《烘烤》中的詩人是“社會的怪物、孤兒浪子、單戀的情人”。他“夢想著溫情脈脈的紗幕凈化一切污穢”,可身軀備受酷刑,愈益彎曲。詩人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一如昌耀的矛盾。昌耀為“物質主義的淺薄認識”而激憤不已,卻無緣保護;他為深愛的“S·Y”成為藥材商販的新婦而痛苦,卻只能視“金錢為萬惡之源”;他無耐詩歌不被“金錢狂躁、感官刺激被高揚”時代所接納,只能自費出版。最終,昌耀在重重矛盾下陷入百年焦慮,不知前行還是卻步,“只有無謂的揮霍著自己的焦慮,當做精神的口糧”,成為一個“無家可歸者”[3]。現實的荒蕪、殘酷卻無法承載昌耀的追求,他只好在理想與現實間,在走與無路可走間,承受著身心撕裂的矛盾與焦慮。
三、精神救贖下的戰斗
“靈魂深處本不平安,敢于直視的本來就不多,何況寫出。”魯迅和昌耀作品的偉大之處不僅在于直視并描繪生存的虛無和精神的絕境,還在于依然保持無望的戰斗
激情。
(一)
魯迅的孤獨有自覺與時代保持距離的因素。秉承“拿來主義”的他把西方進步思想拿到中國來,用啟蒙立場俯瞰世態人生,然而半封建半殖民時代與啟蒙進步思想產生的巨大落差使得魯迅處于兩難抉擇中。最終,魯迅選擇戰斗以自我救贖,盡管“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而偏要向他們做絕望的抗爭”。
面對“無物之陣”,英勇而悲愴的戰士5次舉起投槍;叛逆的勇士雖記得苦痛,看透造化的把戲,仍執著地戰斗,他要令人類蘇生或滅盡;敢于戰斗和犧牲的青年魂靈盡管流血和隱痛相伴,卻堅韌地屹立。魯迅愛這些“可愛”的戰士們,愛和他們一樣擁有奮斗品質的棗樹、野薊。《過客》一文詩意展現魯迅的抗爭精神。過客身前通往墳墓的道路,身后通往黑暗牢籠的來路,他該如何選擇?這是過客的處境,也是魯迅的處境。
(二)
相較于魯迅的自覺孤立,昌耀的孤獨是詩人被時代遺棄的結果。80年代堅守理想主義信念的昌耀不被都市主流文化推崇,甚至是被排擠的對象,陷入日益沉重的孤獨與焦慮。最終,昌耀選擇反抗以自我救贖,盡管“從生到死,在多數情況下,都是不順的”,但“都充滿了苦斗這樣一種精神。”
昌耀把死亡當做血的義務,人的義務,但重點在于他仍和生命作著“苦斗”,其堅韌的意志反映在詩歌中,如金色發動機永無休止、永不退卻,雄牛犄角揚起、噌噌地行走,英雄流血不止卻愈挫愈奮。這種苦斗與反抗是絕無勝算的,他要挑戰的正是命運本身。正如魯迅以虛妄的真實性同時否定絕望與希望,構建一套“反抗絕望”的人生哲學,同樣和魯迅一般經歷社會轉型的孤獨、理想與現實矛盾編織的焦慮,昌耀無意識在與時間和苦難命運的大力絞殺中實踐這種對于絕望的反抗。
寫于1993年的《堂·吉訶德軍團還在前進》:堂·吉訶德是永遠在路上的東方游俠。盡管他詢問,“匹夫之勇如何戰勝現代饕餮獸吐火的焰口?”可是卻“沒有一個落荒者”;他雖因“丟盔卸甲的記錄”被嘲笑,但仍打點行裝去開啟山林;他明知是最后的斗爭,依然前進,以獻身者自命。堂·吉訶德的英勇不屈,使他的挑戰之旅既荒謬可笑又偉大純真,一如詩人昌耀自己,雖然明知與命運的苦斗無法勝利,卻毅然決然直視現實,咀嚼生活與命運的苦楚,這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勇氣。因此,昌耀的詩是詩人與文本的高度一致,是詩人靈肉混合體的真誠袒露,是詩人與苦難抗爭一生的寫照。
(三)
那么,昌耀是如何從一個孤獨者、焦慮者變成一名戰士的呢?筆者認為,魯迅對昌耀的影響是存在的。
從思想層面來說,昌耀后期詩歌深受魯迅直面現實的戰斗精神的影響。他曾在書稿中三次提及魯迅的《野草》,稱贊其深刻的思維美感。《野草》的深刻本文不多做贅述,且看《讀書以安身立命》一文,昌耀視讀書為心靈寄托,獲得“身外的精神價值”來面對社會,而《野草》正是其推薦的一本。可見,昌耀把《野草》作為自己的心靈寄托,并在孤獨、焦慮的心理感受中找到情感的共鳴,而魯迅思維中蘊含的存在主義色彩和無望的戰斗精神傳統著實可以填補昌耀在精神困境中的空白。在生命問題上,魯迅指出生命的終點是墳,而昌耀最終的精神救贖之路就是死亡;在苦難問題上,魯迅把苦難看作生活常態,昌耀把欣賞苦難比作美的歷程,“美,有時徑直就是欣賞苦難”[4]。
從情感層面來說,昌耀受魯迅光環的照耀,使其不自覺地向這位偉大的作家學習與借鑒。《致SY》信中“我一直想買此書而未得,幸而不久前我從街頭一個地攤旁邊經過而偶然發現了這本久覓無處的《野草》,興奮不已。”聞魯迅之大名,欲尋魯迅之《野草》。久尋而得《野草》書已興奮不已,何況閱讀。昌耀喜愛魯迅的《野草》,從愛屋及烏的角度看其實是喜歡魯迅本人。在《致車前子》信中昌耀稱自己是一個“不善于、不甚耐煩于理性思維的人”,不喜分析、綜合、判斷、推理。那么昌耀喜愛魯迅的《野草》極有可能就是感性所為。在中國現當代的文壇上,魯迅的位置無人撼動。雖然魯迅用筆桿子說真話,針砭時事、批判社會,但其左翼作家的身份使得魯迅在現代文壇是主流文學的代言人。他自覺站在時代社會之外,但時代社會卻一直擁護其在內。而昌耀不同,他不被時代接納,仍想追求“集體性社會”以安身立命。某種程度上說,昌耀在與社會妥協,這也是他及不上魯迅之處。昌耀的浪漫、感性使其不會刻意模仿魯迅的某種寫作手法,但潛移默化中以魯迅的思想情感處理現實人生,以期冀能融入社會,甚至是在當代社會擁有像魯迅一般的榮耀。
注釋:
[1][2][3][4][5][6]選自《昌耀詩文總集》[M].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7),305、433、801、726、626、6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