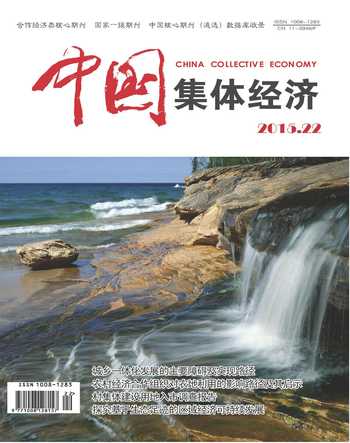農村確權賦權改革與婦女權益問題的分析
魏予祺 徐關饒
摘要:婦女是農村生產的主力,在農村確權賦權改革中保護婦女權益對農村持續發展及和諧穩定具有重要意義。文章介紹了農村確權賦權改革的內容和目標,對農村婦女權益保護的法律基礎進行解讀,針對現實社會中較為普遍的5種農村婦女權益受侵害情形進行剖析,提出須從法律政策、司法救濟、監督機制和宣傳培訓等方面著手,真正實現對農村婦女權益的保護。
關鍵詞:農村;確權賦權;婦女權益
婦女是農村生產的主力。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表明,我國農村女性占農村總人口數的48.8%,農村婦女已占農村勞動力的65%。農村婦女不僅承擔著繁重的農業勞動,還負責照顧家庭,影響著家庭和諧與鄉村穩定。然而,婦女對農業經濟增長和鄉村和諧穩定的貢獻與她們的權益間并不相稱。據全國婦聯和國家統計局的抽樣調查發現,2010年沒有土地的農村婦女占21.0%,高于男性9.1%,比2000年增加了11.8%。因此,正在試點推進中的農村確權賦權改革,婦女能否公平獲得權益,已經成為農村持續發展和和諧穩定的重要問題。
一、農村確權賦權改革和農村婦女權益
(一)農村確權賦權改革的內容
農村確權賦權改革以農村資源要素股份合作為主要內容,包括農村經濟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以及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宅基地使用權、土地承包經營權、房屋所有權的確權、登記和發證等,是賦予農民更多的財產權利、促進農村發展和穩定的機制保障。現行法律的有關規定使得農村村民委員會(及村民小組)和村集體經濟組織職能交叉,通過改革,厘清村民委員會(及村民小組)和村集體經濟組織之間的關系,進而能夠形成比較成熟的《農村社區集體經濟組織條例》,并從中明確村民委員會和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內涵、外延及其各自權能,明確村民委員會及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取得、成員的責任、權利和義務及成員資格的退出機制。
(二)農村婦女權益保護的法律依據
我國法律明確規定,女性作為廣泛民事主體中的一半,權利與男性平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規定“夫婦雙方擁有平等分割財產的權利”。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修正案》第十三條規定,“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平等”;第十七條規定,“夫妻在婚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歸夫妻共同所有,雙方另有約定的除外……夫妻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約定不明確的,歸夫妻共同所有。夫妻對共同所有的財產有平等的處理權”;第二十四條規定“夫妻有互相繼承遺產的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護法》第三十條規定,“農村劃分責任田、口糧田等以及批準宅基地,婦女與男子享有平等權利,不得侵犯婦女合法權益。婦女結婚、離婚后,其責任田、口糧田等應當受到保障”;第五十條規定了責任追究,“劃分責任田、口糧田等以及批準宅基地違反男女平等原則,侵害婦女合法權益的要追究責任”。除此之外,在民法通則、繼承法、農村土地承包法等等相關法律中也有類似的規定,保護婦女平等權利。
二、農村婦女權益侵害的現狀及原因
(一)現狀
從我國的根本大法《憲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修正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護法》、《農村土地承包法》等基本法律,以及其他一系列的規章、政策性文件,農村婦女權益保障的法律框架已經基本形成,但現實中仍有部分婦女因性別、婚嫁或婚變不能享受法律賦予的平等權益,導致法律形式上平等而事實上不平等、分配起點上公平而過程不公平的事實,主要表現有以下幾種情形。
1. 出嫁女權益得不到保障。農村出嫁女特指與其所在村組以外的男性結婚,無法或不愿將戶口遷出的農業戶口婦女,包括“農嫁農”和“農嫁非”兩種形式,其中,“農嫁農”指嫁給農業戶籍男性的農村女性,“農嫁非”指嫁給非農業戶籍男性的農村女性。一般情況下,農村婦女出嫁后,戶口即被注銷或強制遷出,即使戶口沒有遷移,按村規民約也不再享有相關權益。以“農嫁農”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為例,出嫁女在娘家的承包地被強行收回,但嫁入方又以保持土地承包現狀為由,不給承包地,須等下一輪調整時才能獲得。“農嫁非”雖然戶口保留在原居住的農村,但往往由于未履行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相應的義務,被視為“準集體成員”,允許留戶口,但土地承包經營、宅基地、土地分紅和補償等諸多權益被收回或削弱,在土地升值明顯的地區尤為突出。據全國婦聯對1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共414個縣、區的調查表明,在第二輪農村土地承包中,有46%的村莊不給“農嫁非”婦女提供宅基地,38.5%的村莊不給“農嫁非”婦女提供土地分紅、35.4%的村莊不給“農嫁非”婦女提供土地補償費方面應得的村民待遇,35%的村不給“農嫁非”婦女提供土地承包經營權;僅有2%的村對出嫁女保留土地,而14.7%的村對外來的媳婦不給承包地。
2. 離婚、喪偶婦女權益難以保全。與城市離婚、喪偶婦女相比,農村婦女權益在離婚、喪偶后更易受到侵害。由于歷史原因,農村仍舊保留一些有封建色彩的舊俗和思想,農村權益帶有濃重的男性色彩,婦女權益屬于從屬地位,這些都為離婚中以戶為單位的權益分割或喪偶婦女權益的保留帶來諸多問題。特別是對于離婚婦女,即使村委會或農村集體組織沒有采取措施,婆家也不可能讓她們留下來享受“家”里的權益,而娘家則往往把她們當作外人不予分享權益。2004年的全國抽樣調查發現,0.7%的婦女在離婚后失去土地權益。2010年的調查表明,農村婦女因婚姻變動(含結婚、再婚、離婚、喪偶)而失去土地的占27.7%,而男性僅3.7%。最近,浙江省溫州地區首例被法院受理并予以立案的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維護案件所反映的就是典型案例。
3. 上門女婿的權益遭限制。在傳統的中國文化觀念中,婚姻關系確定后,女方到男方家落戶和居住,即所謂的“妻從夫居”婚姻模式。男娶進、女嫁出,在傳統觀念中被認為正常;反之,則被認為不正常,受歧視,并在分享村集體共有資源和利益時體現,尤其在經濟發達地區。對“上門”女婿,現實生活中,有的村莊竟然少分配、甚至不分配土地等資源,在他們的觀念中,婦女本應該“嫁出去”,結果卻招了女婿上門來擠占集體資源;有的農村只允許無兒子農戶家中的一個女兒招婿,為其落戶江分享村集體權益,其余女兒的相關權益在出嫁后將被強行收回;有的則規定必須經村民委員會、村小組同意,并經村民逐戶簽名、蓋章同意,男方及其子女才能享受與本村村民同等的權益待遇。否則,連女方的權益也被收回。2014年7月31日的《京郊日報》曾報道,北京市房山區長陽鎮某村委會以村民代表會決議為借口,拒絕支付上門女婿張先生一家三口本應分到的購房補助款。
4. 未婚女性的權益受侵害。我國幾千年的封建歷史沿襲下來的家庭父權制度,使得男性以“世居者”身份在家庭中處于絕對支配地位,家庭以父系血脈進行傳承。有限的資源與并不健全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驅使“世居者”常常以犧牲“非世居者”的利益來保全自己的利益,他們指望女性出嫁空出股權、土地等集體資源,對未婚姑娘及待嫁女的權益減半計算或者預先取消資格。一句俗語“姑娘遲早是別人的”徹底地詮釋了這一現象,認為家庭和村莊投入到姑娘們身上的資源被轉移到丈夫所在村莊,并能對其做出永久性貢獻;而做出投入的家產和村莊并未獲得回報。前面所述的浙江省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婦女土地權益糾紛案中,還涉及了一直未婚的楊女士和金女士女兒權益減半的侵害。
5. 性別歧視。盡管有法律及政策明確規定女性與男性享有平等的權利,但現實中女性在獲得土地承包經營、土地分紅、土地補償和宅基地等權益時,與男性并不平等,受到了家庭和村集體組織的雙重干預。首先,當土地等“資源稀缺”這一情況出現時,村集體組織盡其可能排斥潛在的“非集體成員”擁有本來便十分稀缺的資源。有的則以“測婚測嫁”規定未婚男子在結婚前可以預先獲得“未來媳婦及子女”的耕地,未婚女性少分甚至分不到土地;有的只給18歲以上的男勞動力分責任地,規定男孩可單獨立戶,而女孩則只能隨父母;有的則給男孩分好地、女孩分差地。其次,家庭財產的繼承受傳統習俗的影響,社會習慣通常只讓男孩繼承。2005年,浙江省義烏市房屋拆遷政策規定,多子家庭按兒子數量分配宅基地,而只有女兒的家庭則不論女兒多少只給一塊宅基地。中國法制監督網曾報道,2009年6月28日通過的浙江省紹興市《×村城中城改造集體土地村民房屋拆遷安置補償意見》規定,戶口在冊的外嫁女及子女,無合法產權房屋的,不予安置;有合法產權房屋的,不享受人均40m2的保底安置;配偶一方戶口在外地的,則可以增加一個安置人口。2013年浙江省上虞市梁湖鎮某村民反映了該村的落戶政策中,規定男性可以帶妻兒遷回,而出嫁女則不能遷回。
(二)原因分析
我國法律賦予婦女與男子平等的權利,國家政策也致力于保障婦女權益的實現,但現實中農村婦女以土地為核心的合法權益屢遭侵犯,究其原因,大致可歸納為傳統觀念的制約、政策制度的不足、村規民約缺乏監督以及司法和行政救濟渠道不暢等因素。
1. 傳統的男權文化。“女性是人類社會中第一種奴隸。作為整體,她們是男性整體的奴隸;作為個人,她們一直是男性英雄們掠奪和壓迫的對象”。在我國,男權至上在《易經》中已基本形成,從秦漢,經唐宋,至元明清,漫長的封建社會系統化了中國古老的男權思想,形成了“男尊女卑”、“男主女從”等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強行將婦女置于依附性的性別角色。在傳統男權觀念的影響下,一些傳統習俗逐漸形成并沿用至今。“妻從夫居”習俗影響著農村女性的合法權益,女性結婚后搬至夫家生活,其在原居住地享有的集體資源被剝奪似乎已成約定俗成。“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男性繼承”習俗直接導致女性權益的喪失。資源的有限與擁擠,“養兒防老”和農村社會保障機制的欠缺,很自然地將女性權益盡可能排除在外。
2. 法律制度的不足。我國目前有關農村女性權益保護的法律規范并不缺乏,在《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修正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繼承法》、《農村土地承包法》等均有涉及,但法律的質量有待提升,存在反復規定、沖突、疏漏等問題,法律原則性有余而操作不足。如《婚姻法》第十八條規定“一方的婚前財產為夫妻一方所有”,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解釋(三)》(2011年)第五條明確“夫妻一方個人財產在婚后產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應認定為夫妻共同財產”,立法的原意是追求公平價值,但無形中損害了農村離婚婦女的權益。我國農村結婚傳統是男方準備房屋,女方準備生活用品類的嫁妝,房屋通常是升值的,但作為日常用品的嫁妝只會貶值或被消耗。又如,《農村土地承包法》第六條規定“農村土地承包,婦女和男子享有平等的權利”,在第三十條規定“承包期內,婦女結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婦女離婚或者喪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但在第十五條中又明確“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戶”,正是因為缺乏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取得、認定的統一法律機制依據, 導致現實中以不具備集體成員資格為由而侵犯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同時,土地政策的長期穩定性與女性因婚姻而流動的矛盾,造成因“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大穩定,小調整”而使得出嫁女權益兩頭落空。另外,以戶為單位的承包地、宅基地及其附著物以及集體分紅等權益主體,雖然形式上是中性的,但卻忽略了農村家庭中固有的男權制度的傳統,使政策在實施過程中給女性帶來不利。
3. 村規民約缺乏監督。村規民約是我國傳統鄉村文化的重要組成,介于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間,調節著社會生產生活以及道德規范。我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是農村實行村民自治的法律依據,它確認了村規民約在農村自治中的作用。《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在第二十七條規定了“村民會議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第五條又規定“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對村民委員會的工作給予指導、支持和幫助,但是不得干預依法屬于村民自治范圍內的事項”。然后,農村婦女權益受損的很多情形都打著村規民約的旗號,標榜著村民自治,以集體的形式侵犯個體成員的權利。雖然強調合法是村規民約下村民自治的前提,但由于村民自治范圍內的村民會議決議不能被干預,村民會議可以以村民決議是合法程序通過為由而不予遵守婦女權益保護相關法律條款,村民決議內容缺乏有效監督。另外,受傳統男權文化以及婦女自身素質的影響,參與村規民約討論與制定的基本為男性,制定的村規民約自然以男性利益出發。前述的《×村城中城改造集體土地村民房屋拆遷安置補償意見》以黨員大會和村民大會參會人員100%同意加以執行就是實例。
4. 司法救濟存在問題。農村婦女在自己的權益受侵害時,大多選擇村委會協調解決,然而這在村民會議上難以實現權益的維護;少部分的女性會通過法律渠道維護和保障自己的權益,但法律往往沒有有效手段來解決。以土地權益為例,《土地管理法》第二章規定“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農民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屬于農民集體所有”,“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依法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經營、管理”,這一規定使得法院難以對這些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問題做出裁判;第十六條又有“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爭議,由當事人協商解決;協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處理”。因此,法院則不能直接受理農村女性要求土地權益的訴求,而是必須先由鄉鎮政府調解,再通過行政訴訟來裁決。程序上只有在鄉鎮政府做出處理決定后,才能向法院提起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這一過程又會因管理責任、執法權限等問題而推諉。另外,多數農村沒有土地預留,即使法院作出裁決,也難以執行。
三、建議和對策
我國農村婦女權益受侵害十分普遍,已直接影響到農村婦女的家庭生活,打擊她們參與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影響著和諧社會的建構和男女平等的實現。針對農村婦女權益侵害的原因,我們認為可從法律政策、司法救濟以及監督機制著手。
1. 完善法律政策。法治國家的根本任務是依照法律和政策法規治理國家。因此,建立科學、完善的法律和政策法規是維護和保障農村婦女權益的基礎。通過修整現有的農村婦女權益保護的有關法律法規,刪除不適合農村實際的法律條款,增加法律政策的可操作性,調解村規民約與國家法律的沖突,實現農村婦女權益的有效保障。建議在《婚姻法》中明確“夫妻一方個人財產在婚后產生的收益,均認定為夫妻共同財產”;明確《農村土地承包法》中“家庭承包方”可以是“戶”,也可以是“個人”,同時在承包合同或轉讓合同的要件中,“戶”需注明全體成員及簽名;在《婦女權益保障法》中,明確“農村女性與男性在股權、分紅、土地承包、土地征用補償、宅基地分配等權益中享有平等的權利”,增加“上門女婿權益”內容,明確各種婦女權益侵害的特征、構成要件,提高可操作性;增加《物權法》中對婦女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相關規定,進一步保障婦女土地權益;細化和規范《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中“村規民約”的制定、備案、監督、修改等相關條款,保證其與國家法律政策一致;修改《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條“在土地承包經營期限內,對個別承包經營者之間承包的土地進行適當調整的,必須經村民會議三分之二以上成員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避免多數人按照鄉土社會的傳統習俗對少數人實行權益侵害,做到有法可依;在農村確權賦權改革政策制定中,可以確權到人的權益,如集體收益分配權,明確“確權到人、權跟人走”,以戶為單位的,如宅基地使用權,做到“證上有名、名下有權”。
2. 建立司法和行政救濟渠道。農村婦女合法權益屢遭侵害,與仲裁機構缺位、法院缺乏措施、基層政府對村民自治缺乏有效管理等有關。因此,必須建立采用司法和行政相結合的方法來維護和保障農村婦女的合法權利。鄉鎮政府能切實意識到維護和保障婦女合法權益的重要性,專門設立相關機構協調村規民約與國家法律的關系,調解權益糾紛;建立村民自治的司法救助機制。村民不服鄉鎮政府行政決定時,可向法院提出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發揮婦聯組織力量,發展保護婦女權益的民間組織,建立民事公益訴訟制度;在縣(市)級以上(含)的政府機關中,設立專門的婦女法律求助中心,為農村婦女合法權益維護和保障提供免費法律服務。
3. 完善監督機制。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在作出決策時,引入政策文件性別平等咨詢評估機制,充分考慮該立法和政策對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影響,消除立法和政策中對女性的不公平之處。針對村規民約侵害婦女權益明顯的現實,在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制定階段,鄉鎮政府應審查草案內容,不允許違反國家政策、法律規定的內容,提交村民大會表決,從源頭上杜絕;在村規民約的執行過程中,發現有侵犯發生的,基層政府主動介入,及時化解矛盾。
4. 提高婦女的維權意識和地位。長期“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內”的影響,導致農村婦女在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接受培訓機會、財產擁有權等方面均明顯弱于男性,在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層面處于弱勢,在集體事務中缺乏聲音和權力。因此,須提高農村婦女文化素質和法律意識,增強其維權能力。在具體措施上,一是加強宣傳,通過普法培訓與宣傳,教育和引導廣大婦女知法、懂法,增強權利意識。二是在制度上保障婦女的維權地位,提高參政比例,在村民自治組建中,確保婦女占有一定比例,保證婦女在農村重大事項決策中的參與權,以制度確保權益。
參考文獻:
[1]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M].中國統計出版社,2012.
[2]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課題組.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主要數據報告[J].婦女研究論叢,2011(06).
[3]商春榮.中國農村婦女土地權利保障研究[M].中國經濟出版社,2010.
[4]全國婦聯婦女兒童權益部調查組. 土地承包婦女權益——關于農村第二輪土地承包工作中婦女權益被侵害情況的調查[J].中國婦運,2000(03).
[5]全國婦聯.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修改論證材料[R].2004.
[6]浙江省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障問題研究課題組.淺析浙江省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障問題[EB/OL].http://lib.zidx.gov.cn,2004-12-23.
[7]潘綏銘.神秘的圣火[M].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8]何華征. “神似”的中西方男權主義思想-談古代社會人們對男權統治的抗爭[J].勝利油田黨校學報,2013(03).
(作者單位:魏予祺,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學;徐關饒,浙江大學繼續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