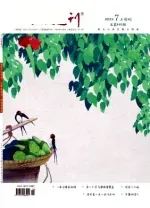春風不度玉門關
吳勝明
黃河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唐代詩人王之渙的這首《涼州詞》很有名,其中還有個故事叫“旗亭畫壁”。有一年,三位詩人王昌齡、王之渙、高適一起到旗亭酒樓飲酒。恰好有十多位歌女也在此聚會吃飯。三人約定說,我們三人都有詩名,現在請歌女演唱,誰的詩入歌辭多為勝。一歌女,先唱的是王昌齡的,王在墻壁上畫一首;接著唱的是高適的,高則畫一首;接著又一歌女唱的仍是高適的,高則畫二首。這時,王之渙臉上掛不住了,指著歌女中最美的一位說,她唱的若不是我詩,我終身不與二位爭勝負。不久,這位歌女唱的就是“黃河遠上白云間”這首詩,三人大笑,飲醉才歸。可見,這首詩在唐代已是膾炙人口的名篇;有人甚至認為是唐人絕句壓卷之作。筆者介紹此詩,因為這是一首包含地理科學知識的生動描寫的詩。在介紹之前,先寫一件往事。
上世紀60年代,筆者在中科院做研究生去甘肅酒泉搞農業區劃。當時的中科院副院長、著名的地理氣象學家竺可楨也親臨酒泉為我們講話,特別講到這首詩的第一句應為“黃沙直上白云間”。他說,在涼州(今甘肅武威)是見不到黃河的,倒是可以見到滾滾的黃沙;而且只有“黃沙”才和“孤城”等相對應。竺老的話過去了幾十年,但至今我仍記憶深刻。竺老是一位對古代詩詞很關注的科學家。他1972年寫的著名論文《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中就引用了這方面的資料。他寫道:
唐朝詩人張籍(公元765年~約830年)《成都曲》一詩,詩云:“錦江近西煙水綠,新雨山頭荔枝熟”,說明當時成都都有荔枝。宋蘇軾時候,荔枝只能生于其家鄉眉山(成都以南60公里)和更南60公里的樂山,在其詩中及其弟蘇轍的詩中,有所說明……從陸游的詩中和范成大所著《吳船錄》書中所言,十二世紀,四川已不生荔枝……現在眉山還能生長荔枝,然非作為經濟作物……由此證明,今天的氣候條件更像北宋時代,而比南宋時代溫暖。
你看我們的院長竺老是多么關注古代文人的詩詞啊。他這篇論文中引用的詩文既是“證據”,又使文章生動無比。筆者寫這個專欄也是希望科技界的專家、學者能夠從中國古代文人的詩詞中汲取豐富的營養。
三年前我去北京大學數學院請研究拓撲學的院士王詩宬為我的科學著作《中國最美的地質公園》寫序,發現他辦公室門上貼有他抄寫的柳宗元的一首詩《江雪》: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我看過后,心中涌起層層的波濤!好!
還是回到王之渙的詩。“春風不度玉門關”是這首詩的最后一句,但卻兩次出現在20世紀中國高考地理試卷試題中,問這里“春風”是指什么?這卻難倒了一些考生。正確答案應為這里的“春風”是指我國的夏季風。我國為季風氣候,春夏之際,風從東南沿海吹向大陸,稱為夏季風。它帶來了豐富的降水,但越往西北其勢力越弱,到甘肅省的河西走廊(即涼州,今武威市)就如同強弩之末了。這就造成玉門關以西沙漠、戈壁廣布。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這是王之渙另一首流傳廣泛的詩《登鸛雀樓》。說明一個道理,就是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遠,才能看到事物的大局和全局。我們研究地學的人,在野外工作時,對此深有體會。我們到一個地方總要登上最高點,鳥瞰這個地方的山水大勢。杜甫說,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不到絕頂,怎么能體會到眾山小的境界。孔子兩千多年前就發出了“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嘆!做任何科研工作,應該都要更上一層樓;你在每一層樓看到的風光,看到的景物以及關系都是不同的。我在廣西資源縣天門山考察資江上游的180°曲流時,花1個多小時艱苦地登上山的頂峰時,瞭望這個河流的拐彎,從內心發出:好美啊!最好的風光不一定在頂峰,但頂峰一定有你看不到的精彩!
(易茗摘自 《中國科學報》2015年0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