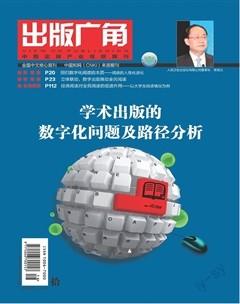論俄羅斯后現實主義文學的藝術風格
【摘要】后現實主義文學產生于19世紀下半葉,是俄羅斯文學運動中涌現的一個重要流派,至今仍在不斷地發展和演變。后現實主義文學產生于后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彼此交融、作用的過程中,具有濃厚的后現代主義氣息,但并不盲目追隨后現代主義的價值取向。本文介紹了俄羅斯后現代主義文學的內涵和基本特征,探討俄羅斯后現實主義文學的藝術風格,以期對當代中國文學發展有所借鑒。
【關鍵詞】俄羅斯文學運動;后現實主義文學;文學藝術風格
【作者單位】王敏,山東女子學院。
【基金項目】俄羅斯女性高等教育發展狀況分析,課題編號:NXGDJY03。
蘇聯解體后,社會主義現實文學一統文壇的格局不復存在,俄羅斯的文學界呈現錯綜復雜的氣象。1991年后的俄羅斯文壇,不再以意識形態來劃分文學派別,而是以體裁、風格、文體等來劃分流派,形成多元化局面,先鋒主義、現代主義等多個文學流派并存,后現代主義則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一、俄羅斯后現實主義文學的內涵
俄羅斯后現實主義文學,是指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文壇上仍堅持發揚俄羅斯文學傳統的現實主義,并在此基礎上吸納后現代主義文學藝術的新現實主義文學類型。俄羅斯后現實主義文學的形成是建立在以下基礎之上的:一是對這個不斷變化世界的認知;二是已經得到一定程度的理解與認同;三是創作者審視、描繪世界的開放性。
二、俄羅斯后現實主義文學的基本特征
俄羅斯后現實主義文學有它獨特的人生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后現代主義文學。后現實主義并不認為混沌亂象是難以擺脫的品質,而是主動尋求超越它的途徑。后現實主義將對非因果性關聯的探尋與決定論整合起來,將永恒性與耦合性整合起來,將原型性與典型性整合起來,在混沌亂象中進行自我調節。從人與現實的關系來看,俄羅斯后現實主義文學表現出兩個特征:一是不懷疑現實世界,現實是多樣性的,是多種因素的集合,并以各種方式影響人的命運;二是不割裂人性與現實的聯系,以人作為支撐,去混沌深層尋找支點,人的命運總是在混沌的環境中沉浮。
俄羅斯后現實主義文學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在受困現實中尋找意義的人。例如,馬卡寧描繪的“地下人”,他是社會底層的典型人物,有非常多的缺點,不肯接受蘇聯時期的制度,也不肯融入蘇聯解體后的新社會制度。他始終堅持自我選擇的一種生活狀態,不趨炎附勢,不望風使舵,而是始終堅持自我,即使他始終不被社會所認同和保護。通過塑造這樣的人物形象,俄羅斯后現實主義文學家反思了蘇聯時代人們的命運,批判了當代俄羅斯在資本積累時期的丑態,表達了對追求自我的推崇與渴求。
俄羅斯后現實主義作家往往很會“講故事”,其作品帶有很強的可讀性和藝術性。在他們手中,通俗與高雅、現實與神話之間的藩籬已不復存在,他們用迷宮般的情節、嘲諷式的語言對現實進行寫生,塑造出一個個躍然紙上的文學形象,不但讓人們讀得有趣,而且使人主動去思考現象背后的深層意義。例如,葉里扎羅夫的《圖書管理員》,作者運用魔幻藝術手法賦予蘇聯時期那些被雪藏的書籍改變人們命運的魔力,所表達的觀點是這樣的:蘇聯時代雖然不完美,但卻有其不可取替代的精神力量。對蘇聯和俄羅斯的比較,只是作者創造的表象,而深層次是作者對歷史與現實的思考,也代表了一部分年輕人對蘇聯時期的特殊心結:不是一味決裂,全盤否定,而是一種對故園的懷念與追思。
三、俄羅斯后現實主義文學的藝術風格
1.將決定論與非因果性關聯的尋找相結合
決定論是俄羅斯后現實主義文學中的常見思想,后現實主義文學家經常為作品中的描寫尋找現實邏輯依據,作品中角色的生存狀況往往和社會之間存在某種因果關系。與此同時,后現實主義文學并未將作品當作一種現成的社科資料來看待,而是試圖在非因果性與決定論間構建關聯。后現實主義文學作品經常將本不存在因果關系的事件聯系起來。例如,在斯拉波夫斯基的《我——不是我》中,主人公的身份總是在不斷變換,這賦予故事情節一種荒誕的色彩,徹底打破了傳統現實主義的邏輯結構。又如,在馬卡寧的《地下人,或當代英雄》中,主角捍衛其創作的權力,甘愿棲居在地下,但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像這樣一個穩重的人,居然會做出“殺人”這一反常的行為。可以說,這樣的故事情節徹底打破了因果性的支配,顛覆了讀者的認知,并令讀者不由地產生困惑。
2.以典型性和原型性的彼此交融作為營造藝術意境的原則
受決定論的影響,傳統現實主義普遍存在這樣一種現象,即主體在反映客體時往往受限于客體的規定性。這一點反映在作品之中,即作者執拗于客體的“現實性”傾向,專注于刻畫典型境遇中的典型性格來突出某種“真”。在俄羅斯后現實主義文學作品中,這樣的情況也有發生,但更傾向于對藝術意境的營造,也就是展示藝術的典型姿態。后現實主義作家期望借助這一手法來對作品的重心進行深入探討,即從多個角度對人的精神存在進行深層次的思索。在戈連施坦的長篇小說《贊美詩》中,作者將《圣經》中提到的四種災難——戰爭、饑荒、瘟疫、死亡和俄羅斯民族所遭遇的衛國戰爭、大饑荒、極權專制等真實場景交錯在一起,使現實的界限變得模糊。又如在《新魯濱遜一家》中,盡管作者仔細交代了人物的現實背景,但描述其全家重新進入森林過原始生活的情節,又賦予了現實一種亦幻亦真的朦朧色彩。
對宗教形象的應用也是俄羅斯后現實主義文學作品中很常見的內容。例如,在作品《圣經》中,諾亞堅守正義,謹遵圣訓,即便在大災難面前依然堅持自我,毫不動搖,并打造了一艘拯救生靈的方舟。又如在作品《新魯濱遜一家》中,父親的一舉一動無不體現出諾亞精神。為了避免家人被日益腐壞的社會風氣所侵蝕,他攜帶妻兒遠離都市,遷徙到偏遠的鄉村地區,安家于森林的一個洞穴之中,并將這個洞穴視為挽救心靈的諾亞方舟。
3.形象結構本身體現出藝術評價的含混性
在俄羅斯后現實主義文學中,作家巧妙運用“含混”這一藝術手段來搭建形象結構,特別是借助人物性格的含混性,使作品主導思想基調中多出一分模糊感。后現實主義文學作品的人物身上往往表現出悖論與矛盾的特質,這使得讀者無法簡單地用“好”或“壞”的極端標準來對其進行評判。例如,在《贊美詩》中,敵基督就表現出十分復雜的形象特征,盡管他們也是基督的追隨者,但他們顯然不夠“完美”,他們也會有犯罪行為,屈服于撒旦的誘惑。在敵基督的身上,仁愛和貪欲相互交織,罪惡和理智彼此碰撞。又如,在作品《模糊印記》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個具有多重性格的主人公,他悲慘的經歷引人同情,他的軟弱讓人厭惡,他的自我批判又讓人對其產生一絲尊重。此外,很多后現實主義文學家在敘事時并不表明自己的立場,使讀者閱讀時產生困惑。值得注意的是,這并不等同于不摻雜任何個人想法的“零度狀態”,而是其將價值判斷隱藏于更深的深度,讀者只有真正了解作品中的角色,才能把握作者塑造這些人物的意義,進而了解作者的思想。
4.以語言為代表構建文化的多邊對話性
俄羅斯后現實主義文學往往傾向于在本民族內,甚至不同種族文化間構建橫向的連接。很多后現實主義作家都會在作品中將俄羅斯古語、俚語、俗語、蘇聯時代詞匯、意識形態詞匯、外來語摻雜起來使用,使文學作品跨越時空限制。例如,彼特魯舍夫斯卡婭的作品中常會出現一些斯拉夫教會的詞,他還會將這些詞與現代詞結合起來,甚至與高加索語系、印歐語系中的詞匯結合起來,構建出一些臨時性的新詞。
后現實主義文學的多邊對話性也表現在對標點符號的運用上。后現實主義作家打破了標點符號表示語調、停頓的用途限制,使其在文學作品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例如,馬卡寧的作品中,括號、冒號往往會發揮意想不到的作用,尤其是括號會頻繁出現。如他的2萬字小說《出入孔》中竟然出現了大約200個括號,每一句話都有一處甚至多處括號。括號的使用不但方便讀者了解相關信息,也使作品內容的表達更加淋漓盡致。
綜上所述,俄羅斯后現實主義文學與后現代主義文學、傳統現實主義文學有較大區別,后現實主義文學家在繼承蘇聯思想的同時,反思俄羅斯的社會現實,并進行比較,繼而引發讀者的深層次思考。客觀來說,俄羅斯后現實主義文學的出現是特定歷史背景、地域文化的產物,代表了現代文學的發展方向,對此進行研究和思考,對我國文學創作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1] 管月娥.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俄羅斯后現代主義文學發展的羈絆與催化劑[J]. 江海學刊,2010(6).
[2]周啟超. 后現實主義:文學思潮與藝術范式——今日俄羅斯文學氣象手記[J]. 芒種,2013(5).
[3]楊明明. 世紀之交俄羅斯現實主義文學流變[J]. 浙江社會科學,2012(2).
[4]鄭永旺. 作為巨大未思之物的俄羅斯后現代主義文學[J]. 求是學刊,2013(6).
[5]張建華. 守望經典——后蘇聯俄羅斯現實主義文學談[J]. 俄羅斯文藝,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