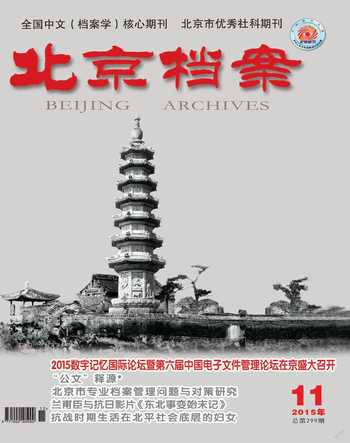“法蘭西—巴達維亞”時期荷蘭文檔管理實踐研究術
任越
摘要:本文結合“法蘭西-巴達維亞”時期荷蘭國家及地方行政管理體制與文檔管理體制變革,梳理荷蘭近代文檔管理發展的軌跡,進一步論證法國文檔管理理論與實踐對荷蘭文檔管理與《荷蘭手冊》問世的必然性與重要性。
關鍵詞:荷蘭檔案史文檔管理荷蘭手冊
Abstract:This pape illustrates the developmenttract of Dutch Archival management combing with therevolution of Country and Local administration and re-cord management system in the period of“France-Bat-avia”,and then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and inevi-tability of the French document management theoryand practice for the document management of Nether-lands and the birth of Dutch manual.
Keywords:Archives History of Dutch;Archivalmanagement;Dutch Manual
《檔案整理與編目手冊》(又稱《荷蘭手冊》)自問世以來,國內外學者圍繞《荷蘭手冊》的內容與歷史價值展開了全面且深入的論述,但很少有學者會提出:為什么《荷蘭手冊》會對來源原則進行論證?什么原因促使荷蘭繼承并發揚了源自法國的來源原則?筆者通過閱讀相關歷史文獻與荷蘭文檔管理工作史,認為法國在“法蘭西-巴達維亞”時期(1794~1813年)對荷蘭的殖民統治,將當時法國政治體制與行政管理體制被引入荷蘭,并對傳統荷蘭文檔管理體制產生影響,最終快速走上“法國式”文檔管理之路,進而引發了荷蘭文檔管理界對來源原則的關注與研究。當然,這只是筆者對荷蘭近代文檔管理轉型的一種推測,法國對荷蘭政體與行政管理體制影響有多深?“法蘭西-巴達維亞”時期荷蘭從國家到地方的文檔管理又經歷了怎樣的轉變?這將成為研究《荷蘭手冊》問世前荷蘭文檔管理背景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
一、巴達維亞時期的荷蘭國家
與地方行政管理體制
(一)國家行政管理體制
1795年前,荷蘭共和國普遍采用合議制的政府治理方式,其中包括省、州一級地方政府、州軍事委員會、州法院、軍事學院等權力和軍事機構。所謂合議制,又稱委員會制,即國家行政組織的決策權及管理權,并不是由單一的領袖所擁有,而是平均由一定數目委員所組成的委員會共同行使。法國進駐荷蘭共和國之后,所有采用合議制的行政機構全部廢止,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官僚制的行政機構。官僚制的核心在于“集權”,因此,這一時期荷蘭每個省、州或城市處于權力核心位置的是長官,他負責為市政當局下達命令與指示。海牙在1798年后成為控制地方行政的權力中樞,地方政府失去了其在地方的自治權,而僅僅保有決策的執行權。這種在行政關系與政府組織架構上的變化最終導致法國官僚體制引入荷蘭中央和地方機構,并隨之產生了新的文檔管理機制。
(二)地方行政管理體制
1895年后,荷蘭政治體制與行政管理架構的變化最先在國家和省級行政機構顯現,但這種新的管理體制并沒有影響地方的政府管理模式。盡管之前聯合政體及合議制的政治制度已被取代,而且政府機構也更換了名字,但是大多地方政府機構的框架基本上仍與之前的情況相同。在國家層面,行政機構逐漸向法國政府治理模式傾斜,在地方層面,大多政府機構卻堅持傳統的政治框架和管理方式。盡管國家政權已經更迭,但是地方官并不情愿實行由國家和省級政權機構強加的行政模式。因此,合議制在大部分地方政府被保留下來,并作為政府行政管理的主要模式。從長遠的角度看,地方行政管理機構是無法避免官僚體制對其行政管理活動的滲透的。
事實上,法國的政治體制與行政機構對荷蘭政治體制與行政管理體制的影響是有限的,這與法國對荷蘭占領時間較短有直接關系。政治體制改革與行政管理權力的重新劃分需要較長的周期,而法國往往集中在權力與資源相對豐富的荷蘭西北部城市,因此地方政府受法國行政管理體制的影響相對較小。盡管法國行政管理對荷蘭的影響局限在國家層面,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絲毫沒有受到法國入侵的影響,但自上而下的國家治理模式以及法國入侵之后的行政縮進政策,使得地方行政管理機構或多或少地受到牽連。
二、巴達維亞時期荷蘭文檔管理實踐
(一)國家文檔管理實踐
1795年法國入侵之前,荷蘭的文檔管理實踐受德國登記室原則的影響頗深,其專司文檔處理的機構主要指設置在不同委員會下的秘書機構。行政權限較大的省、州級委員會一般由極具地方特色的地方行政官、法官與軍隊將領組成,下設2~3個秘書機構。這些秘書機構的主要任務包括四個方面:其一,決議的登記。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在會中制定的各項決策由決議登記機構負責記錄,記錄所形成的表格作為各自檔案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二,對接收和制發的信函、請示、報告及其他資料進行收集和分類。這些資料按照一定的全宗進行收集和分類,檔案種類的劃分依據該委員會制定的主要分類法,或參照國內通用的檔案分類法。其三,對所存檔案的整理。其主要標準是編年體,即按照所收集檔案的時間順序進行文件的排列。不同類別的檔案被賦予不同的符號或標記,這些符號或標記由秘書或登記員根據自身的工作需要進行設計。其四,設定檔案整理的標準。軍事委員會所形成的檔案在整個檔案體系中級別最高,整理最為規范,因此,其他合議制機構的檔案管理全部要依據軍事委員會檔案整理標準進行。
“法蘭西一巴達維亞”時期,荷蘭政體與行政管理體制相繼改變,特別是文檔管理所依賴的管理決策方式的變革,使原本文件整理、分類與裝訂工作出現了明顯的變化。法國對荷蘭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體制進行革新的同時,對文檔管理程序與管理工具也進行了改革。最具特色的是登記表(法語:Indicateur)的引入。登記表,作為法國官僚體制的一種象征,主要用于記錄收文與發文的登記情況。對機構執政長官來說,登記表是一種較好的行政控制工具。在法國官僚機構將這種登記表傳到荷蘭之前,普魯士的部分行政機構已經使用了類似的工具至少有一個世紀。時至今日,部分法國及其周邊國家行政管理機構依然沿用此登記表。
1813年后,荷蘭政治自主權重新回歸,為了提高荷蘭地方執政效率,增強執政信心,國家委員會于1818年,對不同地區與城市的行政管理方法進行了調查,并對地方行政管理機構提出了一套建議性的整改標準。1823年國家委員會頒布了公共行政管理法案,其中規定:(1)所有行政機構的文件實行集中化保管;(2)接收的文件在分發到不同行政機構前需要在一般的登記表中進行登記;(3)發出的文件需要主管長官的簽字,發出前要在登記表中進行登記;(4)文檔在歸檔前必須按照決策時間的先后順序進行序化后保管;(5)文檔在歸檔時不需要裝訂,而是放入文件夾或檔案盒中;(6)以主題形式進行整理的方法被明確禁止;(7)由長官簽發的決策議案及相關文檔,連同登記表直接取代之前使用的決議書;(8)建立由文件主題和文件名稱為關鍵點的目錄、索引和關鍵詞檢索體系。該法案的制定一方面結合荷蘭行政管理實際,吸收了法國文檔管理體系的長處,使文檔管理更加科學規范;另一方面側重登記在文檔管理中的管理與控制作用,為地方行政長官掌控行政流程提供支持,也為政府控制官僚機構數量的增長起到了關鍵性的抑制作用。
(二)地方文檔管理實踐
1795年前,大多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行政管理主體是市自治委員會,該委員會由40名來自精英階層的人士組成。委員會的會議遵循嚴格的程序,首席市政官將討論的問題進行匯總,并草擬相關結論。秘書將決策記錄在登記表中,形成決議書,并最終歸檔。首先,秘書在會議前就草擬好決議書的草稿,經過校對后,由文員將抄寫稿呈送給首席市政官或自治委員會負責人。決議書每年都會形成一冊,并附到會議記錄之后作為附件歸檔,作為地方文檔管理最重要的部分。其次,接收的并在會議上討論的文件會直接附在會議記錄之后歸檔;沒有在會議上討論的信件及相關材料,則單獨保存在專屬的文件夾中。再次,發出文件的草稿與正本,要以決議摘要的形式附到文件記錄的正文中,作為會議決策的一部分進行歸檔。最后,秘書人員以會議決議書的字母順序對會議記錄進行登記與排列。每年的會議記錄都要由秘書制作詳細的復制件保存到首席市政官的辦公室中,正本需要由登記室保管,草稿則直接保存在秘書人員手中。
1795年后,法國在荷蘭諸多地方政府采用新的委員會制代替了原有的合議制,新的委員會制稱為市政委員會制,即每個城市任命2~4名市長,市長脫離市政委員會,單獨組成執行委員會。在接下來的18年中,地方政府執政的核心力量從市政委員會逐漸向執行委員會轉移。1811年后,執行權力幾乎被市長所把持。盡管從國家至地方的政治和行政方面出現了根本性變化,但決策記錄的方式并沒有變化,文檔的保管方式同樣沒有改變。這一時期,決議書改稱法案,是為了仿效國家和省級行政機構對決議書的稱呼;接收的信件依然放置在相同會議程序的卷內;文檔的登記順序與分類標準依然沿用傳統的方法與程序。雖然文檔管理方式與內容保留一致,但政府機構中秘書機構與城市公務員的文檔工作量發生了明顯變化:其一,法國嚴格控制地方政府的行政決策,要求地方執政官每周上報不少于十次的行政決策報告,這就需要秘書機構每日不間斷地制作并上報文件;其二,荷蘭中央與地方政府聯系更加緊密,行政信息的上傳下達頻率明顯提高,這與地方自治時期中央行政機構與地方政府的松散管理截然不同,信息流通頻率提高,使秘書機構每日處理的文件數量急劇增加,進而導致文檔登記與管理機構工作量的增加。
三、法國對巴達維亞時期的荷蘭文檔管理實踐的影響
(一)管理工具的植入引發文檔管理的轉型
從“法蘭西一巴達維亞”時期國家部分行政機構與城市依然沿用傳統文檔管理方式的實際情況看,任何一種對文檔管理體制的影響都不是直接的,法國也不例外。可以說法國的文檔管理體制對荷蘭文檔管理的影響是通過“管理工具”的植入而引發管理方式轉型,如登記表,阿姆斯特丹市將登記表引入本市的行政管理機構,直到法國撤退,該登記表仍在管理機構中使用。一旦使用了法國的這種管理工具,它便與當地的傳統方法相結合,使登記的文件以時間順序進行歸檔,這一工作規范被荷蘭國家委員會寫入1823年頒布的公共管理法案中,正式列入荷蘭國家和地方文檔管理的制度。
(二)行政管理體制的變革引發文檔管理機構與人員的變動
法國在荷蘭的統治時間雖短,但法國行政管理體制對荷蘭行政管理機構,特別是地方行政管理機構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第一,新建的政府及其官僚機構通過不斷地要求地方行政官員提供信息來填補其在地方信息獲取方面的空白,而地方機構并沒有擴大提供信息的秘書機構,由此使專司文檔管理的辦事員始終處于高速的文件制作與傳遞的過程中,強化了對信息獲取與文檔管理的能力,使其不斷思考如何提高文檔管理效率,快速找到歸檔文件等問題。這為提出創新性的管理方法與管理經驗的積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第二,在法國殖民政府的影響下,整個19世紀,荷蘭國家政府將管理規范與分派好的任務強加給地方政府,大部分任務都是由公共機構來承擔,而市長和市參議院委員會的工作任務過于繁重,由此導致官僚機構的出現,文檔管理機構逐漸從政府的工作流程中撤出,成為一個獨立的、專門的業務機構。專業文檔管理機構與人員為荷蘭手冊的問題奠定了理論與實踐的雙重基礎。
(三)輕“社會性”制約了荷蘭文檔管理的發展
法國文檔管理體制受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影響,呈現出與傳統荷蘭文檔管理相悖的趨勢。如文檔整理分類過程中,對按主題分類還是按時間分類的爭論,以及文檔登記所用工具的內容繁復程度的設計等,這只是從工具層面對文檔管理的方式與方法的一種“更新換代”。而法國在文檔管理改革過程中所持的“社會化”原則,在荷蘭社會層面并沒有得到普遍發揚。從上述分析來看,“法蘭西一巴達維亞”時期荷蘭的文檔管理改革完全是被動的,是受“行政力量”驅動的,這與法國文檔管理改革的“公眾力量”驅動不同。前者在公共行政體系的干預下完成了文檔管理方法與程序的革新,忽視了社會公眾對文檔管理的訴求與期望,文檔管理工作勢必局限于機關,難以走向社會;后者在社會公眾強烈的需求下完成了文檔管理社會化的轉型,文檔管理不再是機關行政辦公的“應然產物”,而是社會公眾生活的必需品,這在改革的過程中首先被確立下來。由此,筆者認為法國對荷蘭文檔管理體系的影響是不全面的,這與法國對荷蘭殖民統治的需要相關,但從《荷蘭手冊》中的百條條款內容來看,針對文檔社會利用的條款并不多,可見該手冊問世前荷蘭文檔管理的“輕社會性”傾向。
(四)為《荷蘭手冊》的問世奠定了基礎
雖然“尊重全宗”原則在1841年由法國內政部提出,要晚于“法蘭西一巴達維亞”時期法國對荷蘭的控制,但是從法國引入到荷蘭的文檔管理方法與工具分析,法國文檔管理已經開始使用以時間順序、會議名稱字母順序整理文件,并且對機構內部按照主題的分類方法予以棄用,它更加重視來源于同一機構、同一會議或同一地區文件的完整性,這種傾向于機構與會議的分類法正是來源原則的主要內容。1823年國家委員會頒布法案禁止以主題形式進行整理,提出按照文件形成時間和簽發日期順序進行文件整理與分類。該法案一直沿用到20世紀初。可以說從“法蘭西一巴達維亞”時期開始,荷蘭已經受到法國“尊重全宗原則”的影響走上了“來源原則”的實踐之路,而且在成熟而穩定的文檔管理實踐的支撐下,促成了《荷蘭手冊》的誕生,因此法國文檔管理理論與實踐對《荷蘭手冊》的問世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