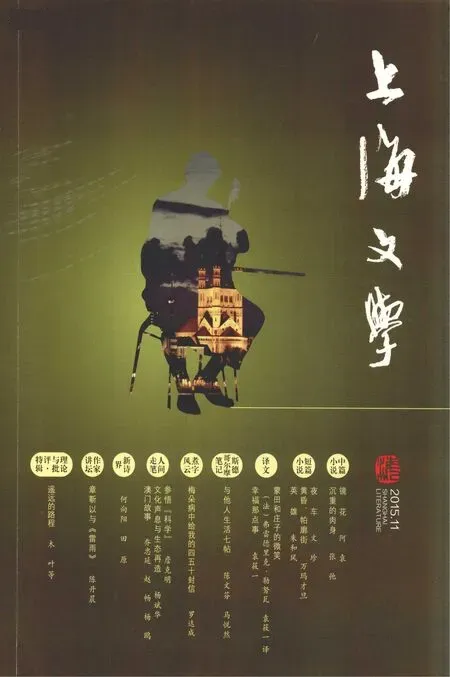章靳以與《雷雨》
陳丹晨
一
曹禺代表作、也是他的第一個劇作《雷雨》發表過程,在文壇一直流傳著多種說法,真可謂眾說紛紜。當事人曹禺、巴金,都談及此事,章靳以的女兒章潔思、巴金的侄子李致都寫過有關文章澄清此事,但另一種誤解又不斷流傳。最近看到曹禺女兒萬方的文章里說道:“當年我爸爸寫出《雷雨》之后,給了他的好朋友、中學同學章靳以。當時章靳以、鄭振鐸和巴金一起在辦《文學季刊》。靳以叔叔把劇本放在抽屜里,放了一年,大約因為我爸爸和他的關系太近了,反而覺得不好講話。我曾問過我爸爸:你為什么不問問呢?他說:‘那時候我真是不在乎,我知道那是好東西,站得住。”(原載《中國新聞周刊》2015年第7期,轉引自《作家文摘》2015年5月22日)類似的話在許多年前,萬方就已經多次在文章中說過。萬方是聽他父親說的,理應也是第一手材料,是可靠準確的。然而事實卻有出入。
我最早聽說此事是在1979年年初。當時我正在為寫作巴金傳記收集材料,知道蕭乾與巴金是多年老友,恰好我的同事唐達成與蕭乾非常熟悉,他們1957年曾在《文藝報》一起工作、一起被打成右派,所以就與他相約去看望蕭乾。那時他們的右派問題還沒有獲得平反。蕭乾住在永定門內天壇南門一個很逼仄的陋室。雖然我是第一次見到他,但他卻像對一個相識多年的熟人一樣隨和,聊了很久。其中談到曹禺的《雷雨》,說:“曹禺寫了《雷雨》劇本后,給了靳以,靳以一直壓著不發。有一天,住在一起的巴金從編輯部辦公桌底下抽屜里發現這部稿子時,已經布滿了灰塵。巴金看了以后很激賞,決定馬上發表。”
蕭乾講這段話時的神情至今我還記得很清晰,感到他對章靳以頗有微詞。后來我從蕭乾寫的有關文章中得悉他在“文革”下放干校田地干活間歇時,還曾對人民文學出版社同事們說過這個段子。事情不知是否從此開始,愈傳愈離譜,甚至有的文章說是巴金從廢紙簍里撿出來才得以發現這部杰作,有的傳記說是從編輯部“積稿”中發現的……
因為蕭乾有這樣的情緒,在他后來寫有關巴金文章時又重復此說,引起巴金極大的不滿。1981年11月巴金在信中嚴辭批評和告誡蕭乾:“你寫文章表揚我卻把靳以掃了一下,這樣對我有什么好處呢?我死了,也難閉上眼睛。因為這不是我的交友之道……”其實早在1979年2月的信中,他就提醒蕭乾在“關于《雷雨》”的文章中“寫出事實就行了”。
那么,當事人巴金又是如何說明此事的呢?就在這封給蕭乾的信中,他說:“事實是,我同靳以談起怎樣把《文學季刊》辦得更好,怎樣組織新的稿件。他說家寶(曹禺原名)寫了一個劇本,放了兩三年了,家寶是他的好朋友,他不好意思推薦他的稿子。我要他把稿子拿來看看。我一口氣在三座門大街十四號的南屋里讀完了《雷雨》,決定發表它。”(參見《巴金全集》第24卷第384頁)其中說“放了兩三年”應是巴老記憶有誤。后來李致在1997年寫的文章中,也是據巴金所說的,內容與此大致相仿,但未再提“放了兩三年”。
曹禺本人多次說過此事。1990年10月說:“那時,我僅僅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無名大學生,是你(指巴金)在那里讀了《雷雨》的稿件,放在抽屜里近一年的稿子,是你看見這個青年還有可為,促使發表這個劇本。你把我介紹進了文藝界,以后每部稿子,都由你看稿、發表,這件事我說了多少遍,然而我說不完,還要說。”(《曹禺全集》第6卷第491頁)他每次說的情況大致如此。與巴金說的不同的是:一、有時,沒有說是章靳以把稿子交給巴金看的。二、放在抽屜里的時間是“近一年”而不是巴金說的“兩三年”。三、所以能發表《雷雨》全歸功于巴金。
以上幾種有關當事人的說法,現在可以就其共同處復原此事的基本面貌是:1933年曹禺寫完了《雷雨》,交給了他的中學同學章靳以。后來在辦《文學季刊》時,靳以給巴金看了,決定發表,刊出在1934年7月出版的《文學季刊》第3期。
二
問題的分歧是在章靳以有沒有延誤、積壓、影響《雷雨》的及時發表。所謂“及時”,最早也只能是1934年1月出版的《文學季刊》創刊號,與實際發表時間7月號充其量也就是相差了半年。
我的看法是不僅沒有,相反的是,章靳以對《雷雨》的發表是與巴金一同起了關鍵的推薦作用的。
現在,我們從曹禺反復說他將《雷雨》稿子交給章靳以“放在抽屜里”一年后才得以發表說起。這里所說的“一年”,如從發表在1934年7月1日倒算回去,曹禺把稿子交給靳以的時間應為1933年7月前后。另外曹禺在1936年1月出版《雷雨》單行本的《序》里,也明確說“現在回憶起三年前提筆的光景……”則應是1933年初。總之,這兩個時間點,《文學季刊》都還沒有成為事實,最多只能算是在議論策劃中。因為曹禺與靳以是中學同學、好友。那時曹禺是清華大學學生,靳以到了北平,兩人重逢后過從甚密,曹禺把稿子交給靳以看,屬于是私人交往的舉動。這段時間就不能算作交給《文學季刊》被放在還沒有成立的編輯部抽屜里積壓不用。
章靳以是在1933年到北平的。他剛從大學畢業不久,已發表過一些作品。有一間書店邀約他編輯一本大型文學雜志,他自覺力量薄弱,想到鄭振鐸這時正在燕京大學任教。他在復旦大學讀書時曾聽過鄭的課,有師生之誼;他還曾投稿給《小說月報》得到發表,主編正是鄭振鐸,因此又有一層編輯與作者的關系。于是就去請求鄭與他一起出任主編。因為,他與鄭畢竟不是深交,鄭是“五四”時期就開始名揚文壇的前輩,以章一個初入文壇的青年作家身份,是帶著忐忑不安毫無把握的心情上門去尋求幫助的。他有一段關于此事的記述:
“一九三三年我到了北京,那時候由于朋友的輾轉介紹,一家書店想約我編一個大型的文學刊物,從經歷和能力來說我都不能勝任,知道他(鄭振鐸)住在燕京大學,就在一天晚上去找他商談。這一次,我們好像老朋友在異地相見,他顯得很熱情;我說出來意,生怕他拒絕,沒想到他一口就應承了。而且爽快地說出來《文學》在上海的處境一天天地困難,有許多文章都被‘檢查老爺抽掉,我們正好開辟一個新的陣地,這個陣地敵人還沒有注意到,可以發揮作用。我們談得很高興,不知不覺就很晚了,卻苦了在門外等我的曹禺和陸申,他們抱怨我說:‘差點凍僵了!后來振鐸知道了這件事,再三怪我為什么不把他們請進去,當時我以為自己還是一個陌生客人,怎好帶去再多的生人!”(《和振鐸相處的日子》)
這段敘述很重要,說明章靳以與鄭振鐸第一次見面商量籌辦《文學季刊》是在一個比較冷的季節,北京一般到陽歷四月乍暖還寒,之前還在烤火取暖季節,所以待在室外時間久了還會感到“凍僵”,則應在三月間或更早。而《文學季刊》進入正式活動是在九十月間。弄清這個時間點,是想證明曹禺不應把稿子給章靳以的時間與投稿刊物混為一談。
《文學季刊》主編是鄭振鐸與章靳以兩位,但因年齡身份不同,章靳以對鄭是尊為師長、前輩,在辦刊方針、指導思想方面會更多尊重鄭的意見。譬如,鄭振鐸除了文學還比較重視文化方面問題,除了創作還比較重視學術論述。這與一般以創作為主的文學刊物還是有所不同。創刊號打頭的欄目就是論文,且有十三篇之多,涉及文學、戲劇、文藝思想、古代文學、外國文學以及語言文字、漢畫、心理學等。這都與鄭的想法有關。鄭振鐸在與魯迅通信中就談到這個構想,得到魯迅的贊同和支持,說:“《季刊》中多關于舊文學之論文,亦很好,此種論文,上海是不會有的,因為非讀書之地。”(1933年10月27日,見《魯迅書信集》[上]第42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可見鄭的意見是起主導作用的。
其次,章靳以還很需仰仗鄭在文藝界的影響爭取著名作家的支持和供稿。魯迅的稿就是鄭寫信邀約來的。1933年10月以編輯部名義在什剎海宴請當時北平的名人作家周作人、朱自清、楊振聲、沈從文等籌劃《文學季刊》創刊。編委會成員有鄭振鐸、章靳以、冰心、朱自清、沉櫻、吳晗、李長之、林庚以及上海的巴金、徐調孚、傅東華等。刊物得到這些名人的支持都與鄭的影響有相當關系。
宴后組稿活動隨之展開,靳以和巴金先后去到周作人、冰心等名人寓所拜訪。冰心記述此次晤面,那是他們初識,說:“記得是在一個初夏的早晨,他(巴金)同靳以一起來看我。那時我們都很年輕,我又比他們大幾歲,便把他們當作小弟弟看待,談起話來都很隨便而自然。靳以很健談,熱情而活潑。巴金就比較沉默,靦腆而稍帶些憂郁……”(《他還在不停地寫作》,引自《冰心著譯選集》[中]第113頁)這里說是初夏,時間有誤,因為巴金是在9月才到北平,因此他們的見面不可能在此之前。除了年紀比巴、章大幾歲(冰心生于1900年、巴金生于1904年、章靳以生于1909年),還因冰心成名早于他們近十年左右,也是有很大影響的前輩作家了,他們對她當然都是很尊重的。從這些活動都可以看到《文學季刊》創刊之初是非常重視著名作家的作品文章的。
所以,作為實際主持刊物工作的主編章靳以和其他編委們一定都在考慮頭幾期特別是創刊號怎么能夠一炮打響,爭取更多的優秀作品,這對于辦刊物的人來說是很自然的做法。因為著名作家在讀者群中有號召力,受到歡迎;一般能夠保持作品的質量,這對創刊之初尤為重要。《文學季刊》第1期十三篇論文,作者有鄭振鐸、黎錦熙、楊丙辰、李健吾、問滔、吳晗、郭昌鶴、賀昌群、李長之、吳文祺、吳世昌、黃源、夏斧心等。第二個欄目是“小說”,有老舍的《黑白李》、余一(巴金化名)的《將軍》、吳組緗的《一千八百擔》、冰心的《冬兒姑娘》、叔文的《黃家的二小》、沉櫻的《舊雨》、蹇先艾的《血泡粑的典禮》、靳以的《凜寒中》、李素的《容的一生》等九篇,其中前三篇后來都成了文學史上的名篇。吳組緗是曹禺在清華的同學,接著在第2期又有新作《樊家鋪子》。其他欄目還有詩歌、散文,此處從略不贅。可以看到名家陣容確實很豪華。這說明章靳以和編委們選稿的考量是努力追求刊物的質量和影響。當時的曹禺還是一位剛畢業的大學生,還沒有發表過作品的文學青年,靳以與他又是把兄弟,沒有把十幾萬字的《雷雨》推薦編入創刊號,也是可以理解而正常的事。
事實上,許多青年作者的創作也得到靳以、巴金的相當重視。如北大的何其芳、卞之琳、李廣田,清華的林庚、吳組緗、吳晗、李長之,燕大的蕭乾,以及有些默默無聞的文學青年都成了《文學季刊》的作者,有的還是編委,他們中的許多人的文學生涯是從此起步的。所以從靳以來說,更不可能對身邊的曹禺有所忽視。
巴金是在1933年9月到北平的,初期寄住在府右街達子營沈從文家里。據他說,住了兩三個月,后來還臨時回過一次上海。《文學季刊》創辦后,靳以租了三座門大街十四號房子作為編輯部辦公室和他的住所,這應是宴請作家們之后的事了,也即那年10月以后。所以巴金搬到編輯部與靳以同住,應是1934年初。巴金曾說:“我常常想起一九三四年上半年在北平的生活,當時我們都住在三座門大街十四號北屋,每人一個小房間,中間一間大的辦公室,靳以和我坐在一張大寫字臺的兩面,我們看校樣,看稿件,也寫信,寫文章……”(《隨想錄·〈靳以選集〉序》)他們經常在一起討論如何把刊物辦得更好,發表更多的優秀作品。這時,靳以就說:家寶有個劇本在我這里。他把《雷雨》交給了巴金,巴金看了非常激動,與靳以一起決定立即發表。按照季刊三個月的出版周期,他們應正在選編第三期的稿子,破例一次刊登完這部劇作。所以說“破例”,當時有些篇幅長的稿子一般就分幾期登完。像巴金的《愛情三部曲》的第三部《電》(發表時篇名改為《龍眼花開的時候》,作者署名為歐陽鏡蓉)約十萬字就是從第2期開始分上下兩次登完的。
當時一些師友與章靳以相處都有很好的印象。沈從文說他“那時還極年輕,為人特別坦率,重友情,是非愛憎分明,既反映到他個人充滿青春活力的作品中,也同時反映到他編輯刊物團結作家的工作里”。(《悼靳以》)冰心則說:那時“你是一個多么熱情,多么正直,又是一個多么淳厚的青年啊!”(《關于男人·悼靳以》)巴金說“他正直善良,熱愛生活,他把他心靈中美好的事物完全獻給祖國的文藝事業”。(《再思錄·我永遠忘不了他》)這些品格當然也表現在他對曹禺作品的處理上,也是很盡心的。何況他與曹禺是發小,靳以的女兒記述說:“無論課余假日,曹禺總喜歡待在我的父親家中。他好似天津昆緯路我們老章家的一員。在這個充滿明朗氣氛、有六個兄弟加上表兄弟簇擁的大家庭里,曹禺找到了自己少年時代的快樂。他與父親換帖成了把兄弟,父親與他情同手足……”(章潔思:《曲終人未散·〈雷雨〉前后》)這樣的友情非同一般。現在,章靳以早一步進入文壇,就熱心介紹曹禺認識鄭振鐸,認識巴金,那時曹禺、蕭乾、李健吾等都是《季刊》的常客,經常到編輯部歇息、聊天,結伴外出游覽、聽戲;曹禺很快與巴金熟識。無論從哪方面說,章靳以都不可能故意把曹禺的作品放在抽屜里雪藏起來。
巴金曾說,靳以曾把《雷雨》給編委李健吾看過,李認為寫得比較亂。靳以就不敢用了。但是,《季刊》公布的編委名單里并沒有李的名字。當然這并不意味著靳以沒有征求過李健吾的意見。李健吾那時從法國留學回來,之前他就已出版過小說等作品,這時著重研究戲劇、創作劇作、寫評論,與《文學季刊》關系很密切。他的哥哥李卓吾也是無政府主義者,是巴金的老朋友。所以靳以想多征求一些行家的意見也屬常理。這可備一說。還有李長之因為對稿件刊用等一些事不滿意,后來為此鬧意氣退出編委。諸如此類的人事也都從某個側面說明作為主編的靳以所處的環境,需要考慮的方方面面。
所以,《雷雨》之沒有在《季刊》創刊號刊出,試想,一個還沒有發表過作品的青年的大部頭著作去充當打頭陣的角色,章靳以礙于老同學的關系不便提出這樣的設想也就完全可以理解。再試想,去見鄭振鐸時,曹禺連門都不好意思直接闖入呢!但是,當巴金談起怎樣辦好刊物時,章靳以還是不失時機地把《雷雨》推薦給了巴金看。那時巴金已是負有盛名的當紅作家,又是本刊編委,住在編輯部與靳以一起工作,他們意氣相投,互相尊重,成為終身的好友。巴金的意見就更有分量,靳以當然欣然同意。曹禺前期的作品《雷雨》(《文學季刊》一次登完)、《日出》(《文季月刊》從創刊號開始連載四期)、《原野》(《文叢》第2期開始連載四期)等都是由巴金、靳以或靳以單個主編的刊物最先發表的。巴金就說:“從《雷雨》起我就是他的作品的最初的讀者,他的每一本戲都是經過我和另一個朋友的手送到讀者面前的。(他相信我們,如人相信他的真實的朋友。)”(《〈蛻變〉后記》)這另一個朋友就是章靳以,他們對曹禺及其作品是滿懷著友誼和熱情的。所以,應該說是巴金和靳以一起把曹禺送進了文壇。這才是歷史事實。就像巴金一直認為鄭振鐸、葉圣陶兩位前輩作家先后都是最早發表他的詩歌或小說的前輩編輯,是他們“把我送進了文藝界”(《再思錄·懷念振鐸》)一樣,所以他一直懷著感恩之心。
1937年,章靳以在他主編的《文叢》創刊號上撰寫廣告詞,稱:“《雷雨》是曹禺先生的第一部劇作,發表以來,轟動一時,各地競相排演,開未有之盛況。兩年以來,《雷雨》支持了整個中國的話劇舞臺。我們可以說,中國舞臺,是在有了《雷雨》以后才有自己的腳本……”這樣高度的評語再一次可見他對《雷雨》的真誠和熱情。
章靳以是現代文學史上一位卓有成就的優秀作家,不僅留下豐碩的作品,還曾致力于大學文學教學,桃李盈門。他創辦并主編了許多有深遠影響的文學刊物《文學季刊》、《文季月刊》、《文叢》、《現代文藝》、《收獲》等等,在他一生的文學生涯中占有極重要的位置,自始至終幾乎未曾間斷過,一直堅持到最后倒在編輯崗位上,所作的杰出貢獻足以為文學編輯人的師表和典范。他為曹禺作品的發表出版所作的努力不過是其中之一例而已。
三
曹禺對巴金、章靳以懷著感激之心。1936年出版的《雷雨》單行本的《序》末了,他說:“不過這個本頭已和原來的不同,許多小地方都有些改動,這些地方我應該感謝穎如,和我的友人文慧(謝謝他的友情,他在病中還替我細心校對和改正)、孝曾、方序,他們督催著我,鼓勵著我,使《雷雨》才有現在模樣……”1937年出版的《日出·跋》最后說:“我愿意把這個戲獻給我的朋友巴金、靳以、孝曾。”這里的“文慧”是巴金,“方序”是章靳以;陸孝曾是曹禺的同學陸以洪的侄子,那時幫著做了許多輔助的工作。那些年曹禺對自己的處女作發表并得到轟動效應,譽滿天下,有人讀,有人演,心情自屬歡悅欣喜,帶著女友鄭秀,與巴金、靳以等經常歡聚聽戲、餐飲,沒有資料說及他對發表的時間早晚有什么抱怨和異議。1935年復旦劇社排演《雷雨》,復旦大學教授趙景深函請曹禺為此題字。曹禺嫌自己的字寫得不好,就請靳以代筆冒名頂替,趙當時沒有發現還回信說:“你和靳以真是好朋友,連字也像他。”這個小插曲也從側面說明那時他們哥兒倆是多么要好到不分你我。
即使到了晚年,他還說:“靳以也許覺得我和他太近了,為了避嫌,把我的劇本暫時放在抽屜里。過了一段時間,他偶然對巴金談起,巴金從抽屜中翻出這個劇本,看完之后,主張馬上發表,靳以當然欣然同意。”(《簡談《雷雨》,見《收獲》1979年第2期)這與巴金說的差不多了。但是同年,曹禺在對記者訪談時又說:“(把稿子)交給了一個同學,那個同學把它擱在抽屜里,擱了一個時期,有個人發現了這篇稿件,讀了一遍,就拿去發表了。”(《徐開壘散文選·舞臺背后》第312頁)他的女兒萬方在之后許多年里多次記述他的話,也都是這樣說的,而且明確說是靳以把稿“放在抽屜里,放了一年”,有時甚至說“沒有看,也沒有提起過”。萬方問曹禺:“你為什么不問問呢?”他說:“那時候我真是不在乎,我知道那是好東西,站得住。”(原載《中國新聞周刊》2015年第7期)萬方引述這些話是想證明他父親“年輕時真是非常的自信。這是一種多么大的幸福”。
《雷雨》成了中國近代話劇史上的里程碑,傳世的經典;曹禺晚年對自己的作品也更倍加珍惜之余,為它沒有得到更早的發表,對靳以不免有遺憾之情。其實,他沒有辦刊物的經驗,對編輯工作的甘苦也不太了解,對他的把兄弟曾為他盡心因為年代久遠而有所疏忽。我個人曾有幸接觸過許多前輩名人作家,他們的作品中的大氣卓識都給人深刻印象,但有時對于幾十年前的某些具體細節記憶不一定那么準確,或為此糾結在心而放不下。這種情況在有的老年人來說,也是常事。
至于蕭乾那時是燕京大學學生,也是《文學季刊》作者,常到編輯部走動,與巴金、靳以等都熟悉。但他不是此事的當事人,所傳明顯不實,不足為憑;巴金在通信中就批評了他,同時指出原因是他與靳以私人之間有點過節。但因此造成訛傳甚廣。蕭乾后來文章雖按巴金所說而寫,他強調了巴金的謙遜。其實還是應更看重巴金的講真話、尊重事實的精神。另外,在我寫的一篇關于巴金與蕭乾的文章中也因提到此事,蕭乾夫人文潔若大姐就在我文后附言說:“看了此文方曉得,他對蕭乾的了解,比我想像的深多了。蕭乾認為,在復旦任教時期,倘非章靳以帶著某種情緒對他講郭沫若被稱作郭老,茅盾被稱作茅公,他不會那樣來寫那篇文章(用錢鍾書的話來說:‘蕭乾盛年時過于鋒芒畢露。)所以介紹情況時,是戴著有色眼鏡來看靳以的……”(《博覽群書》2006年第7期)至此,事實就更清楚了。
我想,我們研究或談論歷史時,特別應該注意細節的真實;歷史事件無論多重大,總是由許多細節組成的;細節失實,往往全盤受影響。例如這件《雷雨》發表過程的公案,問題也是出自細節的不真實,有時經過渲染夸大的細節往往更引起人們興趣而易傳播,但卻扭曲了真相。現在,有關當事人都已作古,無法再對此說什么。本文盡可能從多方面求證,對此事作了詳細的梳理,特別注意細節的復原,澄清事件的本來面目,希望此后能不再訛誤流傳。不知是否做到,敬請讀者鑒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