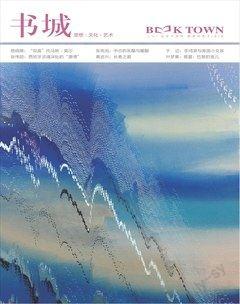“司名器者之蠹國自利”(下)
陸建德

段祺瑞政府財政總長李思浩(1882-1968)
三
章士釗曾經上書段祺瑞,檢舉金案。他不敢揭發為法國謀利益的涉案人士,名義上是“自劾”,即自請查辦。民國年間沒有秘密可言,章士釗身為部長,沒有人身安全,此舉有很大風險。呈文段祺瑞的時間,據他自己回憶是在一九二五年六七月間。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約在四月上旬,財政總長李思浩在國務會議上聲稱,因有某公民為金法郎案控告經手大員,現在中法協定已修改完畢,呈請段祺瑞將協定交付司法部審查。必須說明,李思浩通過段祺瑞轉司法部審查的是中法協定的條文,他并不是想請司法部就指控是否屬實展開司法調查(這應在檢察廳職權之內)。結果中法協定全文就到了章士釗手中,經復核后再呈段祺瑞。為什么需要這一手續?章士釗是否在國務會議上流露出對協定有所保留的意思?財政部不是司法部的下屬,請司法部審查中法協定,是為了防止差錯,請專家把關,還是拉司法部共同承擔責任?是出于謹慎,還是計謀?筆者以為李思浩未必有惡意,但是章士釗就此變成了審批金案的國務員之一,從后果而言,于他非常不利—他送給既有或潛在的對手一張打擊他的王牌。這個月十四日,章士釗兼署教育總長,教育界有的派系為此不快,再說他的一些舉措立即引起爭議。而且,教育部此刻又走向中法教育基金委員會的對立面:法國退還款中用于教育的部分,教育部是否有權力動用?假如李石曾需要掃除“異己”,那么章士釗自然名列首位。就在這段時期,關于他得賄的流言紛起。章士釗在呈文中自謂:
倘彼時釗以事非主管,諉而不為,此誠滑吏之恒情,而士釗則以為與輔佐執政,協恭同寅之義未合,硁硁愚忠,罔識其他。此中法協定全文由本部核復之大概情形也。詎料協定公布之后,浮議漸起,謂此案為利藪所在,通國皆知,司法部不應無所圖利,而漫干預職權以外之事,是必與財政部狼狽為奸,朋分贓款,于是言本部分五十萬者有之,分三十萬者有之,至十余數萬萬元亦有之……蛇市虎,道路競傳。
章士釗不能默認,故而“以法自繩”,希望總檢察廳檢察長查閱有關賬目,并且調查金案受賄流言。他還要求“將此呈發與財政總長李思浩閱看,以資接洽”。李思浩和他的朋友們讀到這篇呈文,很不舒服,因為章士釗自信清白,“自劾”的真正動機是要求政府查辦其他涉案人物。章士釗身為司法總長,有此請求,其意義就非路人可比,必為金案私下得利者痛恨。
幾個月過去了,調查取得進展。《甲寅周刊》(第1卷第13號,1925年10月10日)“時評”欄刊出“質”的短文,章士釗別名“民質”,應該是他的手筆。質還有質問的意思:
本年七月,前法長章君,因金法郎謠諑紛紜,詞連司法部及章君本人,以謂該部審查是案,所下穩妥無疵四字,乃重金買來,而重金又悉為章君流用,未入部賬等語。章君當即呈請執政,自行檢舉,結果由總檢察廳依法辦理。承辦者檢察官翁敬棠即為一人,此案情也。事逾數月,該檢察官于檢查財法兩部出入簿記,及北京各銀行有無與章君往來賬目,及其存支之數如何。曾一一應有盡有而鉤稽之,然迄無一字呈報。本案中章君是否受賄之重要節目,世莫得知。數日前,該檢察官忽分呈司法總長及總檢察長,將論點完全變更,置章君受賄一節不問,而盡情攻擊外、財兩長,援引刑律第一百八條之外患罪,指為有故意不利中華民國之行為。全篇論調,純是政治意味,與新聞論說相同。且于遞呈之先,陰將眷屬移往天津,呈發而己亦隨往,顯有情虛畏罪之跡。夫在昔中人之主,不戮諫官;共和自由之邦,寧傷檢吏?如此虛怯,其別有情節可知。且“不利”之云,焉有不移界說?所謂“故意”,周內抑又何難?政爭陰謀,人至傀儡法吏以逞其志。君子不禁為司法獨立痛惜也已!
此文的語氣筆調,很值得玩味。“置章君受賄一節不問”,是不是意味著流言不值一提?但是章士釗希望翁敬棠說清楚,不說等于自己還是懷疑對象。檢察官“情虛畏罪”,移居天津,也可能擔心北京不安全,有可能招致報復。“諫官檢吏”如此虛怯,究其原因,不外政府內部有派系之爭,外有不歸執政府指揮的警備司令部,以致法吏沒有權威,躲來躲去。《甲寅周刊》這篇時評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北京失治的形象寫照。

調查“金法郎案”的檢察官翁敬棠(1884-1956)
翁敬棠對金案提出檢舉是在十月三日,認為外長沈瑞麟、財長李思浩應為損失國庫八千萬元負責。時評短文應該作于此后兩三天之內。但是事態的發展立即對章士釗不利:“翁敬棠為本身安全起見,即日離京赴津,七日又在天津再提出檢舉章士釗,謂其在司法總長任內,對金案有共犯嫌疑。……北京政府司法部一面于十月十七日訓令京師高等檢察廳依法辦理,一面于十二月三日,準李思浩辭職。十五年三月六日,北京高等檢察廳宣告金案不予起訴。此案表面上是法律問題,而實際則是私爭、政爭。翁敬棠受人運動,亦系難免。”李思浩辭職后,繼其位的是孫中山南京臨時政府時的財長陳錦濤。章士釗還想政府出來主持公道,又致書新任財長談金案,敦促查明案中的貪瀆。此信亦在《甲寅周刊》(第1卷第23號,1925年12月13日)刊出。
查此案之原委,弟不甚明。就中損失國庫之至何度?理財非弟專司,亦莫能言。其終展轉出于必辦之一途,尤非弟所決策,惟政府以為必辦矣。據財政總長之閣席報告,依常識之所能至,認為利多而害少,則既同僚為國務員,無拒不負責理,交法部審查者,亦共同負責形式之別見者耳。以政情言,固未見不審查則責輕,審查而責特重也。世人不解此意,亦即不必覙縷,此而獲罪,弟固無說。
段祺瑞政府已經決定必須與法國簽約(“必辦”),司法部只是貫徹上峰的精神,辦或不辦,并無責任輕重之分。接下來章士釗再提社會上關于他分贓的流言(巨額贓款從三萬到三十萬不等),發誓只要有“一文之茍”就情愿伏法。下面他以“大言欺世”的“文士”暗指以金案自肥的陰謀家:
弟謂贓不問大小,有贓必辦。若云弟乎,微論大數如前所舉也,只須有一文之茍,仰即論殺無赦。他犯尚許以情節之重輕,量為進退。何也?以弟文士,號識理道,臧否人倫,平日不惜以大言欺世,其罪自應加人一等也。今夏六月間,弟曾自行舉發,由執政批交總檢察廳,如法偵查,該廳迄無所公布。今兄長部,凡金法郎案之真實利弊如何?積存關余一千零三十萬之支用如何?一年間部賬出入之可以舞弊者如何?以及中法實業銀行遠東存戶之實況如何?皆有權一一勾稽而布達之。

中法實業銀行1914年在天津發行的10元紙幣

中法實業銀行上海分行
章士釗貌似維護自己的名譽,其實是指像他那樣的“文士”賣國得賄,應該罪加一等。引文中四個問題,希望財政部認真查賬答復,也給今天對金案感興趣的人士留下了幾條追查的線索。此信最后表示了雅量(如指控不實,說明有人服務社會,無所圖利,可以勸善),也堅持原則:確有其事,查清弊案,“罪人斯得,邦有常刑,而于貌襲清剛,陰貪大賂,視天下為無物,以是非為市如不肖者,嚴加懲創,以正士風,不失為孔子誅少正卯之意”。“貌襲清剛,陰貪大賂”這一連串嚴厲的文辭讓讀者回想到向紹軒八月份致《甲寅周刊》來信中對“虛士”“陰謀家”的譴責。少正卯是魯國聞人,興辦私學,鼓吹邪說,教育界深受其害。筆者忍不住想說,金案經手大員既為政府高官,就談不上清譽。李石曾創立進德會,發誓不做官吏,不做議員,“貌襲清剛”。少正卯非他,李石曾是也。陳錦濤先是接替李思浩,后進入許世英內閣,還是任財政總長,但是他總共任職半個多月就請假而去,獲準。當時的政府根本無力徹查這樣的大案,更何況中法簽約也有財政上的好處(法國的選項之一是不退還庚款)。國民黨政府要比北洋政府強大得多,即便是蔣經國也不能懲辦巨貪,說明貪腐幾乎與國家機器共生,難以根絕。
章士釗整頓學風,清理各校財務積欠,李石曾是反對的。章士釗的《剏設教授院議》(1925年11月21日)里有一段文字頗有影射李石曾假借“愛國”大義“蠹國自利”的意思:“今天下淫侈之習,亦云至矣。司名器者之蠹國自利,無可諱矣。軍旅濫興,賦稅日亂,黃金之擲于虛牝者,不可計矣。而惟廣文先生(杜甫《醉時歌》:‘廣文先生飯不足),以飯不足聞,此其不平之念,久蘊于胸,遂乃消極拒斥政府整飭之良計,如愚擬清理八校積欠,按實核發,李君石曾即抗言為何不核軍費,而獨核學費。積極浮慕愛國運動之佳名。湯君爾和為言曾在某報見一論文題曰:‘大學教授之責任何在,署名者,為北大教授某君。余因亟取讀之,得知彼所謂責任,乃說卸長衫領導學生赴天安門開會,遇有軍警干涉,即與奮斗,余大失望。政潮侵入學林,而大學地位杌隉不安,日見其甚。”李石曾財源滾滾,章士釗以他比“廣文先生”,顯然是用了反諷的筆法來刺激他。李石曾不愿意教育部出面清理積欠,按實核發,因為這一行動可能導致清查基金會的賬目,侵犯到他的領地。李石曾對一個較為強勢的教育部,非常注意防范。
《剏設教授院議》作者如此行文(刊載于《甲寅周刊》第1卷第19號),已忘記這一年五月自己魏家胡同的寓所曾經被毀。十一月二十八日,暴徒又來。將《寒家再毀記》一文(《甲寅周刊》第1卷第21號,1925年11月30日)置于金案背景下再讀,不免嘆息。章士釗寫道:“愚近以審查金法郎案有贓名,意家中宜有與贓相應者若干事,而乃無有。……前以金法郎受賄嫌疑,愚自請查辦,以是此項出入簿記(銀行借款記錄)俱已為總檢察廳所得。……至金案云者,愚以閣議通過交部審查之件,深自縛于國務一體共同負責之中,未嘗拒之,此而有罪,乃所甘受。惟謂審查此案,除圖利他人伙同受賄以外,不能有他種較可公開為國服務之動機,此則嫌微之地,別明至艱。愚既信望未孚,無從以此動機征信于人,使其渙然,亦惟自咎以待天下之公裁,期于水落石出而已,不敢多所論議也。日來政變突生,北京漸入恐怖時期,人無法自障,國務員賤如狗。愚所愿道,竟無人假我紙墨,舂容寫出,亦未可知。愚懼久之真相不明,諸兒橫被指目,曰:‘此其父乃自鬻于某案者也。或且無以為人,故并自狀于此。”魯迅在《雜論管閑事·做學問·灰色等》一文笑話章士釗藏書之多,不提金案。

李石曾(右)、吳稚暉(左)與張靜江,他們和蔡元培被并稱為國民黨四大元老
四
法國為金案對財務危機中不能自拔的中國政府威逼利誘,后者幾乎不得不從。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華盛頓會議簽訂《九國關于中國事件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通稱《九國公約》),根據這份條約,中國的主權將得到尊重,關稅將提高到百分之五,關稅自主權將恢復。但是首先相關國家必須舉行關稅會議,八國已經批準,唯獨法國揚言,中國拒絕付金,法國國會就不會批準華盛頓協定。這樣中國政府急盼的關稅收入就無法到手。而且法國動用了強大的外交資源,得到日美等國支持,中國政府不合作,扣留在總稅務司安格聯手中的海關關余、鹽余就不能進入國庫。綜合起來考量,財政上已經焦頭爛額的中國政府根本不具備討價還價的實力。
但是這一過程中,中方上層人士為法國打通關節,甚至“蠹國自利”,也是事實。顏惠慶在自傳中講到一件事:“有關本案緣由,至今有件趣聞不曾公開,現披露給讀者。有位著名中國政客,曾為法方要求的實現而賣力,一日來訪,談論主題時,他信口許諾,倘若我能促成此案,可以收到五十萬美元的酬金。我笑而答之,感謝盛情,并稱部中正缺支付駐外使館的經費,我將愉快地用此傭金救急。該來訪者從此不再提及此事。”這位“政客”應該有一定的隱蔽性,不大可能是王克敏、李思浩(兩人均在1922年之前擔任過中國銀行總裁和財長,王克敏兼中法實業銀行中方總裁,1913年曾訪問法國)等直接與此案相關的經手大員。顏惠慶當時為總理兼外交總長,這個月二十七日,他辭去外長兼職,三十一日又請假出京,內閣改組。為法國利益向本國官員行賄,已經觸犯刑律,但是在中國,顏惠慶甚至不敢點他的名字。政治生態之惡劣,竟至于此。中法談判結束后,金案不斷發酵,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的群眾示威活動中,金案又變成打擊段祺瑞執政府的武器。最直接的金案得益者中法教育基金委員會卻安然無恙。李石曾摘了桃子,又讓桃樹上枝條的猛力反彈,抽到他對手的臉上,留下難看的紅腫。這樣高明的手段,必須記述下來,以防遺忘。
另有一個細節應該與讀者分享。用庚款退還款恢復中法實業銀行,關鍵是發行五厘美金債票,換回該行倒閉時發給債權人用以抵債的無利債券。中法協定達成前可能會有行賄受賄行為,在履行相關條款的過程中,依然會有種種違法的動作,“蠹國自利”之門依然洞開。一九二七年四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金案還有不小的余波。據葛夫平研究比較:
在無利債券的交涉中,北京政府在維護國家利益方面要勝于南京政府。南京國民政府沒有堅持一九二五年中法協定規定中國應享之權益,也沒有堅守北京政府在與法方進行無利債券談判中所取得的有利地位,而是輕率地同意“中法教育基金委員會”代替“中國政府”成為無利債券的所有者和中法實業銀行的債權人。這是一個嚴重的失策。因為中法教育基金委員會不是一個由中國獨立管理的機構,它由中法雙方共同組織,在表決時雙方各有一權,經費各支配一半,而實權則操縱在退款國法國駐華公使之手。因此,以無利債券受益者中法教育基金委員會取代無利債券所有者中國政府,成為中法實業銀行的債權人,這就使中國方面失去了對該債權的控制權和管理權。不但如此,它還導致了無利債券最后不能切實收回。(《中法庚款案中的無利債券問題》,《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
筆者深信,以李石曾的精明能干,這是有意為之,并非“嚴重的失策”。一九二八年春,李石曾到法國為尚未得到國際承認的南京政府推動外交,儼然有中國駐法大使的氣勢。這時他在國民黨內處于權力的頂峰,在南京,吳稚暉、易培基等人正在為他統管華北政治和教育界籌劃。除了大的外交方針,他肯定會與法國政界人士討論中法教育基金委員會的工作(一度受到三一八以后北京政府的干擾)和如何收回上述無利債券等事宜。他既是國民政府的使者,又可以全權代表中法教育基金委員會,沒有權界。他與法方達成的默契或交易是否影響到后來國民政府的決策?這是有待調查的。過了兩年,他在國內教育界權力之爭中落了下風,中法教育基金委員會依然逃不出他的手心—不管中方主席為誰。“故宮盜寶案”傷害到李石曾的公信力,他的左右手蕭瑜也吸引了太多輿論的關注,于一九三四年再赴法國,到普瓦捷大學攻讀,一九三八年回到香港。一九三六年,南京國民政府監察院調查中法教育基金委員會,賬目的混亂讓人震駭。李石曾本人則在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前不久遠赴法國出席某個文化上的會議,在法國一住就是四年,一九四一年短暫訪問重慶、昆明,后又遷往更安全的美國做寓公。抗戰八年,他基本上全在國外,這是一位世界主義者合理的選擇。
章士釗抗戰時的經歷,此處不談。一九四五年秋,李石曾從美國回到上海。一九四七年二月二日,他在林森路(二戰結束前稱霞飛路,現淮海路)的世界社會所(現淮海中路1800號)舉辦他與林素珊的婚禮,章士釗出席祝賀。與不久前那場慘烈的戰爭相比,還有什么前嫌不能拋棄?至于后人,還不能放棄自己的獨立判斷。
[附錄] 庚子賠款各國分配率
庚子賠款共計關平銀四億五千萬兩,三十九年還清,年息四分,本息合計近十億兩(982238150.05兩)。各國分配率以俄國最高,正本數一億三千萬兩,本息總計近二億八千五百萬兩。其余受賠國在賠款總量中所占比重分別是:德國20.02%,法國15.75%,英國11.25%,日本7.73%,美國7.32%,意大利5.92%,比利時1.89%,奧匈帝國0.89%,荷蘭0.17%,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和挪威四國加起來僅0.06%。賠款中另有“雜項”,比重為0.03%。一九一七年八月中國對德國和奧匈帝國宣戰,中止對兩國的賠付。這樣法國份額僅次于俄國,超出美國的兩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