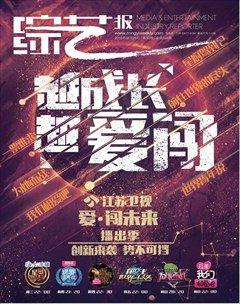《旋風九日》 歷史揭秘紀錄電影
戈凹

在《旋風九日》眾多宣傳中,我們很難看到“紀錄片”的字樣,轉而以“歷史揭秘電影”這樣的說法冠之,折射出片方的微妙心理——在蓬勃增長的電影市場中,紀錄電影甚至連邊緣都算不上,幾乎成為“棄嬰”。
縱觀全球,紀錄片固然從來沒有成為過電影市場的主菜,但也不乏引爆觀影熱潮的大作。美國“刺頭兒”導演邁克爾·摩爾幾番制造出票房大賣的話題之作《科倫拜恩的保齡》《華氏911》;法國的雅克·貝漢及其團隊不斷以《遷徙的鳥》《微觀世界》和《海洋》發現自然真實的影像奇觀;韓國從《牛鈴之聲》到《親愛的,不要跨過那條江》接連沖到年度票房榜前列;就連臺灣地區,也出現過《看見臺灣》這樣票房超過2億新臺幣的口碑之作。
中國大陸的情形也在悄悄發生變化。自從央視紀錄片頻道開播以及《舌尖上的中國》之類紀錄片大熱,紀錄片市場的回暖與升溫都是可見的。但是要試圖改變觀眾只在電視上觀看紀錄片的慣性思維,嘗試進入影院欣賞,依然是需要逾越的一大關隘。可喜的是,敢于吃螃蟹的越來越多。去年以來,被官方劃歸為“紀錄電影”范疇的《爸爸去哪兒》《奔跑吧,兄弟》動輒收獲數億票房,卻也引發爭議。嚴格來講,這些由熱播電視欄目衍生而來的電影形態與電視欄目并無二致,最多算作“真人秀電影”或“綜藝電影”,不能視為嚴格意義上的紀錄片,但它們的票房表現多少證明了“真實”并非沒有市場,對于亟待市場破冰的紀錄電影來說具啟發和鼓舞性。
更具參照意義的是以《歸途列車》《小人國》《飛魚秀》《鄉村里的中國》等作品為代表的一系列嘗試,尤其是范立欣,這位曾獲得艾美獎的導演堪稱是國內目前最具國際視野、并熟稔主流商業紀錄片模式的紀錄片制作人。他一年一步走,執導的《歸途列車》曾嘗試在北京MOMA藝術影院做長線放映,后以“一城一映”的形式推廣至若干城市;擔綱監制的《千錘百煉》也曾以超過200家影院的規模在全國公映,雖然票房反響均不盡如人意,但為紀錄電影的市場推廣積累了彌足珍貴的經驗。2014年暑期,批著一層“粉絲電影”的薄紗,范立欣的《我就是我》以全然的商業電影操作模式推向市場。這部電影通過紀錄2013年“快男”選秀,完成對中國電視選秀十年歷程的總結陳辭,并嘗試以此為窗口進入90后的心靈世界,最終差強人意地獲得接近700萬元票房,幾乎可以看做是對當下國產紀錄電影行情的摸底。
說回《旋風九日》。嚴肅的政治題材,卻規避掉正襟危坐的宏大敘事形態;聚焦重大歷史事件,也特別注重從歷史的細微之處挖掘不一樣的新意。不論是在國內首次引入漫畫手法描摹領袖人物、還是以快速剪輯營造高強度視聽節奏,出身新影的導演傅紅星都在自覺地與新影風格形成區別。加之邀來跨越政界、商界、文化界多位巨擘大佬的集體吆喝,都毫不掩飾本片對于市場和觀眾的強烈渴望。
1979年,鄧小平為期九天的訪美帶來了中美關系的破冰。2015年春夏之交,在《復仇者聯盟2》的強大攻勢下,這部《旋風九日》似乎也擔當起為紀錄電影破冰的歷史重任。不論最終結果如何,種種跡象表明,紀錄電影正在積蓄力量,準備假以時日成為電影市場不被忽略的別樣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