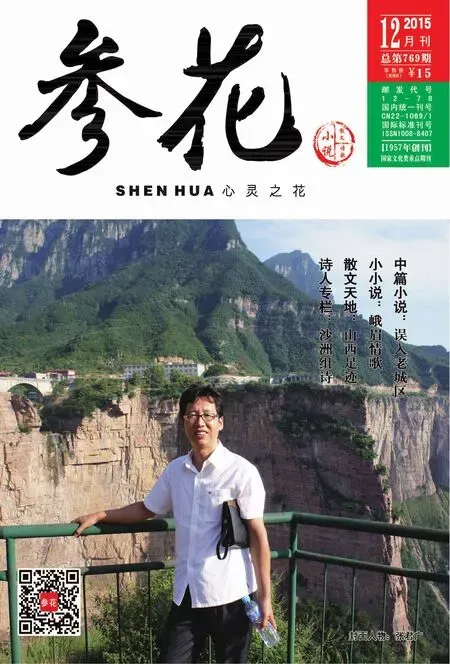我這條路
劉澤禹
鄰村的張光明死了,五十五歲。
張光明賣肉。家住在村頭,每天都在自家院子里哐嘰哐嘰地剁骨頭,晌午不到就推著個車子來村里頭賣。大家都不愛買他的肉,因為老缺斤少兩,總能聽見別人罵“真他媽狗娘養的,買了一斤肉就吃了兩天,他要是沒加水我倒過來爬”。罵完沒過幾天還要買,因為除了他沒有賣的。
張光明從十幾歲就開始做賣肉的營生,一直到快四十了還沒有找上媳婦,媒婆著急得不行,他自己倒不急。鄰里百家都奇怪他到底在干什么,“一天到頭都在看‘大辭典”,就這樣傳開了。
所謂的“大辭典”就是新華大字典,張光明城里的二叔給他的,叫他學認字。他也是真的聰明,學了沒一陣子就開始看《紅樓夢》了。在城里上學的王冬瓜,在街上看見張光明,大老遠就喊“賈寶玉還沒找著俺那林黛玉喲”,末了的“喲”還加一個拐。坐在陰涼處的女人就咯咯咯地笑起來,好像她們聽得懂什么意思一樣。
張光明也不說什么,只顧走自己的路,大家都無趣,漸漸也無人再取笑。他的生意一天天好起來,對于他在肉里摻水,大家習慣后也少了些抱怨。畢竟村里喜歡不吭聲的人。
后來這個小村,就發生了一件對村民來說天大的事。村長的豬被人偷了。
于是柳樹蔭下、麥子地里、水井旁邊、山坡頭上,人人都在猜是誰做的。
“說不定是李二喜,村長那天剛占了他家的一塊韭菜地。”
“二喜老實,沒準是他爹。”
“說不定是王花呢,她不想嫁村長他外甥你們又不是不知道……”
“嘁,女人家還是不敢,我倒想是莊光頭,他恨村長不讓他拉走茅房的糞。”
結果還沒待到結果,村里就又炸了鍋。
殺豬的張光明娶媳婦了。
幾天前張光明上城里找他二叔,“俺只是尋思著再借本書看,”張光明坐在炕上說,“該就是命里寫著的。”聽到這,把頭湊在一起聽的女人們咯咯地笑起來。
“哎喲,妹妹看起來可頂年輕,芳齡多少啊?”村長老婆撇著腔調問,一臉皺紋摺出的假笑。
“二十。”
屋里的笑一下子停了。女人們互相交換了眼神,說不出一句接的話來,全看向村長老婆。
村長老婆咽了口唾沫,“你們城里人時髦,以后可別嫌棄我們鄉下人。我這地里還有點活沒干,就先走了。”一眾女人便嗯嗯呀呀地都隨著走了。
一走出欄柵,“我說呢,那女人看著頂年輕,原來才二十,殺豬那玩意看著老實,其實是老實拐古。”
“我倒看是那女的狐媚殷勤,要不年紀輕輕嫁來這地兒干啥。定是有圖的東西。”
“你可別這么說,那女人可是大人家的閨女,聽說城里的藥房就是她爹開的。”
“懂啥啊你,早就家庭敗落了。”
“別酸了,瘦死的駱駝也比你家馬大。”
“去一邊的,懂什么,都說那拔毛鳳凰還不如雞呢。”
張光明的老婆叫白芳。長得標致可人,婀娜生姿。從小家庭顯赫富貴,父親開藥房,親媽早早去世,又納了個小媽。小媽揮霍無度,卻還有點人滋味,父親死后,給白芳留了不少錢,自己離開了。白芳身材高挑有氣質,穿的衣服鄉下人連見都沒見過。總之,她的一切,都是賣肉的屠夫所配不上的。自嫁過來后,白芳就在廚房做事了。
從和面、揉面、發面一點不會,到幾十個人吃的飯不在話下,白芳是有天分的人。雖然只是在廚房做事,她仍然每天修眉描眉,搽口紅胭脂。頭發也用烤熱的棒子卷,戴上發簪。身上的香水香滿了整個成二村。女人都把她看成是眼中釘,抽空就在背后亂說,“你看她走路的樣,不害臊。”可日子久了,村里的女人也心癢癢了,又開始撿著好話給白芳講,末了再添一句,“哎呀妹妹,差點忘了,你看俺明天去城里,尋思著可不能給咱村丟人啊,你那件束腰的白衣服……”白芳倒也爽快大方,“不行。”
于是白芳的壞名聲就傳遍了村,但白芳不在意。
那日“老實頭”媳婦氣鼓鼓地出了張光明的門,一出去就看見劉姨,“哎呀劉姨我跟你說,這白閨女真是摳下個人來!我這輕易不求人,頭一次借她的那個破簪子,又不是衣服鞋,可她就是不借,說著說著倒成我去搶她的了!”
說完,又看見李二嫂,“哎呀嫂子,我跟你說……”后來又碰見賣油的小竇,“哎呀小竇,可是見著你了,我跟你說……”“老實頭”媳婦的大嘴巴是出了名的,到最后全村的人都知道白芳的“摳門至極、鐵石心腸、裝小姐毛病”了。白芳自己也不解釋,照樣打扮自己的,做自己的飯。
說到這里,白芳倒有點得意了,咧嘴對我笑了笑,“那衣服鞋子都是是我爹給我買的,簪子更不用說,怎么能說借就借。總歸我還是大戶人家的閨女,是有一點脾氣的。”見眼里突然盈眶,她隨即又扯開話題,笑說:“嘻,老張還給我寫過詩呢,酸的牙都疼。”
后來的張光明讀上白話詩,這種詩是白芳所看不上眼的。但情深意切的張光明還是執意寫了一首,送給白芳:
獻給 蜜絲白
大天地里 撞著個你
想起二叔說 孩子 遇見心儀的 才來告訴
我便去告訴
一萬個人有一萬種人生
一萬條路
偏偏我的 交叉在你的上
白芳讀完,輕輕笑了一下,“你若把你用在這淺詩上的歪才,用在唐詩宋詩上,定成張子美了。”說罷,把那張寫詩的紙疊了疊,夾在書里了。
張光明也笑,不善言辭,無別的話來答。就只是笑。
有日,畏畏縮縮的杜老頭偷偷地跑去村長家,說了點悄悄話。
第二日村長就叫張光明來了。
“小張啊,叫你來是想問問你,你還記著俺丟的那頭豬嗎。”
想了想,“記著。”
“這不昨日,哎,我本來不想查,可那老杜跑來跟我說他知道誰偷的,叫我說吧,我是絕對不信的,但一想到傳出去可不太好啊,我就尋思問問你。你知道是誰嗎?”
“不知道。”
“張得水,你二叔。”
“刀子張”沒說話,村長接著說下去,“說是你娶媳婦那天,你二叔來,夜深了才家去。回家的路上看見俺家的豬棚沒鎖上,趕著一頭豬就走了。這事你知道不?”
“刀子張”咽了口唾沫,“不知道。”
“嗐,就知道你不曉,不然早就來告訴我了。是不是?”
“是。”他說,又補一句,“當然是,自然的。”
“那明天我叫你二叔來一趟怎么樣?你同意嗎小張?”
他點頭。
第二日張得水接到通知說,讓他來村里領個米。早早便來了,牽著他養了九年的狗。
張光明也來了,只不過是站在遠處的坡上,拿著他用了二十九年的剁肉刀。
他看著張得水進去,也看著張得水咋咋呼呼地出來,“怎么可能!他血口噴人!我偷你的豬來做什么!我他媽又不吃肉!”
“刀子張”悄悄地走過去,快到跟前了,他二叔才看見,“哎呀老侄子,你好歹來了!你快來評評理,他非說我偷了他家的……”
“哐!”一刀下去,全靜了。
“二叔,我知道,是你家狗干的,我替你解決了。”
這件事從那后沒敢再提的。整村只要是個活人,就知道張得水愛狗如命,他親侄子一眼不眨地剁了他狗的頭,張得水當場就暈了過去。后來醒了就半身不遂了,也不能說話了,躺了幾年就死了。
對于張光明的“老實拐古”,大家也都心里明白了,“干殺畜生出身的,不中交。”更何況白芳還是性子高傲的人,便無人再跟他家來往。
“是他二叔偷的?”我問。
她搖了搖頭,“就算是,也是為他。我見著是成親那天桌上有不少肉,后來才曉得竟是這樣來的。”
我喝了口水,“那對你呢?對你也這樣暗地里狠毒嗎?”白芳眼神飄忽了幾秒,失神地笑了笑,“對我是好的。有八分,他恨不得給我十分。可大家不是都說,苦才是人生嘛。一點也沒錯的。”
好一陣子來,張光明都隔天地出來賣肉,有時隔幾天,有時甚至隔半月。家家吃菜都見不著點油腥氣,個個的牢騷積了一肚皮。
再往后更甚,一個月都不出來。好歹出來一次,也沒有多少好肉,肉里頭注的水也更多。張光明的面色日漸槁黃,愈發寡言,身形也消瘦,甚至后來幾次連骨頭也剁不開了。
村里頭大家背地里都議論紛紛,再加上白芳日日憔悴的臉,無暇理擺的頭發,還有張光明夜里去城里的次數越來越多,斷定,“八成是染上吸銀粉了。”
是染上了。
從剛開始的“就吸一下嘗嘗滋味”,到后來哪日不吸就得發瘋。張光明城里的所謂“好友”讓他天天夜里去城里拿。花光了半輩子賣肉的錢,只得花白芳的錢。白芳知道那銀粉,從小爹就告訴,“這是治煞天上皇的毒物,萬萬碰不得的。”可她攔不住他。她不給,他就偷,再后來就搶,那辛辛苦苦賣藥賺下的錢,怎抵得上買那毒藥的花銷。沒幾月就空了。
張光明卻愈演愈烈,非要白芳當了她的衣物首飾,白芳不肯,他威逼利誘,“這最后一次,發毒誓。”可哪有什么最后,毒癮上來就如何也不顧了。最后那次,一巴掌把白芳打到地上,頭破了,嘩嘩地流血。白芳坐在地上號啕地哭,把從小從年輕憋的淚全哭出來,說,“今生該是我欠你的。你別逼了,我盡我力。”
當日晚上就收拾了行李,說是行李,只有一件布衣服,和她的三個發簪,其他都留給賣肉的,離了家。
說完這里,白芳一仰頭,喝空了酒,站起來晃悠悠地,小聲說著話。聽不出是什么。
她離了家,無處落腳,薦頭店老板娘把她引到我家里來,母親問她會做什么,“女紅,做飯。”問她家庭,“死了父親,死了丈夫。”看她樣子標致可人,卻一副看透了的超然模樣,便留她下來。
那時,她也不過剛剛三十歲。
“我生來幾年,把我后來幾十年的福早享了,也不虧。”酒有點烈,她笑著說。
今日里是白芳頭一次提及過去的事,該是心里頭憋久了,得說一說。可但凡提的,也是放下的事罷了,當年怎樣認識,怎樣肯嫁大自己二十歲的屠夫,是不肯說的。看著眼前這張臉,縱是美麗,卻是憔悴衰老了,如何也想不出它曾被精心地涂粉抹紅。
前日聽到張光明抽銀粉抽死了,尸體放在山頭草房子沒人管。白芳愣了一天。昨日默默地拿著發簪,去城里當鋪當了,跟我母親說,“放二日假給我吧。”
回去給張光明發了喪。
“為什么?總該有點原因。發簪珍貴,他卻那樣狠毒寡義。”我問。
白芳又喝了一大口酒,沒有答話。
“若是沒有嫁他,日子該是比現在好。”我有點哽咽,說。
“哎呀,你說……誰有重來一次的機會呢……這就是我的路啊……”
“一萬個人,有一萬種人生,一萬條路,偏偏我的,交叉在你的上。”她斷斷續續說出,已經徹底醉了。
還在絮叨,“不去看看你,我怎么放得下心……一萬條路,唉,一萬條路,沒錯的,偏偏我的,交叉在你的上。”
(責任編輯 劉冬楊)
(作者系山東淄博第四中學高三一班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