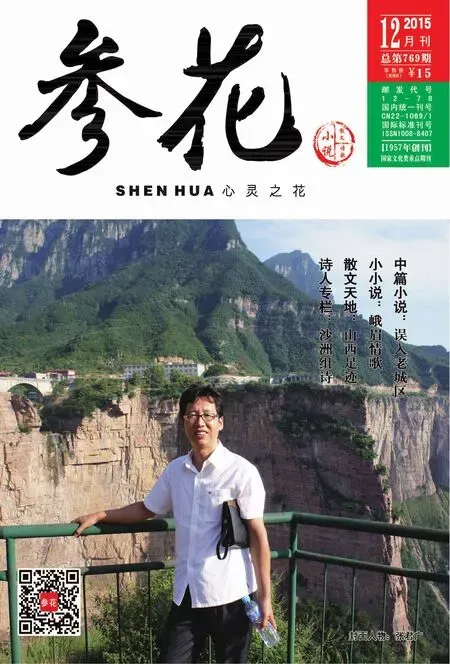藏族民間故事阿克頓巴與納西族民間故事阿一旦藝術特色之比較
摘要:藝術風格的形成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單從形式方面來講很難把它從藝術的總體中分離出來,作品的藝術特色是認識生活以及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同類事物的藝術特色是相似的,而《阿一旦的故事》和《阿克頓巴的故事》兩組故事產生背景、思想意義和人物形象等都極為相似且兩者都是現實主義的作品,因此兩組故事的藝術特色相比也幾乎相同的。
關鍵詞:藏族民間故事 阿克頓巴 納西族 藝術特色
《阿一旦的故事》和《阿克頓巴的故事》兩組故事產生背景、思想意義和人物形象等都極為相似且兩者都是現實主義的作品,因此兩組故事的藝術特色相比也幾乎相同的。
普適性。兩組故事,點點滴滴無不取材于現實生活。它們所反映的雖是當時社會現實中的主要矛盾和斗爭,但它們不是憑著龐大的離奇的事件,也沒有曲折錯綜的情節,而是切取日常生活中平凡可見、能夠觸摸的小事,每個故事幾乎是信手拈來,真切自然,散發出當時社會生活的濃郁氣息,使人感到,這些事就像發生在自己的周圍。如《怕父親》,木老爺叫阿一旦使本事騙他跑糧架,阿一旦說怕父親知道了挨打,叫木老爺先到糧架上看他父親在不在家,如果不在就可以。木老爺真的爬上糧架看阿一旦的父親在不在家,便下來叫阿一旦騙他,阿一旦笑著說:“剛才不是騙過了嗎?”又如在《貪心的商人》中,阿克頓巴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辦法,讓貪心的商人既賠了錢,又丟了人。
典型性。從每一個故事看,篇幅較短,情節精粹,結構緊湊,布局嚴密,把博大的思想內容濃縮在小容量的篇幅中,寓“全豹”于“一斑”,顯得玲瓏剔透,無疑是經過千錘百煉的,具有高度的典型性。從所刻畫的環境和人物看,也都是典型化了的。在階級對立的環境中來刻畫人物,使人物形象具備了典型性格,栩栩如生,做到了如恩格斯所說的:“把各個人物用更加對立的方式彼此區別得更加鮮明些。”
幽默性。一個故事就是一幕出色的諷刺喜劇,充滿了詼諧幽默的氣氛,無不令人會心而笑,產生強烈的效果。如《狗怎么叫》中木老爺和他的夫人與阿一旦打賭,如能讓木老爺學狗叫,愿輸五兩銀子。阿一旦說有一只打獵狗“瞿瞿瞿”地叫著追趕他,木老爺自作聰明地反駁:“狗屁……大獵狗都是‘嗚嗚嗚地叫。”阿一旦哈哈大笑:“你的叫聲真像一只大獵狗。”這時,讀者也不禁要被感染得捧腹大笑。在笑聲中是那些假、丑、惡的東西來達到對真、善、美的贊頌和肯定,這樣就產生了以笑為武器揭穿舊勢力的內在空虛和價值的本質,激勵人們去為埋葬它們而斗爭的喜劇效果和美學意義。
哲理性。在不少的故事中,都或多或少蘊含著深刻的自然哲理和社會哲理,在笑聲中給人以啟迪。如《釜為貴,禾最高》中木老爺過年時貼了一副對聯:“天下金為貴,人間木最高。”炫耀木家的富有、高貴,阿一旦只填了一兩筆便改為:“天下釜為貴,人間禾最高。”這里雖只改了兩個字,卻鮮明地道出了兩個階級截然不同的價值取向,于平凡中顯示出深刻的哲理。
在探討藝術特色時,還應提一下互滲性,這一性質在阿一旦的故事中尤為明顯。阿一旦的故事與阿克頓巴的故事之間同樣存在互滲性。例如,阿一旦的故事中的《借一串還兩串》與阿克頓巴的故事中的《借糧還舞》等,在局部內容或演繹的手法上都有些相似,這種互滲性已成為各民族機智人物故事的一個共同點。
通過觀察阿一旦的故事和阿克頓巴的故事,本文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他們是在相連的兩片大地中開放的兩朵奇葩。
第一,他們的故事都是有一個特定的人物作為正面的主人公貫穿起來的。故事主人公都是扎根在被壓迫的勞動人民之中的普通勞動者,都是有機敏詼諧、見義勇為、扶弱濟貧的高貴品質,都表現出以智慧取勝、以弱克強的過人本領。
第二,故事的基本主題都是反映納西族與藏族人民同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和斗爭,反映勞動人民在統治階級桎梏下,被欺壓被盤剝的悲慘生活,表現勞動人民反抗壓迫、剝削的斗爭精神和他們要求改變不合理的現實生活的思想愿望。故事的結局都是善良正直的勞動人民贏得斗爭的勝利,而狠毒殘暴的統治者剝削者遭到辛辣的嘲諷和嚴厲的制裁。
第三,故事都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藝術作品。故事的現實作用和社會意義,常常是伴隨著笑聲傳達出來的,故事的篇幅都比較短小,能充分發揮諷刺藝術的特長。善于運用虛構和夸張的表現手法,把現實生活中的時間描繪得有聲有色,新鮮有趣,興趣盎然,引人入勝。對反面人物帶有漫畫式的勾勒,從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反面人物的精神世界。故事結構單純、緊湊,情節生動,構思新穎,不落俗套,語言貼切,耐人尋味。
以上綜合分析兩個故事的共同特征,可以看出,作為不同民族的兩個一樣機智的人物的故事屬于同類型的題材,同類人物。
(作者簡介:澤珍卓嘎,女,西藏大學文學院2013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藏漢翻譯)
(責任編輯 劉冬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