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的尊嚴與影視救贖——《智取威虎山》的徐克解讀方式
李 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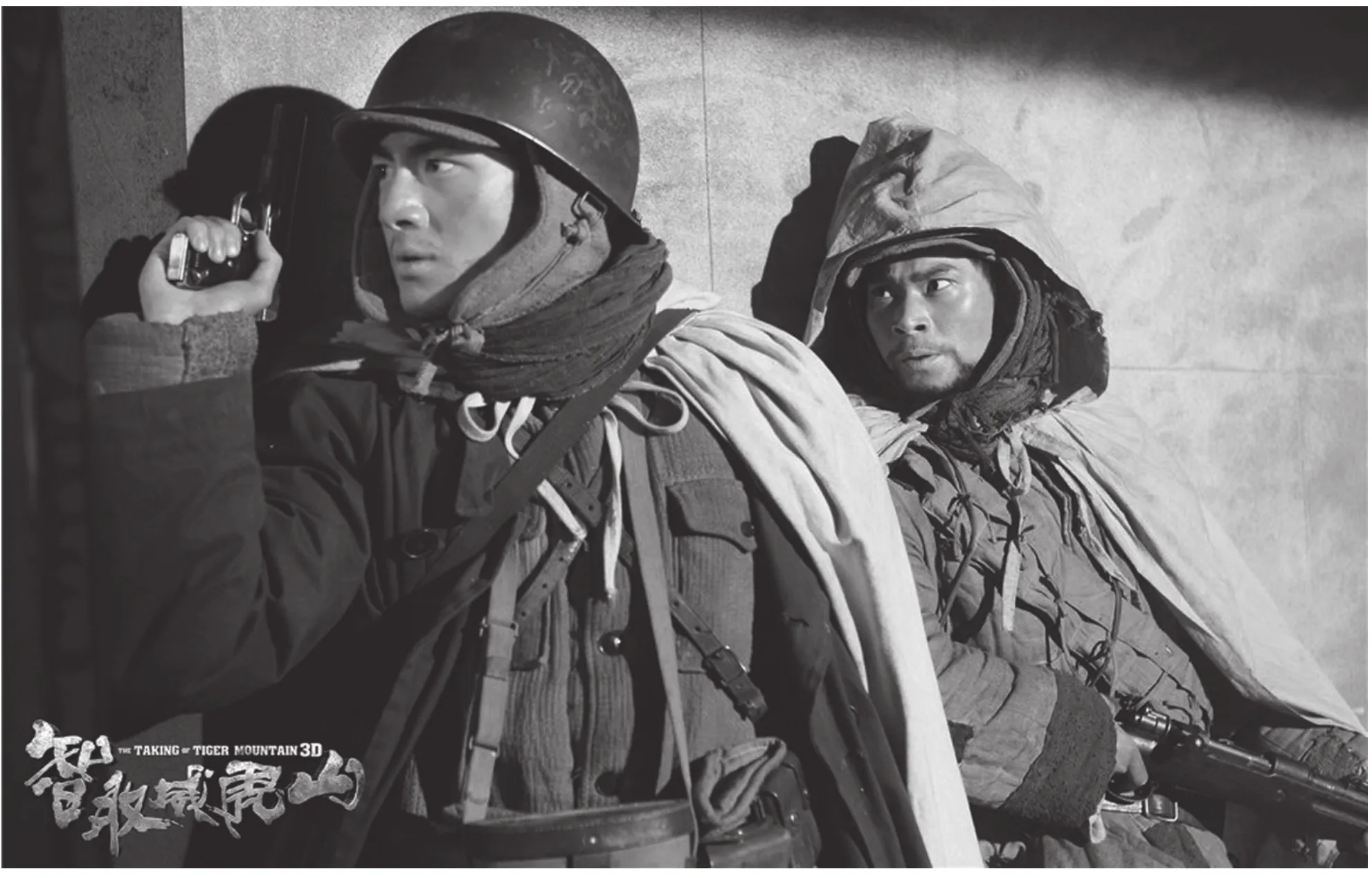
電影《智取威虎山》劇照
近期,由徐克導演的電影《智取威虎山》以近7億元的票房成績超越了被寄予厚望的姜文導演的《一步之遙》。徐克版《智取威虎山》以天馬行空的想象力和武俠片的影視手法,賦予了紅色經典《智取威虎山》以時代意義,電影以諜戰片的姿態,顛覆了樣板戲的意識形態頌揚。相比較姜文的《一步之遙》,徐克版的《智取威虎山》更像一個文化符號,它延續了紅色經典的當代闡釋高潮,紅色經典集體記憶的天然親和力加上功底成熟的視覺操作,讓徐克版的《智取威虎山》在觀眾的期待心理上比《一步之遙》先行一步。正如影評人王子榛所說:“未來有關紅色題材的改編可能會成為業內一種新的潮流方向,因為從現在的視角來看,所有的紅色題材都是一個超級IP,它的版權形象已經非常朗朗上口,深入人心了,缺少的就是現代化的重新演繹。”[1]
徐克電影《智取威虎山》與革命樣板戲《智取威虎山》都出自曲波小說《林海雪原》,樣板戲的時代經典意義歷久彌新,因此電影改編的標桿自然就是樣板戲,而非小說原著,這也是徐克版《智取威虎山》的影評和輿論宣傳集中在電影和樣板戲之間的孰是孰非的原因所在。可以說,當代的影視改編是戲劇擺脫困境的一種救贖方式,雖然影視的改編不乏誤讀,但這也是文化娛樂時代藝術跨界生存的必由之路。
一、戲劇的影視救贖
在影視出現之前,戲劇作為一種經典藝術樣式是大眾的主要藝術消費方式,但是隨著視聽影響媒介技術的提升和大眾生活節奏的提速,戲劇展演這一程式化的、耗時、耗財的文化消費方式逐漸呈現出了雅化的傾向,走進劇場看戲逐漸成為少部分精英的喜好。傳統戲劇在“劇場”中雖然能夠保存其藝術內涵和表現力——有舞臺,有表演,有引人入勝的劇情設計。但是戲劇作為一種與觀眾深度交流的藝術傳播方式,藝術理解的深度界定已經隨著快餐時代的到來而逐漸喪失。劇場面對影視的強大沖擊,走視聽銀幕化之路成為戲劇適應時代需求的藝術探索模式,這也是市場化的必然要求。
《智取威虎山》節選自著名作家曲波《林海雪原》中的一段故事,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中與《白毛女》《紅色娘子軍》《紅燈記》《沙家浜》等一同被樹為紅色經典的傳統樣板戲。在徐克之前,這部紅色經典題材曾被演繹過多個版本——1958年,上海京劇院曾將《智取威虎山》改編成話劇;北京京劇團又將該題材改編成《智擒慣匪座山雕》;此外,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也曾將《智取威虎山》改編成話劇;1970年京劇《智取威虎山》以電影的形式展演。徐克版的《智取威虎山》是在借鑒這些戲劇版的基礎上的當代演繹,融入了更多的時代審美需求和時尚技術元素,這也是電影對戲劇的時代超越。
英國戲劇理論家彼得·布魯克在界定戲劇時說:“戲劇是一種人類根本性的需要,而劇場和戲劇的形式、風格等等只是些暫時的盒子,完全可以被取代。”[2]他的這一界定為戲劇實驗和戲劇嘗試提供了多種可能性,而影視劇則是戲劇在電影領域的跨界表現。電影雖然是工業化的產物,是最商品化的藝術形式,但是,他作為現代最豐富的藝術表形式卻保留了傳統戲劇的內涵和精髓,并且用更技術化、多維的方式展現其藝術魅力。影視劇對傳統戲劇的改編并不是將原作進行面目全非的大幅度調整,它只是將一個部分從完整的戲劇結構中抽離出來,并且放大,讓人們通過畫面更深刻地感受到戲劇所傳達的情感和意義。
電影對戲劇的改編方式是多種多樣的,汪流教授在他的《電影編劇學》中將電影改編方式分成六種:移植、節選、濃縮、取意、變通取意和復合。[3]“節選”和“濃縮”往往應用于小說改編為影視的情況,受制于篇幅等原因的選擇;“移植”和“復合”多應用于諸多題材和主題的融合;“取意”和“變通取意”是指從某一作品中得到某種啟示,重新構思,大部分分保留或較少保留原作中的人物和情景以及原意的改編方式,這也是戲劇改編為影視的主要手段。
徐克版《智取威虎山》在小說與樣板戲的基礎上“取意”,表達的是一種革命的英雄主義,張涵予的恰當表達也將楊子榮的孤膽英雄形象塑造得淋漓盡致。但是,徐克版《智取威虎山》則在淡化樣板戲的意識形態性和政治話語的教導意義,將武俠情結“移植”到電影當中,這也契合了徐克傳統的諜匪片、懸疑片的暴力美學傳統。楊子榮深入威虎山臥底,單刀赴會的場景是義士、俠客的形象的現代演繹,而身在匪窩的亦正亦邪、亦善亦惡的表現,則滿足了撕碎道德戒律的幻想欲望。其中最為經典的是途中穿插的一段武松打虎般的奇遇更是將武俠之風的極致表達。當百雞宴除夕,部隊滑雪進山時,“便產生了《西游記》師徒四人斬妖除魔般的期待與快感,這種快感同時遵循著暴力相向的原始沖動和邪不壓正的道德正義”。[4]
電影對戲劇的改編除了主題的“取意”之外,在內容上更多的則是“變通取意”。徐克版《智取威虎山》更多的“移植”了當代商業電影的一些要素,讓電影看起來比樣板戲更具有時代感。電影中剿匪小分隊戰士之間不再互相稱呼同志,一方面是為了淡化政治形態,另一方面主要是為了拉近電影和觀眾的時代距離。樣板戲楊子榮與座山雕的情感完全是敵我對立的,而電影中則隱約的表現出來惺惺相惜的意思,這更符合“人”的普通情感。為了增強時代震撼力,徐克還在結尾增加了一個極具現代感的飛機追逐戲。樣板戲對少劍波與衛生員白茹之間的情感是采取的回避手法,而電影中則將二人的情感進行微妙的傳遞,雖然這條線索最后是無疾而終。然而,這些改編都是對傳統樣板戲生硬的人物個性和政治符號化的當代闡釋。
電影在強調視覺沖擊和技術至上的同時,挖掘了戲劇中的“戲劇性”要素,電影的這些技巧的應用打破了傳統戲劇的“第四堵墻”的限制,沖破了“三一律”的禁錮,擴大了戲劇的時空廣度和深度,讓戲劇的寫意舞臺更加多樣化,實現了戲劇空間、時間的流轉、剪輯和自由轉換,這樣戲劇的整體式微在電影表達中得到有效扭轉,這也是戲劇的自我救贖之路。徐克《智取威虎山》的市場效果說明了一切:從2014年12月23日下午17點開始公映的《智取威虎山》,首周5天半的時間里收獲了3.18億票房,成為當周的票房冠軍,年輕觀眾對該劇的熱衷度可見一斑,戲劇改編成電影的藝術魅力更是顯而易見。
二、影視對戲劇的誤讀
電影是在視聽時代對傳統戲劇的一種救贖,電影與戲劇是兩個不可分割的領域。但是,戲劇畢竟是歷史悠久的藝術,在漫長的藝術實踐中積淀了人類的深層文明和情感。電影作為年輕的藝術形式是必須向戲劇致敬的,所以這就要求每一個電影人在創作時應保持對戲劇尊嚴的尊敬,將新式的表達形式與古老的藝術形式結合,創作出具有市場價值與藝術價值雙贏的作品。
理解電影對戲劇的“誤讀”,必須明確電影與戲劇的差別所在。電影從出現之初就是從眾多藝術形式的母體中孕育發展的,它集合了戲劇、音樂、舞蹈、建筑、文學等眾多的藝術門類的技巧和手法。“100多年后的今天,當我們仔細審視獨居品格的現代電影形式時,不免感慨它包含了太多的其他藝術的元素、構建、色澤、機理,并欣喜的看到漸趨成熟的電影在藝術上的‘輸出’,看到絢麗的電影對曾是可望不可及的‘成年’藝術——戲劇等等悄無聲息地滲透和影響。”[5]
電影的這種藝術雜糅并不能抹去它和戲劇的差異,兩者在藝術特質、敘事手法、形式要素等方面有著根本性的差別。首先,戲劇是以語言、動作、舞蹈、音樂、木偶等形式達到敘事目的的舞臺表演藝術的總稱,舞臺表演時戲劇的核心。電影是由活動照相術和幻燈放映術結合發展起來的一種連續畫面,是一門視覺和聽覺的藝術,畫面技術是電影的根本,技術的提升是電影發展的內驅力,而技術的背后助推則是商業利益的驅使,因此,商業性是電影的重要屬性。
畫面技術可以對舞臺表演進行再現和模擬,但是這種模擬和再現由于受到商業利益的左右,則存在眾多“有意識”的“誤讀”。徐克版《智取威虎山》是對樣板戲的解讀,在解讀的過程中有意識的回避樣板戲的政治屬性,將其打造成諜戰、現代武俠大片,這是對樣板戲的“誤讀”。戲劇《智取威虎山》是在小說原著的基礎上改編而成的現代京劇舞臺藝術片,是八部革命樣板戲中的第一部,旨在表現人民解放軍在東北的剿匪斗爭,其中所包含的紅色美學是該劇經過歷史滌蕩的精神內核。徐克版《智取威虎山》將其替代為僵化狹義,是對戲劇精神內核的“誤讀”。張涵予所塑造的楊子榮更多的是刀關劍影、豪情仗義,缺少了一種“紅色信仰”,而這種信仰是樣板戲等紅色經典的根基所在。“香港人徐克當然無法理解這些,他既沒有經歷過這種話語、思維方式的形成過程,也不是被這種文化啟蒙浸潤的,不然就算動作上可以用現代招式更換槍打雙燈和飛身插椅,也決不會丟棄‘老九不能走’這句已然脫離母本而獲得獨特意味與記憶的經典名句。”[6]
其次,電影與戲劇的敘事手法的不同所引發的誤讀。電影與戲劇雖然都是時空藝術,但是,電影的時空較戲劇時空更加自由和寬泛,電影的敘事技巧和手法可以讓表演動作、細節定格、升格、降格。而舞臺的相對固定就讓戲劇的時空相對受到限制,可以說戲劇是“動作在固定空間和延續時間中的持續發展”。[7]樣板戲《智取威虎山》舞臺背景主要鎖定在幾個不同的場景,而電影《智取威虎山》充分運用了時空切換技術,甚至在影片開頭運用了流行的“穿越”手法。電影的這種時空藝術讓故事更加好看,也更具有藝術張力,但是相比較樣板戲的矛盾集中爆發所引發的觀眾的情感共鳴來說,這種“多點開花”的時空藝術分散了觀眾情感的注意力,這是對戲劇的“場景”的誤讀。
電影的敘事結構與戲劇的敘事結構也不盡相同,戲劇的敘事結構是由一個個的“場”構成的,基本是順序的疊加。而電影的敘事結構是由一個個的“鏡頭”組成,鏡頭的剪輯技巧和拍攝技巧讓電影的敘事結構可以全方位的表現時空概念。樣板戲《智取威虎山》就是節取了《林海雪原》的一部分片段,然后通過場景來展現敵我斗爭,而徐克更多是通過鏡頭來展現英雄品性和推動故事情節。鏡頭的多維應用讓電影人物更加“豐滿”,讓故事情節也更具看點,但這種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戲劇的表演的本性,這也是對戲劇的“誤讀”方式。
電影對戲劇的表演技巧和欣賞視角也存在“誤讀”。戲劇和電影作為一種具體可感的藝術形式,故事敘述者和觀眾的關系尤其重要。但是,欣賞戲劇的時候,觀眾的欣賞視角是不變的,而欣賞電影觀眾的視角卻是全方位的,這讓觀眾更能夠形成一種宏觀的欣賞效果。在電影《智取威虎山》中鏡頭可以將座山雕的面部擴大到極致,可以利用特技將老虎追趕楊子榮的場景進行虛擬化再現。但是,這種全方位的視角卻省略了欣賞戲劇時的關鍵要素——“想象”,直觀的鏡頭呈現和逼真的技術虛擬,是對戲劇“想象性舞臺”的“誤讀”。
三、跨界的藝術生存方式
戲劇作為大眾曾經的主要精神食糧,在藝術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曾經不可一世。然而隨著電影和網絡娛樂形式的普及,尤其是近些年西方大片的扎堆引進以及國產商業大片的提檔升級,戲劇的生存現狀不容樂觀,在這種整體式微的時代氛圍之下,戲劇中的許多經典元素正在逐漸消失。因此,戲劇與形式的相互促進、跨越和互動則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
戲劇與電影的跨界結合的過程從電影產生就已經開始,經典戲劇基本都改編過電影,經典電影也曾經以戲劇的形式在舞臺上演出,尤其是近幾年戲劇借用了電影的大量技術手法,表現出了對電影技術的盲目崇拜,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燈光、背景、舞臺旋轉、升降等方面,以期讓戲劇達到影視的觀演效果,而這恰恰是對戲劇本真的背離,“但戲劇的本體是演員的表演,是一種高水平的文學本根,如果不注重讓戲劇更多的抓住當代人的心弦,讓戲劇的舞臺表演更加絲絲入扣的體現人物的情感,再多的技術創新都不能在觀眾心目中留下深深的刻痕”。[8]電影與戲劇的理性跨界存在方式,應該是在電影中的戲劇性表達與戲劇中的電影化應用中把握住適當的“度”——藝術的本體特質。
電影的戲劇性表達的觀點一直受“影戲理論”的影響,我國第一代影視理論家侯曜就認為:“電影是戲劇之一種,凡戲劇的價值它都具備。”[9]電影的戲劇性表達在我國的第五代導演中也有著極端的嘗試,那就是將戲劇直接搬上電影。張藝謀的《滿城盡是黃金甲》就是對莎士比亞《哈姆雷特》的中國闡釋,但是這種直接扮演的方式,限制了電影表達空間。徐克的《智取威虎山》是對樣板戲的電影化再現,人物塑造、故事情節的構建基本是忠于戲劇文本的,除了增添了像土匪婆等一些邊緣角色之外,電影基本延續了樣板戲的故事脈絡,甚至是臺詞都是大段照搬。表現的最為突出的是人物性格定位上,仍然延續了樣板戲的臉譜化:楊子榮就是一身正氣,集所有優點于一身的正面人物;座山雕就是窮兇極惡的,狠毒、狡猾。正如有的評論者所說:“票房的高筑,并不代表《智取威虎山》有多可取,相反,我們要警惕二元思維的抬頭。畢竟人性是復雜的,用非黑即白的好人與壞人來區分,不盡科學。”[10]
電影化手段和思維不僅戲劇中廣泛應用,其他藝術形式也都將電影手法作為創新的重要突破。這一方面是藝術形式的破繭重生,另一方面也是不同的藝術形式追求觀眾的需要。戲劇電影化的手段擴大了戲劇自身的表現力,擴大了戲劇的傳播空間。“戲劇對電影的染著力不僅體現在劇本編創過程中的結構和模式上,也體現在電影中的戲劇元素上。”[11]當前的舞臺劇、歌劇等經典戲劇樣式以及“小劇場”戲劇都廣泛應用影音元素,將影視劇本的編寫方式直接應用到戲劇劇本的創作過程中,并將其作為嘩眾取寵的主要亮點。
電影是戲劇的當代救贖方式,然而戲劇不能將電影作為藝術實踐過程中的救命稻草,戲劇在當下狀態下活得有尊嚴,終究還是根源于自身藝術特質的張揚。而電影改編戲劇,在迎合時代需求和大眾審美期待的同時,對戲劇底蘊的挖掘應該是電影戲劇性的根本。
[1]張漢澍.紅色電影的新時代逆襲《智取威虎山》票房目標定為10億[N].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2015-01-06(A2).
[2](英)彼得?布魯克.敞開的門——談表演和戲劇[M].于東田,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封面.
[3]汪流.電影編劇學[M].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359-361.
[4][6]徐鵬遠.香港人徐克不懂共產黨員楊子榮的心[EB/OL].鳳凰網?鳳凰文化?《洞見》(115期).(2014-12-29)[2015-05-01]http://culture.ifeng.com/a/20141229/42822085_0.shtml.
[5]周華安.比較藝術視界:電影與戲劇[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4).
[7]汪獻平.電影敘事與戲劇敘事之比較[J].中央戲劇學院學報《戲劇》,2005(1).
[8]高薪茹.從舞臺到銀幕的跨越與互動——中國戲劇與中國電影的可持續發展[J].藝術教育,2013(11).
[9]侯曜影.戲劇本做法[J].當代電影,1986(1).
[10]曾念群.評徐克電影《智取威虎山》:故事改編無突破[N].羊城晚報,2015-01-06(B1).
[11]黃飛玨.戲劇對電影的染著力[J].上海戲劇,20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