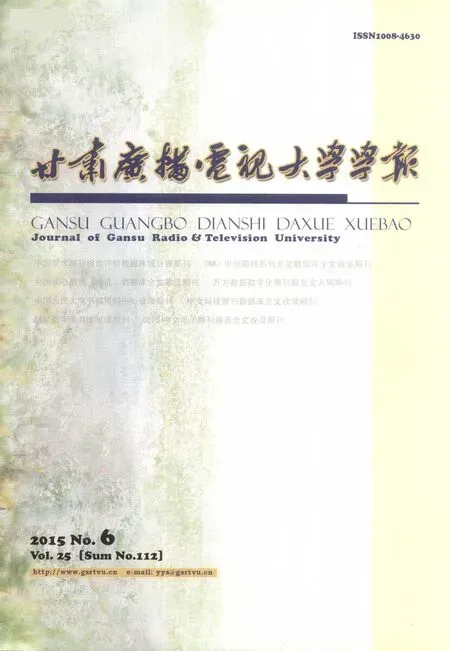漢代四言詩的《詩》學背景
張 侃(上海商學院 文法學院,上海 200235)
漢代四言詩的《詩》學背景
張 侃
(上海商學院 文法學院,上海 200235)
《詩》學是漢代高雅形式的四言詩的創作背景。從《詩經》本文的實用典雅到春秋以來的“賦詩言志”,再到戰國以至漢代的《詩》學理論的宗經、征圣、明道到“美刺”的批評,主旨皆在遵循傳統而付諸實用,未曾出現四言詩創作的新見,使四言詩在漢代走向衰落。
《詩經》學;“美刺”;四言詩
歷經戰國動蕩、楚漢相爭的數百年動蕩,漢王朝的建立,終于迎來了王朝的統一與社會的安定,傳統文化也進入劫后復蘇的階段,然而其基礎卻相當薄弱。一是劉邦草莽出身,輕慢儒術,遑論文教。人笑項羽“沐猴而冠”,同是楚人劉邦未必不是如此。二是漢承秦制,至惠帝時始除秦挾書之律,風雅文教才得以傳播和實行。以《詩》《騷》兩大傳統文學為背景的文學才得到發展。因而在對《詩經》與屈《騷》闡發與批評的基礎上,屬于漢代自己的詩歌創作漸次生成,并首先影響到作為漢代主流詩歌形式四言詩的創作。漢代詩學理論的建立,是基于對先秦典籍的發現與整理,并與當代經驗主義的思想基調一致,而對《詩》《騷》的闡釋與仿制,就成為漢人詩歌創作的出發點和最終目標。所以,《詩》《騷》尤其是《詩經》的批評理論,直接引導著漢代四言詩的創作。
漢初即以魯、齊、韓三家今文詩立于學官,《毛詩》是古文經,在西漢初年已行世,至東漢尤其是經鄭玄箋注之后,才將三家詩的統治地位取而代之。但無論古、今文《詩》的興替如何,其對政治教化功用的強調卻屬一致。而漢人特別重視《詩》學這一功用的其因,可從如下幾個方面梳理。
一、《詩經》本身的實用功能特征具有典范意義
周民族在早期持續不斷的遷徙生活中,農業生活造就了其重實際而輕玄想的氣質,形成了重事功而黜文飾的作風,這使得詩人的激情往往是通過質樸的語言以含蓄蘊藉的方式表達出來,形式上也是以節奏質樸而工穩的四言為主。在此意義上,《詩經》正可謂純文學。而四言詩這種以兩個節奏組成一句為主體的音律節奏形式,既是漢語詩歌發展早期的一個必然階段,也恰適于表達那種溫雅醇厚的宗法倫理精神。當然,《詩經》中并不乏四言以外的各種語句(節奏)形式,說明《詩經》時代的人們并非不能創作出四言以外的詩句,而從人們多采用四言形式寫作并普遍地欣賞這種形式的詩,可知其審美觀念為時代主流。換言之,這種簡短而且明暢的節奏,與宗法貴族體制的社會中人們莊重、舒緩的感情和氣度相契合,也與這個時代的審美需要相一致。
從其深層的文化功能看,由于《詩經》的時代是貴族宗法倫理精神統治的時代,每個社會成員都是宗法制度下的子民,其精神生活、物質生活的取向與社會體制基本保持一致,詩人宛如家庭成員,負有一定的義務與責任。如《大雅·公劉》謂:“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何楷釋云:“君、宗,即燕飲中事。公劉自以一身為君臣之君、宗也。對異姓之臣稱君,對同姓之臣稱宗。”因此,關注社會生活是每個詩人的天職,“詩言志”,所以《頌》詩希望通過對先民與部族英雄的感念以培固今日的社會秩序,如《周頌·維天之命》:“維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雅》詩褒揚兢兢于王政朝綱,扶正糾偏的政治舉措與美好愿望,如《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小雅·節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讻,式訛爾心,以富萬邦。”《風》詩雖然“感物道情,吟詠情性”①,但更多的則為“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宣公十五年》)。所以,以四言節奏為主的旋律,使《詩》的本事本旨借音樂的翅膀飛向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并進一步為《詩》提供了醞釀與生長的沃土②,所以詩人能夠“作此好歌”(《小雅·何人斯》)、“穆如清風”(《大雅·烝民》),出于自然的吟唱,卻不期然而然地具有了“動天地,感鬼神”(《詩大序》)的藝術力量。因此,《詩》便發揮著以樂教、言教相期“神人以和”(《尚書·虞夏書》)的巨大社會功用,是詩人的社會責任得以實現的津梁,也是引導全社會和諧共存與向前發展的精神指南,“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所以說,《詩》幾乎是那個時代精神生活的全部。
二、春秋戰國以來的板蕩格局,使《詩》的功用發生新變
《詩》曾經維系著西周至春秋初期政治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而當王綱解紐、社會出現危機時,諸侯爭霸成了社會政治的常態。因此朝聘盟會之際,諸侯卿大夫于折沖樽俎之間,必賦《詩》以言志。因為他們表面上都打著代天子征伐的旗號,所以最初必須申述一個各方不得不認可的觀念標準,故所言之志也許尚與《詩》的本旨本義相近,以示師出有名。后來則于針鋒相對之中,拋棄了尊王的觀念,只將賦詩言志這一形式存留了下來,大家都借《詩》以陳意,《詩》于是有了詩外之旨,所謂“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須稱《詩》以喻其志”(《漢書·藝文志》)。隱幽難表之意借發揮《詩》而得以曉暢明白,于是《詩》本旨本義成了喻體,而所賦之志成了主體。而因為《詩》成了喻體,所以詠桑間濮上男女風情之《詩》也可用在外交迎接的場合③,同一首詩也可言不同之志④,聽者不能知志且未能答賦者,等于在這個馳騁爭霸的時代缺乏一種溝通交流的手段,等于漠視被吞并覆沒的危險,被斷為“必亡”之兆⑤,所以“不學詩,無以言”,不僅是不能“使于四方”(《論語》),且不能“明志”⑥,不能“興于詩”而致知⑦。因此孔子也以斷章取義之法教《詩》。從此,《詩》成了交際中一種用以溝通的具有實用意義的經典。
到了戰國時期,朝聘賦詩已成歷史遺跡,詩樂分家,世俗之樂興起,于是《詩》的文字意義凸現,斷章取義的局限也就暴露了出來。首先是孟子認為斷章取義、賦詩言志的做法有礙于學《詩》修身,他指出:“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他認可詩樂的分家,“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孟子·梁惠王下》)。所以強調對《詩》的整篇本義的理解,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法先王”,以至于達到“人皆可以為堯舜”的境地(《孟子·告子下》)。其次是荀子從性惡論出發,以為“人之于文學也,猶玉之于琢磨也”(《荀子·王制》),只有學(勸學),才可為“天下列士”(《荀子·大略》),而圣人的治理經驗則反映在《詩》、《書》、《禮》、《樂》、《春秋》之中,所以要“宗經”,并由此途徑而體會圣人之道,即“征圣”,而“圣人者,道之管也”(《荀子·儒效》),可以使人進而明道。將《詩》的功用歸諸宗經、征圣、明道的教化系統之中。需要說明的是,他并不主張復古,以為“欲觀圣王之跡,則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荀子·非相》)。針對當代的社會實際,他強調“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荀子·王制》)禮因文飾能使人在愉悅中接受,而禮義之文中,正包括著詩樂等等,“樂合同,禮別異”,樂對于不同等級的人們之間的親和具有重要作用,樂教是禮制的輔助,而由于樂是“人情之所必不能免”,所以“樂者,圣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移俗易,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荀子·樂論》)。《樂論》以為詩、樂、舞本是三位一體,所以對于《詩》,他更強調音樂的因素,看到音樂巨大的社會作用,進而主張用強制手段將“圣王之跡”通過“樂”推行,在系統強調《詩》的實用功能的同時,啟漢代文化專制觀念的先河。要言之,這是一個“王者之跡熄而《詩》亡”的時代⑧,一方面使《詩》成為經典,另一方面詩義被曲解,成了這個時代詩學衰落的誘因。而到荀卿的《詩》學理論,則對漢代詩樂觀念具有直接而重大的影響。
三、漢代《詩》學理論與批評的實際
從漢初至景帝末,漢朝貴黃老而尚無為,各家學術繼戰國余緒而發展,儒家思想并不占統治地位,但儒家經典還是受到相當的重視⑨,荀卿的學生浮丘伯在高后時仍然在長安講《詩》,他的學生魯國申公一直活躍于漢廷與諸侯王國之間,其所傳《魯詩》,與《齊詩》、《韓詩》并立于學官。承荀卿的學術傳統,漢代《詩》學仍然主要就文字立論。
首先,從《詩》學理論而言,據《漢書·藝文志》載,“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今存十一篇。因為先秦時代所謂“樂”往往是指詩、樂、舞三位一體,所以《樂記》論樂,實際上包含著它的詩學理論⑩。《樂記》繼承了荀子《樂論》中對“樂”的重大社會功用的強調。荀子以為樂為“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樂記》進一步指出“唯樂不可以為偽”皆“人心之感于物”,所以“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鑒于樂“其感人深”,所以樂具有“禮樂刑政”而達于王道的政治意義:“故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具有“移風易俗”導民向善的教化作用:“樂者,所以象德也。”鄭玄注:“樂所以使民象君之德也。”“樂也者,圣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荀子·樂施》)因此,對樂的強調也就是對《詩》的重視。《樂記》詩論有兩個特點,一是強調詩的教化作用,“不能詩,與禮繆”(《禮記·仲尼燕居》),“志之所之,詩亦至焉;詩之所之,禮亦至焉”。從詩之“志”可知先王之禮(《禮記·禮器》),以求得“明于禮樂”(《禮記·仲尼燕居》),使詩成為政治教化的工具。二是指出詩之志的品質,“志之所之,詩亦至焉”,而“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也”(《禮記·經解》)。《詩》具有了“美刺諷諭以教人”的功用和“溫柔敦厚”的品質。
其次,就《詩》的具體批評而言,齊、魯、韓三家《詩》仍然依文字立論,其共同特征是對《詩》的闡釋緊密結合現實,摻雜了當時的政治觀念,并非就《詩》本義立意,而是引詩證“序”,“序”重事理,而所謂事理多為當時的政治觀念乃至陰陽災異讖緯,其目的是為現實政治教化服務,故其實質與春秋戰國時代的賦詩、引詩相一致。所以對《詩》的功能的認識,重在美刺,參與現實斗爭,諷諫朝政。大儒董仲舒的《詩》學與三家詩說相去不遠,他將詩的“美刺”的根源附會以天之譴告,他指出“《詩》無達詁”,然而并未就詩藝的含蓄蘊藉進行探尋,只是為主觀隨意的附會和曲說拓展了更大的余地。在此理論引導下的創作,不論是王朝的雅樂如《安世房中歌》、《郊祀歌》,還是詩人韋孟、韋玄成等的詩作,以四言形式為主的高雅詩歌都竭力展示其“美刺”的用意。
毛詩屬古文經學,西漢末年平帝時始立于學官。毛詩結合樂、舞論詩,認為“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又指出詩必須“發乎情,止乎禮義”,對詩的感情以嚴格的限制,其目的在于標舉詩的教化功能。《詩大序》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在于強調詩具有諷諫功能,“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毛詩對《詩經》“六義”的分析尤其是對賦、興、比的分析,幾近于真正詩學意義上的剖析,但他的出發點卻是為了說明詩具有“主文而譎諫”的功用與風格。《毛詩》對一些不合“主文而譎諫”的作品,以“變風變雅”釋之:“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與三家詩相比,毛詩則側重于采詩、編詩之意的發掘,似乎更重于述古,但目的還是為了闡明教化功能。東漢鄭玄遍注群經,對《毛詩》尤其有發揚光大之功。鄭玄以為,因禮而制作詩樂,為的是宣揚圣人賢德,以達到“風化天下”的目的,“歌詩所以通禮意,作樂所以同成禮文也”(《禮記·仲尼燕居》),“大合樂者,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其禮亡,今天子以大射,郡國以鄉射禮代之”(《禮記·月令》)。所以古詩是“風化之源”、“教化之源”。詩歌風教又體現為美刺諷諭的手法,鄭箋云:“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也。”據孔穎達《正義》,就是借詩歌音樂的特性不直言君主的過失,而是委婉曲折地規諷,以維護君主的尊嚴。所以毛鄭《詩》學仍然在“美刺”,與三家詩重視《詩》之社會功用方面殊途而同歸。

注釋:
①《朱子語類》卷八十:“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
②參見顧頡剛《論詩經所收錄全為樂歌》,《古史辨》三下。
③見于《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參見聞一多《詩言志辨》。
④參見揚之水《詩經名物新證》第8頁。
⑤《左傳·昭公十二年》:“宋華定聘魯,魯之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
⑥明志即修身。《國語·楚語》:“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韋昭注:導,開也。顯德謂若成湯、文、武、周公之屬,諸詩所美者也。
⑦《論語》:“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
⑧《孟子·離婁》:“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
⑨如文帝前元九年,詔命晁錯往齊從秦博士伏生學《尚書》。
⑩《樂記·樂象》:“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方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樂器從之。”《樂記·師乙》:“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古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責任編輯 張亞君]
2015-11-02
上海商學院科研項目“基于中本貫通改革的大學語文課程設計研究”(JX2015A0214)。
張侃(1962-),男,甘肅通渭人,副教授,文學博士,主要從事大學語文教學與中國古代文學研究。
I207.22
A
1008-4630(2015)06-002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