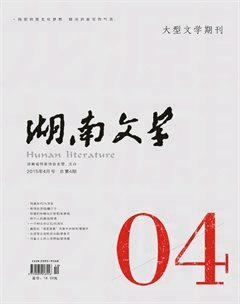其人其書(二題)
李佳懌
東寫西讀陸公子
陸灝陸公子,擱古代可入《世說新語》。開鳳鳴,辦《萬象》,編萬有,化脈望,“威海路梁朝偉”。江湖傳聞太多,我記下我見到和讀到的。
第一次見陸公子是在社里,他來開會,我很想一睹風采。會剛開完,我們完顏主任往走道一聲吼:誰誰不是想看陸灝嘛!臊得我和一行同事沒好意思近前,也避免了“看殺衛玠”的重演。
后來因工作關系,和陸灝先生有一些聯系,比文字還生動,他真是個很好玩的人。一次座談會后我們收拾桌子,發現一只香蕉上用水筆畫了仕女像,是陸公子開會無聊時的“杰作”。有一陣他忽然想收集自己的出生年一九六三年的所有學術書,刻兩方章鈐在上邊,一方印“癸卯同生”,一方印“人書俱老”。
我喜歡從書里讀人,尤喜讀讀書人。陸灝出得少,至今僅三本半:《看圖識字》《東寫西讀》《梵澄先生》(與揚之水結伴)和今年這本《聽水讀抄》。
從《聽水》知,九十年代中,陸灝提議鄧瑞先生整理其父鄧之誠日記中的讀書心得,后又寫信給鄧先生的弟子王鐘翰,商量日記整理事宜。同時期,協助王元化先生編輯《學術集林》。陸灝九八年主持《萬象》,在此之前做的事,似乎都在為此做積累。
我一個做報紙編輯的朋友,收齊了陸灝時期的全部《萬象》,前些時候忽然感慨:陸灝在我們這個年紀的時候已經在編《萬象》了。見過幾張他年輕時候的照片,眉眼里滿是謙恭和真誠。《聽水》書前祭出的十幾位助陣嘉賓,多是他的作者。陸灝當年拜訪完他們總是“恭恭敬敬地用毛筆寫封信”“一張信箋三四句就寫滿了,約稿有時也不用明說”。金性堯先生視陸灝為“暮年知己,不僅僅為文稿事”。施蟄存先生生前還替他擔憂:“我們死光了,誰給你寫?”更打動我的,是陸灝在書里講到的他和《古今》雜志的主編周劭先生的忘年之交。周公滿腹晚清民國掌故,在陸公子約請下寫成不少文章。多少筆底明珠,因陸君未虛擲。
黃裳先生過世時,我看到這樣一則微博:
“The grievance that is beyond words.上午去龍華告別黃裳先生。老先生不希望哭哭啼啼,所以大家在古典樂中鞠躬致敬,獻紅玫瑰。瞅見眼睛紅紅,一直沒說話的陸灝,黑T恤上‘words have no meaning。真是知己。”
博主Sean勵應是勵俊。可補一箋:據黃先生女兒稱,黃裳先生過世前兩三年病中極少說話,只與人筆談,至后來一言不發。
陸灝與前輩的交往令人艷羨,然難學;他與平輩作者的交往可學,然難得。一次與傅月庵先生談天,他推陸為那一輩大陸編輯中第一人。很會寫信。不時寫信問候作者,并及家人。作者拖稿,不催,自己挺過去。偶爾致信,稱在某處見一文章,和我們之前談過您要寫的文章有些相似,或見著您可能需要的資料,寄來供參考。如果覺得文章不夠好,決不妄改,直接致信指出具體何處欠佳,作者自知慚愧,主動改稿。但決不會第二次退稿,自己承受下來。下一次作者肯定會寫來好稿子。
揚之水和陸灝的交誼,我也頗感興趣,一南一北好編輯。《聽水》里陸灝稱她“我的朋友宋遠”。董橋兄為余英時的《中國文化史通釋》寫序說:我和余先生有緣做朋友,靠的也許竟是彼此都抱著“舊文化人”的襟懷。陸揚之交想也如是,氣味相投。愛讀書,勤寫信,一手好字。《〈讀書〉十年》里,揚之水多處記到陸灝給她寄書,她到上海時,陸灝帶她拜訪滬上文化老人。陸灝也曾提起,他到北京時,揚之水和他一人一騎自行車,一天走訪多位作者。我也八卦一下,陸灝和揚之水用的是“情侶包”,上博大克鼎金文紀念手提袋,陸灝送給揚之水的。
陸灝說過,“如果說我崇拜一個人,只有錢鐘書。”讀《聽水》就知道陸公子真是錢先生的高端粉,圣徒狗仔兼之。所謂圣徒,“我所知道的一切,他都在行。可是他還有一個世界,而那個世界我一無所知”。所謂狗仔,“偏愛知道別人不肯給人知道的一部分”。
陸灝連讀書趣味、方法都和錢先生相類。中西通吃,愛抄書,每從書中尋常處讀出別人見不著的趣味。陸灝曾發下“宏愿”,要把《管錐編》中提及的英文書全部找來讀一遍,不知是否遂行。楊絳先生說,錢先生在牛津時,為放松頭腦,每天讀一本偵探小說。陸公子也愛讀偵探小說。他說自己讀法國學者多米尼克·拉波特的《屎的歷史》,“像以前讀福柯的書那樣,采用買櫝還珠的方式,專看書中所引的例子,而對作者的那套理論分析,只能抱歉地原套奉還”。讓人想起錢鐘書先生龐大建筑和木石磚瓦的比喻,“往往整個理論系統剩下來的有價值東西只是一些片斷思想”。
楊絳先生在《〈錢鐘書手稿集〉序》里說,“鐘書自從擺脫了讀學位的羈束,就肆意讀書”甚至“隨遇而讀”。陸公子也在《東寫西讀》后記中說:“讀書是我的一項愛好,對我來說,除了消遣取樂,讀書并沒有其他功效,既不為考試,不為研究,也不是為了寫書評。”在一次訪談里,他說自己特別幸運,從小到大沒人逼他讀書,更沒有誰逼他讀不喜歡的書,換句話說,他沒有讀“傷”過。“我從不憤世嫉俗,讀書時很開心,讀書時可以做古人和外國人。”這開心,便勝卻人間無數。
《聽水》延續了陸公子的風格,毛尖筆下的“萬象特色”:“講故事,不講道理;講迷信,不講科學;講趣味,不講學術;講感情,不講理智;講狐貍,不講刺猬;講潘金蓮,不講武大郎;講黨史里的玫瑰花,不講玫瑰花的覺悟……”小考水滸兵器,統計梁山好漢家小,讓人想起錢鐘書對李元霸兵器重量的津津樂道。為一本一九四五年的舊《大眾》里夾的電影票根,心血來潮跑圖書館翻《申報》電影廣告,享盡錢先生所謂“業余消遣者的隨便和從容”。書中不時冒出的奇想,也很有意思,似乎聽得到陸公子的笑聲,“我曾經有這樣的想法,評論《西游記》是否高明,關鍵看對豬八戒的分析”。
讀陸灝前兩本書,就覺得好玩好看。讀《聽水》,似乎看出了陸灝深藏的眼光。陸公子讀史料,也編定史料。讀掌故,也記錄掌故。他頻頻回顧那個人人各具聲氣的時代,錢鐘書在潘金蓮“老娘這腳”旁批注的“江青所師”,陳寅恪《柳如是別傳》里的“呵呵”“臭尚書”沈曾植捫虱而嚙之,章太炎的書房里“壁上趴著一條碩大的鱷魚標本”,鄧之誠筆下“滿身火氣,宜服清涼散”的陳垣,都不會再有了。他記下的吳祖光先生關于遺忘的故事,黃苗子順走杜月笙家工藝品的軼事,也沒人再聽到。還有胡風舒蕪對一次會面的兩種表述,吳梅和吉川幸次郎對彼此的迥異印象,真相從來只有一個。或許就像書中所說,“歷史的撲朔迷離往往還有另一種現象,表面冠冕堂皇的道理之下,或許只是一些細碎末節的緣由”。正如錢鐘書先生在《一節歷史掌故、一個宗教語言、一篇小說》一文中,引諾法利斯和梅里美的話:“歷史是一個大掌故”“我只喜愛歷史里的掌故”。
有一遺憾,陸灝的日記寫得太精簡,看《梵澄先生》,都是些流水備忘。我剛讀《〈讀書〉十年》那會,一次問起他是否也會出版日記,他說自己的日記僅備以后查檢之用。又問起是否會寫傳,他笑說,等我一百歲的時候吧。我疑心亦期愿另有一版日記,買書記錄,讀書心得,師友交往,臧否人物,正如倫明(哲如)詠鄧之誠的詩,“此外當編今世說,笑嬉怒罵總關情”。
揚之水日記里,她訪梵澄先生,說起陸灝,他說,總覺得太可惜了———人這樣聰明,卻沒有好好攻一門專業,“人總該給這個世界留下一點可以留下的東西”。(《梵澄先生》,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廿八日)我想,陸灝先生應該不會沒考慮過這個問題,可以留下的東西應該已經留下了,不過是在他那個我們一無所知的世界里。
愷蒂其人,“南非”其書
我向來懷疑人能輕易改變,能從別人身上稍微照見自己的形狀,得著一點讓自己完善起來的東西,就值得感恩。這是做編輯給我帶來最大的快樂。認識愷蒂的過程也是如此。
我不是老《萬象》的讀者,愷蒂的文章接觸得晚,早過不四五年前,讀到《南非之南》,一讀進去就特別喜歡,手不釋書呑下薄薄一冊,還沒及緩過神來,她已然坐到我最喜歡的作者群交椅上。找來她寫過的所有書,逆著寫書時間整個讀了一遍,卻好像從頭疏理了自己。
愷蒂是文匯報名記者鄭重的女兒,本名鄭海瑤。自小在安徽宿縣長大,后來在復旦中文系讀完本科,研究生轉到英文系,再到倫敦讀了個電子資訊科學碩士,所以在文理思維間轉換得特別自如。初見時,我說她沒有“文人氣”,她說“我根本就不算是文人,我屬于邏輯思維特強特理性的人”。據她書里的線索(她早期的書評喜歡從自己的經歷切入),可大體補白出她的性情、喜好、感情經歷。二○○○年左右,她受到比較大的挫折,獨自一人去了趟印度。二○○一年底隨南非裔丈夫(她書中偶見的“方思”)到約堡開博物館,宣傳南非作為人類起源的非遺文化。她赴南非時已有一女甜藝(小名豆豆),一子開文尚在襁褓中,兩個孩子是在她寫南非的文章中不可或缺的主角。
去年五月,她舉家搬回倫敦,九月,王為松社長把《南非十年》的書稿交給我,由陸灝先生代理合同事宜。為了有效交流,提前把稿子吃透,我去年底始與她聯系,當晚為傳書中圖片,與她聊了兩個半小時。
她說自己四月份可能要去云南蒙自拍紀錄片,是一家澳大利亞制片公司的片子,拍馬鹿洞最新的考古發現。因為蒙自靠邊境,外國劇組是否能去拍還得等批文。她在全國許多地方都拍過紀錄片。她說,照例外國媒體不用批文,有采訪自由,只要被拍的人接受采訪就行,但是國內許多地方一定要見到紅頭文件才愿意接受采訪。所以,以前她寫過一文,叫《你的自由與我無關》,是拍片子時寫的唯一文章。我建議她寫部關于拍紀錄片的書,她沒置可否。她說有時同時負責好幾個項目,有紀錄片的,展覽的,還有投資的。有的是興趣,有的為養家,例如商務投資的。她在南非的時候在中資能源企業也干過,不只是翻譯,還兼中非“協調員”。這些經歷使她在寫南非經濟相關文章時,能夠掌握第一手資料。
我把初審時發現的十幾個問題反饋給她,她說自己文章里常有錯字,手寫時錯別字更多,是出名的。我覺得是因為她思路太敏捷,看她的文章,常覺得是一氣呵成的,像笑談般流暢。和鄭重老師談過他的文章,他說自己喜歡構思,曾被理科專家稱贊他的文章都有一個精巧的系統。愷蒂的文章粗看不像乃翁,但讀她的長文,尤其是寫格林的幾篇,可知并非信馬由韁,亦自有“系統”。
跟她聊天時,她身在倫敦。她說英國很溫吞,英國人看到什么都很大吃一驚的樣子。在約堡住整天就覺得在刀刃邊上,她卻能把那些如驚悚動作片的場景寫成“一個普普通通的約堡黃昏”。英國雖然boring,晚上可以睡得更安穩。所以,十年非洲之后,還是回英國過boring生活。我說想看看她文章里南非那種夾路接天的藍楹花,她就上網找了張圖發給我。
我告訴她網上能下到她以前的書的PDF,問她是否介意,我可以幫她寫信給平臺商,她說沒有意見,“我相信信息公開”。
她問我有沒有二十五歲?我告訴她我一九八四年生的,并笑問為什么感覺我這么小,她說:“我主要是覺得自己年輕,那年我進大學!”
她把兩個孩子的入學大頭照發給我,和我讀她書時想象的一樣,甜藝機靈,開文乖巧,都特別好看,洋氣,從皮膚看得出混血血統,笑容有“乃母風范”。愷蒂的照片總是笑得特別開,見過一張她年輕時的相片,長辮子,大笑著,像高巖上迎風開的花。
她說她先生是自由職業者,主要是做文化遺產的保護,博物館展覽的設計,也拍紀錄片。她發給我的照片都拍得特別專業,就出自他的手。她建議我問領導多要些預算,我們可以出一本圖錄,每張圖她都能寫一段配文。哎,我不知道有多想!
拿到的書稿,是愷蒂在南非十年文章的合集,字數近四十萬,我猶豫了很久,在跟她商量后拆成了兩冊,一是希望入手感覺更舒服;二來是想通過分擔成本把書做得更精致些。愷蒂已經把書稿分成了社會、生活、文化、經濟、旅游、政治六個板塊,使得分冊工作相對輕松。但我還是把每一篇稿子的字數和所占頁碼單獨統計了一遍。我們美編幫忙設計了版式,并根據每輯的內容,挑選了六幅書中插圖,用PS剜出非洲元素,作成灰度輯封,別致又點題。書名是愷蒂自己定的,一冊叫《南非歌行》,一冊叫《約堡黃昏》。后來李媛手繪了封面畫,耀眼的明暖色調,愷蒂說,乍看比較刺眼,“馬上就讓我想起南非家中院墻上滿滿覆蓋著的如火如荼的九重葛,那般強烈那般耀眼,正如南非,紅色特別紅,紫色特別紫”。
書排出校樣,大概在四月底,愷蒂要到云南拍記錄片,在上海逗留了兩天,我把校樣送到她家里。在四平路鄭重老師家里,我終于見到了愷蒂,她看起來比去年陳子善老師微博上發的照片要瘦黑,皺紋也多了些,不少眼角魚尾,愛笑的人都難免。
她說自己最好的文章都在《書緣·情緣》里,因為那時還沒小孩。鄭重老師也說,那時的文章最好。愷蒂又說,那時還是有些矯情,她更喜歡寫南非的這些文章,跟文藝無關,跟現實更緊密。又說,她在南非的生活非常忙,從下午三點接孩子回家到九點孩子上床睡覺前,都是圍著他們,就晚上寫點專欄文章,可以說百分之九十的時間跟文學都沒有關系。又說自己百分之四十的時間和精力都在孩子身上,后來又改口說,應該是百分之五十。鄭重老師笑說,是百分之五十在兒子身上,百分之四十在女兒身上。
我想到跟一位朋友的交流,我給她看了愷蒂寫的南非文章。她說,離生活近,離夢想遠,不如三毛。我當時覺得她說得有道理,但也并不完全贊成,后來另一位朋友說,這可以說愷蒂比三毛小,也可以說愷蒂比三毛大。為了弄清自己的想法,我找來《撒哈拉的故事》重讀,激情如昨,讀完之后就釋然了,這本是不同人生階段的女人講出的不同的非洲故事。如果非要比較,大概因為我現在的準媽媽身份,大抵是更近愷蒂的。后來書展活動海報上,我寫了一句“三毛帶走南非,愷蒂帶來南非”,一去一來,也有我的心境轉移。
問起她要到云南蒙自做的紀錄片,她說其實她管的都是瑣事,作為制片人而不是導演,要安排好所有的人食宿,打通各種關結,小到租車,大到獲取通關文件,都是她來負責。她說這些天云南都在下雨,那幫澳大利亞人特別著急,擔心沒法按日程表開展工作,她說他們本來就不該花這么多時間來定計劃,這種活動本來最重要的就是“靈活”。又說,導演是和她年紀差不多的女生,第一次拍紀錄片,很緊張,她得每天通過視頻安慰她。又說她擔心澳大利亞因工會力量自由意志太強大,不肯加班,非要做六休一。但晴天難得,天時不待,她就想到為劇組人員安排好的酒店伙食,并把伙食費預算留足,讓他們能夠把當天所得盡收腰包,從而能夠讓這些聽從她的“靈活”安排。她說自己喜歡緊迫感,喜歡為別人解決問題。說者輕松,我聽起來著實佩服。
鄭重老師說,愷蒂朋友特別多,跟誰都能交流。陸灝先生曾在文章里寫到,他曾經問她,英國人是否會歧視外國人,尤其是黃種人?愷蒂回答:“你不把自己當外國人,怎么會覺得別人在歧視你”?這個答案也讓我豁然開朗,無怪她在復旦讀書時就有幸“采訪”過馬爾克斯,在英國、南非也從來沒有浪費過采訪機會,曼德拉、圖圖、西蘇魯,她都曾近距離接觸,故而能自己的獨到看法。陸先生說:“她筆下的英倫文事,就像我們說起魯迅、周作人、張愛玲那樣親切”,“遷往南非后,她來信說起南非的事,又像在說她自己國家的事情———她很快就像南非人那樣生活和思考”。確實是這樣,愷蒂筆下的南非,就像她嘴里的宿縣話、上海話一樣順溜。從安徽到上海到倫敦到南非,她都像風行水上,水在水中。
我問她為什么叫愷蒂,她說這是以前的英文老師取的,寫文章的時候,就覺得應該有個筆名,就用了,一用就粘著了。又說,中國的父母總是對孩子比較挑剔,認為孩子做得不夠好,“我爸爸太有名了,連我老師都認識他。我就不希望他認出我的名字”。現在的書名中,《南非歌行》是書中一篇文章的名字,也是鄭重老師去南非探親時寫下的一首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