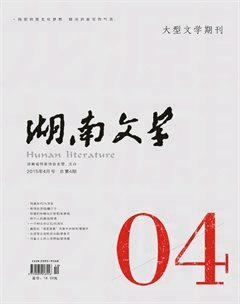超越“活著”之上的精神堅守
李云雷
閻真的《活著之上》,是一部描寫當代高校知識分子生存狀態的力作。小說描述主人公聶志遠從讀博士到被評為教授二十年間的生活,為我們展示了主人公在大學中的人生軌跡,也讓我們看到了當代高校與學術界運行的規則與潛規則。小說中的聶志遠是一位有學術追求的知識分子,但因為不諳學界規則,在人生發展中屢受挫折。然而他以張載、王陽明、曹雪芹等古人為楷模,在窮困中堅守自己的人生理想,最終以真才實學獲得了學界的認可,并在大學中得以安身立命。
與閻真的《滄浪之水》《因為女人》等小說相似,《活著之上》以清醒而細膩的現實主義筆法,對當代知識分子所面臨的諸種社會與文化問題———房子問題,職稱問題,婚戀問題,高校的行政化,以及如何跑項目,如何發文章等等進行了深刻的描摹,舉凡一個青年知識分子可能遇到的問題,在小說中都有所反映,從而在整體上呈現出了當代知識分子所面臨的處境。但不同的是,在這部小說中,閻真筆下的主人公聶志遠并沒有像《滄浪之水》中的池大為、《因為女人》中的柳依依一樣,認可并融入當前的社會結構與秩序,而是在困窘之中仍然保持了一個知識分子的品格與追求,并最終獲得了認可。這一轉變,也顯示了閻真在直面現實之后對理想主義的堅持。但小說中也存在一個問題,我們在作者的敘述與描寫中,可以明顯看到兩種力量的不平衡,學界規則與潛規則的力量遠遠大于聶志遠個人堅守的力量,在這個意義上,聶志遠最后的堅持及其成功,與其說來自他內心的力量,毋寧說來自于作者的愿望與傾向,或者說這是作者在強大的現實面前發出的一聲脆弱的呼喊。
九十年代以來,伴隨著市場經濟與高校科層化管理和學術體制化,當代知識分子一方面將目光從家國命運轉向了專業領域,另一方面也陷入了對高校有效資源的爭奪。在這樣一種社會結構與秩序之下,一個青年知識分子要想獲得認可,不得不適應學界的規則與潛規則。小說中另一位主人公蒙天舒便是適應這些規則的高手,他不僅很快就評上了教授,還當上了學院的副院長;而不諳規則的聶志遠,則處處受制于人,連最基本的生存問題都難以解決,最后只得在規則與理想之間保持了一種脆弱的平衡。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說中我們看到了他的堅守與成功,這可以說是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形象的一個突破。在此之前,我們在賈平凹的《廢都》中看到了知識分子的精神頹敗,在張者的《桃李》中看到了潛規則的無處不在,在何頓的《時代英雄》中看到了知識分子在世俗上的成功,但是在《活著之上》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知識分子超越“活著”之上的精神追求與價值堅守。
在這里,值得關注的另一點是,小說的主人公聶志遠超越“活著”之上所憑借的思想資源,是曹雪芹、王陽明、張載等人所代表的傳統中國文化,而作者所批判的知識分子的世俗化、理性化、個人化———以理性的方式追逐個人利益的最大化,這種思想傾向恰恰是啟蒙現代性的一種后果或產物,也是“五四”以來的啟蒙文化所召喚的一種“理性的個人”的變種。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活著之上》是以傳統中國文化思想資源反思、批判西方啟蒙現代性后果的一部小說,也正是因此,這部小說具有重要的文學史與思想史價值。
整整一百年前,當新文化運動興起時,當時的思想家與文學家以西方現代啟蒙思想為根基,對中國的傳統文化進行了激烈地批判,在這一過程中誕生了中國的“新文學”。在新文學初期,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人物在小說中多以負面或反面的人物形象出現,像魯迅《祝福》中的魯四老爺,就是一個迂腐、頑固、保守的形象,而在巴金的《家》中出現的高老太爺,則更是家族專制與腐朽的一個象征。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中,傳統中國文化及其所塑造的文化人格,大都以這樣的形象出現,傳統中國文化不僅無法成為一種文化理想,更無法對西方啟蒙文化及其現代性展開反思與批判。在這個意義上,閻真《活著之上》的主人公聶志遠以傳統中國文化的代表人物為人生楷模,既是與《祝福》《家》等新文學初期文學作品的一種對話,也是在當前文化整體格局中對傳統文化的重新理解。或者說,作者給我們打開了一種新的文化視野,讓我們可以重新思考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傾向。
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我們崇尚西方文化,崇尚啟蒙,崇尚理性,崇尚個人,但是當這種崇尚所召喚出來的文化人格只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或者只是將個人利益最大化作為追求的人群,那么“啟蒙”及其后果便值得我們深思。而閻真在《活著之上》中,則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文化人格及其理想,那就是中國文化中的“致良知”“君子固窮”“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等傳統。這一傳統及其力量是脆弱的,正如我們在小說中看到的,在現實的利益格局面前它是那么無能為力。但我們也可以看到,重提這一傳統本身就有著重要的意義,它不僅是對抗現實利益的一種精神力量,也是反思西方啟蒙現代性的一種文化理想。而在更寬闊的視野中,這正是中國文化自信的一種表現,或許也預示著一個新的時代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