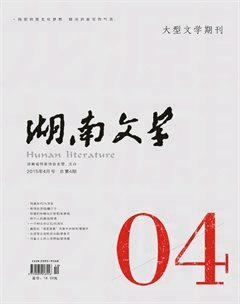活著之上的心靈理由
梁鴻鷹
閻真的創(chuàng)作有明顯理路,那就是知識(shí)分子在現(xiàn)實(shí)物質(zhì)社會(huì)中的遭際,知識(shí)分子在對(duì)抗物質(zhì)利益的誘惑、束縛以及抗?fàn)帟r(shí)所走過(guò)的路程和付出的代價(jià)。在他心目中,知識(shí)分子所持有的立場(chǎng)、良心與品德自然要高出物質(zhì)利益與眼前實(shí)惠,他們應(yīng)該是一群拒絕粗鄙利益、漠視物質(zhì)實(shí)惠的人。當(dāng)年的小說(shuō)《滄浪之水》,是拿孔孟都提到過(guò)的《孺子歌》的“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做了文眼;《因?yàn)榕恕穼?xiě)的是知識(shí)女性精神與肉體的雙重困境,主人公柳依依的命運(yùn)與所走的道路昭示的是當(dāng)下一些女性的無(wú)奈,無(wú)疑很有典型意義和象征意義。先有《滄浪之水》的“逼男為官”,再有《因?yàn)榕恕返摹氨婆疄殒保痘钪稀穼⒃?huà)題投射到高校知識(shí)分子身上,可以概括為“逼教授低頭”,著重探討他們面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選擇之難。
《活著之上》找到了一個(gè)知識(shí)分子潔身自好、遠(yuǎn)離污濁、拒絕利益的精神標(biāo)桿或精神化身,那就是中國(guó)不朽經(jīng)典的創(chuàng)造者曹雪芹。曹雪芹在北京西山窮困潦倒茍活、篳路藍(lán)縷著紅樓,實(shí)際上是用自己的良心抵抗現(xiàn)實(shí)。曹雪芹不求眼前利益,“他選擇了背向主流社會(huì),背向榮華富貴,背向人們所仰慕和渴求的一切。他改變了世界嗎?沒(méi)有。改變了自己的人生嗎?也沒(méi)有。既然沒(méi)有,他的選擇有什么意義?有什么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心靈的理由。”在《活著之上》里,主人公聶致遠(yuǎn)是一個(gè)不肯與現(xiàn)實(shí)同流合污的知識(shí)分子,他經(jīng)常提醒夫人趙平平“能不能什么時(shí)候也朝天空望一眼,想想與自己的日常生活無(wú)關(guān)的事情”,但現(xiàn)實(shí)每每讓他無(wú)法“朝天空望一眼”。他經(jīng)常以曹雪芹的精神給自己提醒、打氣,試圖追求超出自我生存利益的那些東西,但現(xiàn)實(shí)在不少時(shí)候阻擋他、拒絕他,讓他這樣做的可能性變得越來(lái)越小,這恐怕是解讀《活著之上》的一個(gè)重要入口。
作品的思想力量、痛切尖銳之感是無(wú)處不在的。小說(shuō)大部分內(nèi)容說(shuō)的是教育系統(tǒng)、學(xué)校的事情,但作者并非是孤立地、封閉地在寫(xiě)的。其中一個(gè)重要方面是,小說(shuō)里講了那么多有一些小小權(quán)利者的吃、拿、卡、要,但他們?yōu)槭裁磿?huì)這樣做,問(wèn)題只在他們身上嗎?小說(shuō)進(jìn)而挖掘了在我們的傳統(tǒng)中,在我們的文化習(xí)慣中,到底還有哪些東西頑固地活在那里并阻礙著社會(huì)進(jìn)步,哪些東西最要不得。作品試圖將其晾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引起人們的重視。比如聶致遠(yuǎn)回到家鄉(xiāng)魚(yú)尾鎮(zhèn),做漁民的父親也希望當(dāng)上副教授的兒子有“威風(fēng)”,聶致遠(yuǎn)說(shuō)自己是做學(xué)問(wèn)的人,沒(méi)有威風(fēng)。父親反問(wèn)了他一句,“一點(diǎn)威風(fēng)沒(méi)有,要那個(gè)學(xué)問(wèn)有什么用呢?”在不少老百姓看來(lái),權(quán)利無(wú)疑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東西,權(quán)利崇拜似乎已經(jīng)根深蒂固地扎在了每個(gè)老百姓的內(nèi)心。大家都痛恨走后門(mén)、潛規(guī)則、拿好處,但如果自己能夠得到權(quán)利帶來(lái)的實(shí)惠,能夠有威風(fēng)、辦得到別人辦不到的事情,在社會(huì)上比別人吃得開(kāi),那一定會(huì)趨之若鶩、樂(lè)此不疲。作品以人物的家里人、身邊事的具體鮮活,掘開(kāi)官本位、權(quán)利崇拜的全民集體無(wú)意識(shí)的內(nèi)里,指出這種集體無(wú)意識(shí)的危害,提醒人們,這些“傳統(tǒng)意識(shí)”直接造成的社會(huì)病態(tài)和亂象,或許提供了可怕的溫床。
閱讀《活著之上》很讓人感同身受,因?yàn)樽髌放c現(xiàn)實(shí)生活構(gòu)成了很強(qiáng)的互動(dòng)與對(duì)話(huà)關(guān)系。作者揭開(kāi)人們?nèi)粘I畹拿婕啠蠢丈鐣?huì)生活脈絡(luò)之間的聯(lián)系,找出這個(gè)利益與另一個(gè)利益、上一段生活與下一段生活之間的物質(zhì)、人情的聯(lián)系。作者以教育特別是高校為樣本,進(jìn)行了深入剖析、挖掘。由于社會(huì)上的每個(gè)人都要接受學(xué)校培養(yǎng),與高等教育有著千絲萬(wàn)縷的聯(lián)系,在高校這個(gè)知識(shí)階層養(yǎng)成、壯大的地方,人們更期待其成為社會(huì)良心的養(yǎng)成地,教育對(duì)全社會(huì)的覆蓋和影響要實(shí)現(xiàn)正效益化,這是個(gè)太沉重和重要的事情。《活著之上》由此下手,無(wú)疑很有價(jià)值。
在作者看來(lái),讀書(shū)人要有良知、要能夠引領(lǐng)示范于他人。主人公聶遠(yuǎn)志經(jīng)常說(shuō),“作為一個(gè)知識(shí)分子,總得跟街邊炸油條、賣(mài)衣服的人有點(diǎn)不同吧?”他的這個(gè)信念,成了一個(gè)衡量問(wèn)題的自覺(jué)尺度。作品事無(wú)巨細(xì)地描寫(xiě)了在主人公成長(zhǎng)過(guò)程中,不斷“修正”自己,適應(yīng)社會(huì)、屈就現(xiàn)實(shí)的掙扎。從他身上我們發(fā)現(xiàn),原來(lái)在一個(gè)正常的社會(huì)當(dāng)中,居然存在著那么多不正常的東西,知識(shí)分子需要應(yīng)對(duì)那么多與自己對(duì)社會(huì)的信念、道德的信條相沖突的東西,當(dāng)他每次遇到選擇,在用內(nèi)心信念與現(xiàn)實(shí)進(jìn)行對(duì)比的時(shí)候,就會(huì)發(fā)現(xiàn)差距越來(lái)越大,不適應(yīng)感越來(lái)越強(qiáng)。隨著小說(shuō)情節(jié)的進(jìn)展,主人公與現(xiàn)實(shí)的沖突越來(lái)越強(qiáng),作品的思想沖擊力越來(lái)越強(qiáng)。
作品的思想感染力,是由豐富的生活細(xì)節(jié)構(gòu)成與支撐的———那細(xì)枝末節(jié)的生活點(diǎn)滴、對(duì)生活每個(gè)細(xì)部的成功捕捉,有很強(qiáng)的帶入感,產(chǎn)生的都是令人折服的力量。現(xiàn)實(shí)中一些利益輸送、錢(qián)權(quán)交易,由于人們的遷就、放任,會(huì)慢慢地見(jiàn)怪不怪。這種遷就、放任一旦成為常態(tài),污染與危害是極大的。作品寫(xiě)的考研、畢業(yè)、分配、就業(yè)、職稱(chēng)、評(píng)先、提拔等等事情,瑣碎而繁雜,卻為大多數(shù)知識(shí)分子親歷。人們深受其害,深?lèi)和唇^,因此深為認(rèn)同,讀者看了以后會(huì)受到啟發(fā),悟到真相。
作品所著意描寫(xiě)的一個(gè)人的良心能走多遠(yuǎn),精神上挺得住挺不住,靜水流深、驚心動(dòng)魄。作者從不同角度展示了主人公聶志遠(yuǎn)的困境與窘境———他仿佛走進(jìn)一個(gè)價(jià)值迷失的黃昏里、叢林里,他左沖右突,適應(yīng)、反適應(yīng),不斷經(jīng)歷著痛苦的思考與掙扎。作家沒(méi)有孤立地寫(xiě)學(xué)校,他把主人公的成長(zhǎng)放在社會(huì)生活的廣泛聯(lián)系里進(jìn)行考察,在這個(gè)社會(huì)的大系統(tǒng)中,高校這個(gè)看似可以自給自足的地方,實(shí)際上完全不能自洽。來(lái)自社會(huì)大環(huán)境的一切,無(wú)時(shí)不在深刻影響著高校的精神生態(tài)、工作生態(tài)。
作品的批判性不是說(shuō)出來(lái)的,而是從情節(jié)的豐富性中體現(xiàn)出來(lái)的,其藝術(shù)追求上向我們提出的一個(gè)尖銳的課題,那就是,如何達(dá)到小說(shuō)紀(jì)實(shí)性與虛構(gòu)性的融合,在逼真、惟妙惟肖、纖毫畢現(xiàn)之上,在一幅幅細(xì)膩的畫(huà)面、強(qiáng)烈的紀(jì)實(shí)性之上,思想的飽滿(mǎn)、態(tài)度的尖銳,與藝術(shù)的飽滿(mǎn)、自洽始終沒(méi)有分離,這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