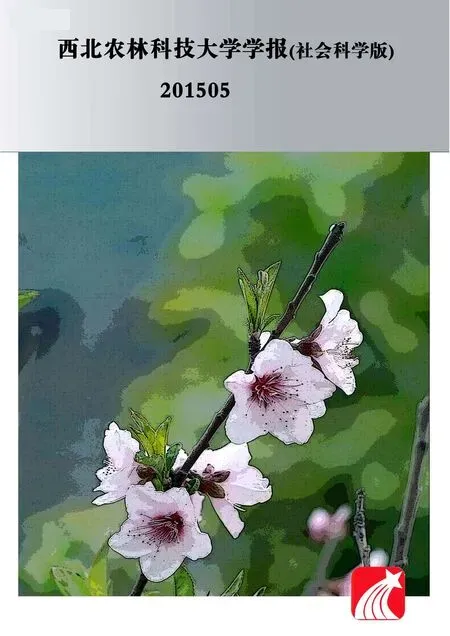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中農地經營權流轉
吳春寶,陳 琴
(1.中央民族大學 管理學院,北京 100081;2.咸寧市委黨校,湖北 咸寧 437000)
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中農地經營權流轉
吳春寶1,陳 琴2*
(1.中央民族大學 管理學院,北京 100081;2.咸寧市委黨校,湖北 咸寧 437000)
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農地經營權流轉與農民工市民化是我國現代化的必然過程。土地規模化經營已然成為中國農業未來的發展趨勢。但由于受農民工自身傳統的土地經營理念、不健全的農地經營權流轉機制、滯后的社會保障體系等因素的制約,當前農民工家庭的土地仍然是“留”多“流”少,這對我國農業生產規模的擴大、生產效率的提高帶來了消極影響。因此,應通過健全流轉機制,規范土地經營權流轉行為;完善保障體系,保障農民工基本土地權益;規制政府行為,維護土地經營權流轉的價格體系等,實現我國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
農民工市民化;土地經營權流轉;城鎮化
一、問題提出與研究綜述
農民工作為農村轉移勞動力的主力,其市民化進程必然給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帶了諸多影響。本文試圖探討在市民化背景下,農民工土地經營權流轉的現狀以及所面臨的困境。
從政策法規角度而言,2014年國家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文件,規范農村土地(本文主要指耕地)經營權的流轉,保護農業轉移人口的切身利益。2014年7月30日國務院頒布了《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意見中明確指出“堅持依法、自愿、有償的原則,引導農業轉移人口有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同時對于進城落戶的農民,意見指出,各級政府應尊重農民的意愿,不得以放棄“三權”作為農民進城落戶的條件。2014年9月2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五次會議,審議并通過了《關于引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意見指出了中國未來土地改革的總體思路,即“三權分置、經營權流轉”,也就是在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促使承包權和經營權分離”的基礎上,形成“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經營權流轉的格局”。
從學術研究層面來看,圍繞我國農地改革方式及其走向,學者們展開了激烈地爭論。但將農業人口轉移與土地經營權流轉二者結合起來的研究成果并不多。經過梳理,筆者發現主要研究成果的觀點有:一是探討土地經營權流轉與市民化關系。一般觀點認為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會推動農民工市民化進程,而當前的土地制度則限制了農民工市民化[1-2],搞活土地經營權流轉不但促進“三化”的協調發展[3],而且釋放農村剩余勞動力,獲取更多的人口紅利[4]。二是在市民化過程中,影響土地經營權流轉的因素。學者們認為農民工的預期收益、打工時間[5]、產權偏好差異[6]以及農民工的收入來源[7]等因素影響著土地經營權的流轉。從根本上來說,農村土地制度安排可通過保險效應和環境舒適度效應影響農民工市民化意愿[8]。三是當前土地經營權流轉導致的困境。在土地經營權流轉實踐中,強推型土地經營權流轉給“被流轉”農戶帶來了市場化困境[9]。綜上,筆者認為在農民工市民化過程中,研究農民工的農地經營權流轉異常迫切。這不但對當前我國的“三化”進程有所推動,而且對農民工切身切身利益的維護也大有裨益。基于此,為了解農市民化背景下農民工家庭土地經營權流轉的現狀,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依托“百村觀察”平臺,在2013年2月對全國30個省的270個村莊958位農民工就土地經營權流轉問題展開了問卷調查和訪談。此次調查共發放問卷1 224份,回收問卷1 200份,其中有效問卷958份*數據說明:本文的有效樣本總量為958個。在問卷分析過程中,分析軟件會將漏填選項的問卷進行自動剔除,這會直接導致我們的分析樣本數會出現少于總樣本數的現象。因此,若無特別說明,文中的數據分析都將按照剔除漏填選項樣本的方法進行。,問卷的有效率為78.27%。在分析此次調研數據的基礎上,筆者將探討當前農民工的農地經營權流轉基本情況,以及土地經營權流轉過程中出現的困境,最后提出切實可行的對策方案。
二、農民工家庭土地經營權流轉現狀
準確而深刻描述農民工土地經營權流轉的現狀,是管窺我國農村土地制度各種癥結的前提與基礎。有鑒于此,筆者將從流轉率、流轉面積、流轉價格、流轉對象、合同簽訂、流轉期限、流轉糾紛等7個方面進行必要的數據分析。
(一)農民工家庭土地經營權流轉率
從農民工家庭承包地的處置情況大致來看,中部地區流轉率最高,東部地區自耕率最高,流轉率最低,西部地區農民工家庭土地拋荒率最高(見表1)。可見,農民工家庭的土地仍以自耕為主,流轉率仍然較低。
表1 農民工家庭承包地的處置情況 %

地區自耕率拋荒率流轉率全國62.0012.1123.90東部67.558.3020.75中部62.5010.2626.31西部50.9624.8421.02
(二)農民工家庭土地經營權流轉面積
農戶土地的流轉有利于土地的規模化經營、推動土地的城鎮化。農民工家庭土地經營權流轉規模反映了農民工在土地經營權流轉市場的活躍情況,通過對農民工家庭承包地流轉面積的調查可知,農民工家庭平均土地租入與租出面積存在一定差異,平均租入面積為4.09畝,平均租出面積為4.21畝,租出面積大于租入面積。可見,農民工家庭土地租出現象更為活躍,農民工家庭更傾向于租出土地。
從不同地區農民工家庭的土地租入情況來看,西部地區農民工家庭平均租入的土地面積最大,為7.34畝;東部地區其次,中部地區最低。西部地區的農民工家庭對土地租入的規模更大,中部地區農民工家庭租入土地的規模偏小。從土地租出情況看,農民工家庭土地租出面積最大的為中部地區,為5.06畝,第二是東部地區,西部地區最少,為2.18畝(見表2)。由此可見,在全國范圍內,中部地區的農民工家庭相比其他兩大區域更傾向于放棄土地、外出打工,將承包地租予其他人。西部地區則相反,該地區農民工家庭更期望擴大農業生產規模,實現規模化經營。
表2 土地經營權流轉面積 畝(個)

地區 流轉類型租入租出全國4.09(40)4.21(193)東部4.14(12)3.23(44)中部2.49(21)5.06(120)西部7.34(7)2.18(29)
(三)農民工家庭土地經營權流轉價格
對于農民工家庭土地經營權流轉價格,從全國看,租入和租出土地的每畝平均價格分別為298.52元和510.85元,租出比租入價格每畝高出了212.33元。一方面說明農民工家庭的土地經營權流轉處于租出方市場,土地出租比較火熱,農民工租出土地的需求旺盛;另一方面,農民工家庭的土地的租出價格與租入價格并不對等。東中西部地區的土地租入價呈遞減趨勢,東部最高,中部其次,西部最低。可以看出租入價格受地區經濟影響。對于租出土地價格,東部和西部地區高于全國平均價格。中部地區農民工家庭的土地租出價格最低(見表3)。可以看出中部地區土地租出的市場需求較小,導致租出價格處于較低水平。也說明中部地區農民工家庭大多不愿放棄土地,不利于該地區的土地規模化、集中化經營。
表3 土地經營權流轉價格 元/畝·年(個)

地區流轉類型租入租出全國298.52(21)510.85(117)東部353.28(7)727.57(34)中部304.00(10)368.86(70)西部258.00(4)707.69(13)
農民是土地經營權流轉的主體,但由于農民很少參加土地經營權流轉的價格的確定,不能成為土地經營權流轉收益的主體而對土地經營權流轉的積極性減弱,對土地經營權流轉的價格不滿情況嚴重。從表4可知,在122份有效樣本中,農民對土地經營權流轉價格表示非常滿意的占比為0.82%;對土地經營權流轉價格比較滿意的比重為11.48%,而表示不太滿意和很不滿意的比重和達到了63.11%。
表4 農民工對土地經營權流轉價格滿意度

流轉價格滿意度 樣本數 占比非常滿意 1 0.82比較滿意 14 11.48一般 30 24.59不太滿意 50 40.98很不滿意 27 22.13
大多數由政府或者村集體和政府一起商定的土地經營權流轉價格并不能滿足農民對土地利益的需求,農民對土地經營權流轉價格不滿情況不容樂觀,這將影響農民對土地經營權流轉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四)農民工家庭的土地經營權流轉對象
從農民工家庭土地租入的對象來看,農民工家庭承包地租入對象為“農戶”和“集體”的比重分別為87.50%和12.50%,從農戶租入的比重遠高于從集體租入。在租入對象為農戶的樣本中,中部地區的占比最高,西部其次,東部最低。土地租入對象為集體的農民工家庭中,東部地區占比最高, 西部其次,中部最少。目前的農民工家庭土地租入對象仍以農戶為主(見表5)。
表5 農民工家庭土地租入對象 %

地區 租入對象農戶集體全國 87.50 12.50東部 66.67 33.33中部 100.00 0.00西部 85.71 14.29
從農民工家庭承包地的租出對象來看,農民工家庭大部分承包地流轉給了“村內農民”(見表6)。可見,農民工家庭更傾向于將土地租給本村內的村民。從地區看,東部地區家庭將土地租給“村內農民”和“本村及集體性質的組織”的比重最高 ,說明在該地區,除了本村村民,本村及集體性質的組織也是農民工家庭的重要租出對象。在中西部兩大地區,將土地租給村內農民的比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村外農民也是農民工家庭租出的選擇對象之一,但比重不高。
表6 農民工家庭土地租出對象 %

租出流轉對象全國東部中部西部村內農民78.6550.0089.0879.31村外農民7.296.826.7210.34本村及集體性質的組織7.8127.272.520.00外村2.086.810.840.00企業0.520.000.003.45其他3.659.090.846.90
(五)農民工家庭的土地經營權流轉合同簽訂
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的正常運行,離不開制度的約束與保障,通過對農民工家庭承包地流轉合同簽訂情況的調查發現,農民工家庭在土地租入和租出過程中未簽訂合同的比重分別為82.50%和86.46%,簽訂了合同的比重不到兩成。從地區看,在土地租入情況下,簽訂合同比重最高的為東部地區,西部其次,最低的中部地區,比重為零。土地租出情況下,東部地區的簽訂比重仍然最高, 西部其次 (見表7)。由此可見,東部地區農民工家庭的土地經營權流轉更為規范有序,農民工家庭的合同簽訂意識更強,中部地區農民工家庭意識薄弱。對于流轉合同的簽訂,農民的重視程度普遍不夠,自我維權意識較差,一方面不利于農民自我權益的保障,另一方面,也危害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市場的健康運行。
表7 土地經營權流轉合同簽訂情況 %(個)

地區土地租入土地租出簽訂未簽訂簽訂未簽訂全國17.50(7)82.50(33)13.54(26)86.46(166)東部41.67(5)58.33(7)36.36(16)63.63(28)中部0(0)100(21)5.04(6)94.96(113)西部28.57(2)71.43(5)13.79(4)86.21(25)
(六)農民工家庭的土地經營權流轉期限
對農民工家庭承包地流轉期限的調查顯示,承包地租入與租出年限存在一定差異。從全國來看,租入土地的平均期限為5.68年,租出土地的平均期限為2.67年,租入期限高于租出期限。同時,土地經營權流轉期限在各地區呈現不同的趨勢,在租入土地的情況下,東部地區的流轉期限最高,西部其次,中部期限最低,為2.4年。東部地區租入期限明顯高于中西地區。在租出情況下,租出年限最高的仍為東部地區(見表8)。
表8 土地經營權流轉期限統計 年(個)

地區流轉類型租入租出全國5.68(19)2.67(93)東部8.30(10)3.21(39)中部2.40(5)2.31(36)西部3.25(4)2.22(18)
東部地區農民工家庭的土地經營權流轉期限均高于其他地區,這也一定程度反映出東部地區農民工對土地的依賴性較中西部農民工小。
(七)農民工家庭的土地經營權流轉糾紛
土地經營權流轉糾紛是目前我國農村社會發生矛盾糾紛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農村人地矛盾、土地經營權流轉行為不規范、產權制度不清晰又進一步激化土地經營權流轉糾紛。尤其是在農村土地向非農用地的流轉過程中,一般有地方政府、村集體決定土地價格、補償金額、補償方式,很少能真正考慮和涉及農民的土地經營權流轉收益,這也激發了征地過程中,農民與政府或村集體之間的矛盾糾紛。從表9的數據分析表明,在流轉過程中,43.9%的農民與政府或村集體發生過糾紛事件,接近一半的糾紛事件發生率表明,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糾紛激化已不容忽視。
表9 農民工與政府或村集體發生糾紛情況

糾紛樣本數占比發生過5443.9沒發生過6956.1
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不僅需要土地交易市場的健全和完善,也需要行政部門的管理和監督。當前,土地經營權流轉的制度還不健全,土地經營權流轉的法律法規還不完善,行政部門對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的管理和監督還很薄弱,對土地經營權流轉糾紛的協調不夠,導致在處理糾紛時,農民往往找村干部或鄉鎮干部協商,有些直接上訪尋求解決辦法(見表10)。
表10 土地經營權流轉糾紛解決情況

流轉糾紛解決方式樣本數占比找村干部協商解決2746.55找鄉鎮干部協商解決610.34找法院解決00.00上訪解決1627.59不了了之915.52
由表10可知,農民在處理土地經營權流轉糾紛時,向村干部或鄉鎮干部協商解決的比重最大,其次是上訪解決 , 沒有人找法院解決 。由此可見,與基層干部協商成為處理土地經營權流轉糾紛的主要途徑和解決辦法,土地管理部分的職能沒有發揮,土地經營權流轉的相關部門沒有有效的處理糾紛。
三、農民工家庭土地經營權流轉困境
當前農民工家庭土地經營權流轉受到各種因素制約,使得土地經營權流轉進程出現了諸多問題,特別是在流轉服務、流轉程序、流轉保障體系以及流轉價格形成機制等方面。具體而言,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流轉服務不健全
土地經營權流轉中介服務體系不健全,土地供求雙方的信息無法流通,土地經營權流轉很少有中介機構介入,流轉一般在熟人之間進行,沒有利用市場對土地經營權流轉進行規范。從農民工家庭承包地流轉是否存在中間人的情況看,農民工家庭承包地租入時,存在中間人的比重為15.38%;承包地租出時,存在中間人的比重為7.04%(見表11)。
表11 土地經營權流轉存在中間人情況 %(個)

土地經營權流轉中間人是否存在中間人是否合計租入中間人15.3884.62100(26)租出中間人7.0492.96100(142)
可見,農民工家庭土地經營權流轉時,很少有中介組織介入或者中間人進行協調交易。農民工家庭土地經營權流轉多為私下交易的方式來轉包或轉租土地。這種交易往往沒有任何法律可循,也沒有任何監督機構保證運作,農民工家庭的土地權益也得不到保障。
(二)流轉程序不規范
現階段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市場不健全,土地經營權流轉交易組織培育不完善,導致土地經營權流轉行為不規范的現象普遍存在。即便是簽訂了合同的土地經營權流轉中,也有合同內容不規范、不齊全的現象出現。
(三)流轉價格不合理
要提高農民工土地經營權流轉的積極性,土地經營權流轉的利益分配公正合理是至關重要的環節。然而,目前我國農村地區土地經營權流轉市場機制不健全,交易組織發育不完善,土地經營權流轉的價格等都無法根據市場供求而定。土地經營權流轉收益分配混亂,農民無法享受應該得到的土地經營權流轉收益,從而引發農民對土地經營權流轉不積極,甚至抵觸的情緒。
從表12可以看到,農民土地經營權流轉過程中,土地經營權流轉的價格不是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控制的,大多數是由政府依據行政命令統一規定。在122個有效樣本中,由上級政府統一規定的比重為72.13%,由村干部和政府商量決定的比重達到22.13%,而由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會議討論決定的比例僅為4.1%。可見,土地經營權流轉的實際過程中,農民工作為土地經營權流轉的主體,卻無法以主體的身份參與土地經營權流轉價格的確定,無法享受到土地經營權流轉的最大收益。
表12 土地經營權流轉價格確定情況

確定方式樣本數占比上級政府統一規定8872.13村干部和政府商量決定2722.13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會議討論決定21.64其他方式54.1
(四)保障體系不完善
當問及“土地經營權流轉或征用后您最擔心的問題”時,僅28.57%的農民工表示沒有什么擔憂,42.31%的農民工表示最擔心因土地得到的經濟利益受損,占比最大。其次是擔心失地后的養老問題,選擇此項的農民工占比為15.93%(見表13)。
表13 農民工失地后最擔心的問題 %

擔憂的問題沒有擔憂后代生活就業養老經濟利益受損其他合計占比28.576.035.4915.9342.311.65100.00有效樣本數52111029773182
這說明由于收入和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擔心失地后經濟利益受損和失地后失去生活保障可能是農民工不愿意放棄或是流轉土地的最大原因。
四、促進農民工家庭土地經營權流轉的對策
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土地規模化經營成為中國農業發展的未來趨勢。但是,目前我國農民工家庭存在著大量零散的耕地,且農民工的土地經營權流轉意愿較低,農民工家庭的土地經營權流轉程度不高,流轉的糾紛也較多,這些問題都導致了農民工家庭的土地利用粗放,阻礙了農業規模經濟的發展。筆者認為,通過促進土地經營權流轉來推進農民工家庭土地的規模化經營,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實現:
1.健全流轉機制,規范土地經營權流轉行為。第一,培育土地經營權流轉服務組織。土地經營權流轉服務組織,為農民工提供土地經營權流轉的服務咨詢,引導農民工依照合法的程序,遵循自愿原則,經過雙方簽訂土地經營權流轉合同,明確土地經營權流轉雙方的權利和義務,完成土地經營權流轉。第二,完善土地經營權流轉配套制度。這主要包括土地經營權流轉的備案登記制度、土地經營權流轉儲備庫制度、流轉收益分配制度、保險制度。完備的土地經營權流轉制度為農民工土地產權流轉行為建立了基本規范,從而在根本上協調土地經營權流轉中各方經濟利益關系,切實維護經營者利益。第三,健全流轉糾紛調處機制。科學規范的土地經營權流轉需要完備的糾紛協調、仲裁機制以及責任問責制等一系列措施。通過制訂調解仲裁工作制度,抓好調解仲裁庭硬件建設,按照仲裁程序規范操作、依法辦理,逐步健全和完善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糾紛仲裁工作機制,減少土地經營權流轉糾紛。
2.完善保障體系,保障農民工基本土地權益。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缺失,使農民將生活寄望于土地,只有逐步建立和完善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為走出土地的農民解除后顧之憂,土地使用權流轉的市場才會建立健全。一方面,消除現行戶籍制度的限制。二元戶籍制度是農民工無法享有社會保障的根本原因之一。戶籍與基本公共服務相掛鉤,致使農民工增加了對土地經營權流轉的顧慮,加之市民化致使農民工的社會身份變得更加尬尷。另一方面,建立和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社會保障體系是社會發展的安全閥,是維護社會穩定的基本手段。在促進農民工土地經營權流轉過程中,我國應健全當下涉農的社會保障體系。這主要涉及到醫療社會保險、養老社會保險、失業保險以及社會救助制度等諸多方面。
3.規制政府行為,維護土地經營權流轉的價格體系。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是農民的自發行為,應遵循農民自己的意愿。一般而言,價格體系形成受到市場基本規律支配。在市民化背景下,農民工的土地經營權的流轉應更加自主。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中就指出“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這一方面充分說明市場在土地經營權流轉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們在市場運作中,應注意防范的內容,即:切勿將市場化的趨勢與發展方向極端化。具體而言,土地經營權流轉價格的形成機制,離不開市場基礎作用的發揮。該過程不是政府推動下的“強制市場化”“拉郎配”,更不是政府的自由放任,不作為。因此,在土地經營權流轉的價格體系形成過程中,應適度規范政府行為。在進一步界定政府、市場二者的行為邊界的基礎上,我們應構建二者的良性互動機制。政府應按照“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從社會環境的營造、經濟市場平臺的搭建以及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等方面入手,為農民工土地經營權流轉提供各種服務,通過“賦權、放權、維權”等行為,激發土地經營權流轉市場的活力,積極推動我國農村土地改革進程。
五、結語及討論
當前無論是各級政府還是學界,對我國農村農地經營權流轉都給予了大量關注。本研究亦是立足于我國“三農問題”實際,對農民農地經營權流轉行為進行的實證分析。本文試圖從全國范圍內對農民工的土地經營權流轉的基本特征進行必要的定量研究,以彌補當前學界對土地經營權流轉研究不足。毋庸諱言,作為一種學術嘗試,該研究成果與其他成果一樣難免存在一定的瑕疵。這是由研究對象的復雜性所決定的。鑒于對學術研究的嚴謹性,筆者認為有責任對其進行必要的解釋,為其他學者進行后續研究提供必要借鑒。
1.樣本數據采集的有限性。本數據是嚴格按照隨機抽樣的方法從全國整體樣本中提取的農民工樣本數。這不是只針對農民工所進行的一次全面性土地流轉調查,存在抽樣不均衡的情況,例如說按照地域分類,有些地區的有效樣本數僅有幾個,而其他地區的有效樣本數可能或出現上百個。這從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我們分析結果的邏輯性及嚴密性。
2.樣本數據分析的表面性。通過SPSS17.0軟件,以簡單的頻數分析,加之以相關性分析及交叉性分析,并沒有開展較為深層次的線性回歸分析。這有可能直接導致對我國當前農民工農地經營權流轉問題分析的表面化、一般化,很難深刻把握諸多影響制約農民工農地經營權流轉行為背后的決定性因素。
3.樣本標準分類的不確定性。數據不是萬能的,它并不能涵蓋我國農民工農地經營權流轉行為的全部特征,因此,這可能導致我們的研究結論現象化。
[1] 趙云.促進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 推動農民工市民化[J].人民論壇,2014(7):72-74.
[2] 呂文靜.論我國新型城鎮化、農村勞動力轉移與農民工市民化的困境與政策保障[J].農業現代化研究,2014(1):57-61.
[3] 楊群.土地經營權流轉:實現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J].學術交流,2013(2):96-99.
[4] 孟令國,余水燕.土地流轉與農村勞動力轉移:基于人口紅利的視角[J].廣東財經大學學報,2014(2):61-66.
[5] 何軍,李慶.代際差異視角下的農民工土地經營權流轉行為研究[J].農業技術經濟,2014(1):65-72.
[6] 徐美銀.農民階層分化、產權偏好差異與土地經營權流轉意愿[J].社會科學,2013(1):56-66.
[7] 賀書霞.外出務工、土地經營權流轉與農業適度規模經營[J].江西社會科學,2014(2):60-66.
[8] 黃忠華,杜雪君.農村土地制度安排是否阻礙農民工市民化:托達羅模型拓展和義烏市實證分析[J].土地科學,2014(7):31-38.
[9] 孫新華.強制商品化:“被流轉”農戶的市場化困境——基于五省六地的調查[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5):25-31.
Transfer of Farmland Operation Right From Perspective of Migrant Workers’ Citizenization: Present Situation, Dilemma and Countermeasures
WU Chun-bao1,CHEN Qin2*
(1.SchoolofManagement,MINZU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081; 2.XianningPoliticalSchool,Xianning,Hubei437000,China)
In the context of new urbanization, the transfer of farmland operation right and the migrant workers’citizenization are inevitable process, the standardized operation on farmland has become the trend of China’s agriculture. But in view of some restraints such as the “land-holding” operation concept (The ownership and operation right of land can not be separated)of migrant workers is difficult to break; farmland transfer mechanism a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re not perfect, then the farmland of migrant workers’families is rather to be “held”than to be “transferred”, which i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xpans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cale and improvement of production efficiency. Based on above reasons, we can transform the “land-holding”concept of migrant workers by strengthening the leading function of policy, regulating the migrant workers’ transfer behavior by improving the transfer mechanism, eliminating the worries of migrant workers by perfecting security system, thus to achieve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land resources and protect migrant work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land.
migrant workers’ citizenization; transfer of farmland operation right; urbanization
2015-01-11
西藏大學珠峰學者人才發展支持計劃“青年骨干教師”項目
吳春寶(1984-),男,西藏大學思政部講師,中央民族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民族政治學、“三農”問題。
F323.11
A
1009-9107(2015)05-0020-06
*通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