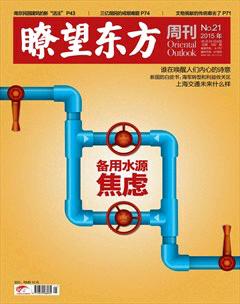室蘭衰落的啟示(上)
關田剛司
時隔20余年,我第一次重返祖母的老家——北海道室蘭市。
這里是我小時候生活過的地方,上世紀80年代初是一片欣欣向榮的熱土,日本的重工業基地之一,不但有新日鐵、日鋼等“龍頭企業”,還有楢崎造船、煉油廠等其他日本特大企業。一到傍晚,鎮上唯一的商業街總是人山人海,餐館、酒吧生意紅火,那種熱鬧的場面讓我至今記憶猶新。
那時候,室蘭市的總人口也就15萬左右,加上外來務工者也不過20萬人,完全不能滿足以重工業為龍頭企業的城市勞動力需求。但好在當時整個北海道的人口數量正處于高峰期,室蘭市還可以從道內其他地區“引進”勞動力,勉強填補不足。
即使如此,也還遠遠解決不了如火如荼的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很多在校學生于是加入進來,課后或周末去工廠打工賺錢。我也在楢崎造船廠打過工,從來沒有做過電焊活的我,一上班就直接被派去做電焊工,弄得手忙腳亂滿頭大汗,從中可以想見企業對勞動力的渴求多么迫切。
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中韓兩國以及北海道周邊地區的制造業日益崛起,再加上當地人口數量逐步下降、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室蘭逐漸風光不再,曾經熱鬧的商業街開始門庭冷落。
之后,我也離開室蘭,到札幌去讀書,然后去東京工作,又離開日本來到中國。
20多年后再回去,這座讓我時時憶起的小城呈現出的是一種死氣沉沉的景象。人丁冷落的街頭,三三兩兩的行人大多是中老年人,很少看到年輕人。與20年前相比,這里的人口少了近四成,空氣質量倒是比以前好了,但一位在公交車站候車的老人跟我聊天時卻嘆息說:“空氣再好也不能當飯吃啊……”
室蘭的衰落,并不僅僅是個經濟增長率的問題。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進入“泡沫經濟”時代,一開始人們總是把它歸咎于產業結構不合理、內需擴大不給力、高科技產品開發遲滯、對外貿易逆差以及“廣場協議”導致日幣升值等經濟因素,并未注意到老齡化加劇和勞動人口減少這兩個更直接的原因。
就這樣,一直拖到2007年,當時的安倍內閣才意識到“少子化”的嚴重后果,在內閣設立專門的對策部門,但是已經為時過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