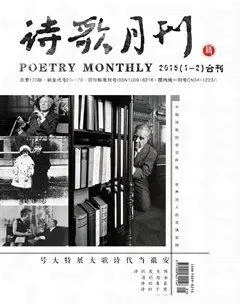語言規(guī)約和言語化
余怒
對(duì)實(shí)在的感受和認(rèn)知是語言的結(jié)果。這種反果為因的結(jié)論總是使我們心有不甘,但真實(shí)情形又似乎是。在思維被語言清洗和同質(zhì)化之前,作為族群中的個(gè)體的意識(shí)一直處在一種混沌的、飄忽不定的晦暗狀態(tài);對(duì)于實(shí)在,他感覺到了什么,但它是無形的、邊際發(fā)散的而中心互斥的,無法在意識(shí)領(lǐng)域予以捕捉、辨識(shí)、闡明,并明確給它以展示、定義和復(fù)述(因?yàn)橥愔g尚沒有發(fā)明出一種用以傳遞信息和交流情感的公共符號(hào)),更談不上推演于他人;那時(shí)他是自由的、孤獨(dú)的,被包裹在純粹的自我的身體感觸里。但自從有了語言,模糊的感受和認(rèn)知便在意識(shí)領(lǐng)域被集體化的語言潤色、補(bǔ)缺或剔除,經(jīng)過一番整理之后,以一種口徑統(tǒng)一、語法規(guī)范、意指明確的方式重新“現(xiàn)身”,當(dāng)感受和認(rèn)知被我們意識(shí)到的時(shí)候,它已經(jīng)從不可言說之物變成了可言說之物。感受、認(rèn)知與語言之間交纏難分,互為表里,使得前者“先天性”地帶有某種言說性質(zhì)。索緒爾曾就思想與語言之間的這種關(guān)系說過這樣一番話:“從心理學(xué)上看,思想如果離開了詞的表達(dá),那么就只是毫無形狀的、模糊的一團(tuán)。哲學(xué)家和語言學(xué)家一直認(rèn)為如果沒有符號(hào)的幫助,我們有可能無法清楚明了地將這兩個(gè)概念區(qū)別開來。沒有語言,思想就是一團(tuán)模糊不堪的星云。沒有預(yù)先存在的觀念,而且語言出現(xiàn)之前,一切都是不夠清楚的。”只要我們一思考或開口說話,語言就作為記憶的伴隨物進(jìn)入到我們的意識(shí)領(lǐng)域,那種感受之初的感受因受到語言的干擾而被扭曲,我們的感受就不再只屬于純粹的“自己”,我們卻渾然不覺,將之認(rèn)領(lǐng)為“自己”的感受。語言是感受的鑄鐵模具,而感受卻是不可描述的、無法自己“現(xiàn)身”的鐵水——也許什么都不是。在語言教育過程中,嬰兒被哺育者的話語引領(lǐng)著,從片言只語的言語狀態(tài)逐漸進(jìn)入語義完整的語言狀態(tài)。前一種狀態(tài)尚帶有體驗(yàn)描述的成分,后一種狀態(tài)這一成分便漸漸減少——語義越完整,這一成分越是稀少。語言教育的過程就是自我逐漸散失的過程,個(gè)體感受被排斥,個(gè)人言語所剩無幾,我們已經(jīng)說出的、即將說出的,甚至心中默念的都是他人的話語,在這些話語中我們總能隱約聽到來自遙遠(yuǎn)歷史深處的某個(gè)人或某一群人的聲音,我們只是訓(xùn)練有素的話語復(fù)制者和意義的繁衍工具,這一點(diǎn)實(shí)在令人沮喪。
在索緒爾看來,語言是一種規(guī)約,是言語中確定的部分,而不是說話者的功能,它存在于每一個(gè)個(gè)體中,為所有人所共有,不為存儲(chǔ)者的意志所左右,它是一個(gè)自足的整體和一套分類原則。語言規(guī)約涉及語言的語法結(jié)構(gòu)、隱喻體系、賦意方式和敘述規(guī)范等。而言語卻是個(gè)人的、臨時(shí)的、地域的、方言的、口語的、非語法的、非邏輯的、多維的、種類龐雜的、異質(zhì)的(在不同個(gè)體之間),無同一性的規(guī)律可循。
我在一篇文章中談?wù)撨^言語的屬性和言語向語言轉(zhuǎn)化的過程,“在日常對(duì)話中,不斷游離于話題的陳述、顛三倒四的敘事、靈活多變的句式、個(gè)人化的語法、突然穿插進(jìn)來的無意義的詞語、不同人物的語調(diào)、莫名其妙的喟嘆,這一切組成了一幅紛亂的自然的原生態(tài)的言說圖景。”“從言語到語言,是一個(gè)持續(xù)規(guī)范化、書面化的過程,先前的口語經(jīng)過書面使用,相當(dāng)大的部分可能轉(zhuǎn)化為書面語,日常口語中的個(gè)人體驗(yàn)漸漸演變成可復(fù)述的、作者讀者雙方認(rèn)同的知識(shí)的定論,口語的隨意靈活、粗礪和不合語法的特征也隨之喪失,變得整飭、圓潤、中規(guī)中矩。公文的應(yīng)用、媒體的宣傳乃至寫作者的寫作都在這書面化進(jìn)程中扮演著或自愿或無奈的異曲同工的合謀角色,因?yàn)檫@一進(jìn)程本身是超越語言使用者的意志的客觀實(shí)在。”
自然語言的規(guī)約為同一語言集體中所有人所共知,政治、哲學(xué)、科學(xué)、藝術(shù)等語言的規(guī)約為分類的各行業(yè)中的人士所共知,更小范圍內(nèi)的文學(xué)、詩歌語言的規(guī)約為文學(xué)家、詩人、文學(xué)(詩歌)愛好者所共知。當(dāng)然,分類的語言規(guī)約會(huì)程度不一地傳播至不同類別的接受者那里。這些專業(yè)語言規(guī)約除了服從于自然語言的規(guī)約之外,還有著“類型話語”自身專業(yè)的獨(dú)特的規(guī)約,傳播者與接受者之間交流的效果取決于后者對(duì)后一種規(guī)約的知曉程度。這就像觀眾觀看象棋比賽,他們對(duì)棋手的棋局和棋步的讀解和領(lǐng)會(huì)往往會(huì)因其擁有的專業(yè)知識(shí)水平而異,不懂或略知或熟知象棋基本規(guī)則和棋譜的、象棋愛好者、業(yè)余棋手、專業(yè)棋手、象棋大師,他們對(duì)該棋手的布局和某一著棋的拙劣或妙處的認(rèn)知千差萬別。各類型文本的讀者也是如此。
每個(gè)語言集體都有著自己的語言規(guī)約,不同語言集體的語言規(guī)約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一門語言中的語言翻譯到另一門語言中有可能只是一些言語,反過來,一門語言中的言語被放置到另一門語言中有可能就成了語言。毫無疑問,翻譯語言要受到“目的語言”的制約,當(dāng)它在后者中找到了同構(gòu)或相似的規(guī)約時(shí),翻譯過程就會(huì)顯得輕而易舉;反之它就只好采取保留原文句法形式的直譯的方式。直譯文本會(huì)退而求其次地在“目的語言集體”的言語中尋找相應(yīng)的對(duì)等形式,如果尋找到了,它也會(huì)被接受者在與言語的比較中接受,反之會(huì)被排斥。一旦譯文尋找到了對(duì)等形式并且被普遍接受,它就會(huì)被納入“目的語言集體”的語言規(guī)約中,成為一項(xiàng)新的規(guī)約內(nèi)容。在這個(gè)意義上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說,一切外來語都是漢語;因?yàn)樗鼈兌伎梢栽跐h語(語言和言語)中找到可供理解的形式的模型或蹤跡(確切地說是語言模型或言語蹤跡)。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譯文被理解的情況發(fā)生。
處于我們之外的另一個(gè)語言集體的思維方式和表意方式常常令我們感到驚訝。倫瓜印第安人在殺死一只鴕鳥后,采取一些欺騙死鴕鳥懷恨的鬼魂的做法。他們認(rèn)為鴕鳥剛剛死去時(shí),會(huì)追趕自己的軀體。于是他們將鴕鳥胸前的羽毛拔下來,沿路隔不多遠(yuǎn)撒一些。鬼魂遇到每一堆羽毛都會(huì)停下來考慮一下:“這是我全部的身體,還是身體的一部分?”懷疑使它停下來,對(duì)所有的羽毛作出判斷,一堆一堆的羽毛使它不得不走彎彎曲曲的“之”字路,浪費(fèi)了許多寶貴的時(shí)間。這樣,獵人就會(huì)安全地回到家里,而這個(gè)尖嘴巴的鴕鳥的鬼魂在村子周圍游蕩。它很膽小,是不敢進(jìn)入村子里的。還有一些原始部落的人認(rèn)為動(dòng)物死后,骨頭上會(huì)長出肉,會(huì)在來年再次復(fù)活,于是他們細(xì)心地把骨頭、碎塊、污物收集到一起埋起來。列維·斯特勞斯在論述“原始人”的思維時(shí)曾引用過人類學(xué)家鮑阿斯的文章,其中談及契努克印第安語一些奇特的描述方式,比如陳述句“這個(gè)惡人殺死了那個(gè)窮孩子”,譯成契努克語就是:“這個(gè)人的惡性殺死了那個(gè)孩子的貧窮。”他們把“這個(gè)女人使用過一個(gè)很小的籃子”這句話說成:“她把委陵菜根放入一個(gè)籃子的小中。”。
盡管這種被列維一布留爾統(tǒng)稱為“原始思維”的思維方式和言說方式與我們的思維方式和言說方式相距甚遠(yuǎn)——我們常常將書本上和日常生活中的這種陳述說成是語序顛倒的病句,但這種陳述在我們看來仍然是饒有意味的——我相信,大多數(shù)詩歌寫作者都會(huì)體會(huì)到其中的新鮮靈動(dòng)和勃勃生機(jī),并從中得到啟發(fā)。這種獨(dú)特的抽象的陳述會(huì)把我們從習(xí)慣的句法鐐銬和表意藩籬中解放出來,對(duì)實(shí)在的描述的惟一性也將會(huì)被重新審視和質(zhì)疑。那么,它是否正是我們一直苦苦尋覓卻無法給以適當(dāng)定義的“詩性”呢?或者是其中一種?在那里,是否隱藏著為我們的詩歌語言規(guī)約所剔除,而為我們的言語居所所容留的東西呢?我們能否將“詩性”界定成作為為個(gè)體辯護(hù)的言語對(duì)思維同一性、同質(zhì)性和語言政治的藝術(shù)性制衡方式呢?更有意思的是,我們常常能在一個(gè)瘋子的話語中嗅到一絲詩性的氣息。它何以被看作是“詩”的?是否它無意間呈現(xiàn)出了那么一種自發(fā)的、“元思維”的、非邏輯的“言語狀態(tài)”呢?
語言及其規(guī)約不是一成不變的,它隨著時(shí)間,隨著舊的分類原則和條款的淘汰和新的分類原則和條款的出現(xiàn)而不斷變化——有時(shí)還會(huì)出現(xiàn)反復(fù)。語言規(guī)約就像一個(gè)進(jìn)出流量不等的蓄水池,時(shí)刻在流進(jìn)流出,但在一個(gè)時(shí)間段里,蓄水量總是保持著大致的均衡。可能在某一段時(shí)間,進(jìn)水流量會(huì)突然大增(如國門洞開之時(shí)),新的語匯和描述方式大量涌入,蓄水量刷新歷史水位,但經(jīng)過一段時(shí)間的調(diào)整、沉淀、排水,蓄水池又將回到正常的水位——即回到語言及其形式足夠滿足我們賦意言說需要的那么一種狀態(tài)。
歷史地看,文學(xué)在自然語言規(guī)約的形成過程中發(fā)揮了很大的作用,這一點(diǎn),我們可以從現(xiàn)代漢語的出現(xiàn),以及逐漸成型的進(jìn)程中更加清楚地看到。一代代作家為現(xiàn)代漢語的語法、敘述的規(guī)范化提供了豐富的樣本,它們也間接地成了政治、經(jīng)濟(jì)、科技、新聞諸領(lǐng)域話語的原始母本。但同時(shí)我們也看到一個(gè)奇怪而有趣的現(xiàn)象,即對(duì)語言規(guī)約貢獻(xiàn)得越多,這個(gè)作家的生命力和享受到的后輩作家的尊重越顯得微弱。比較一下茅盾和魯迅,徐志摩和卞之琳這兩對(duì)作家,相對(duì)來看,茅盾和徐志摩對(duì)自然語言和各自領(lǐng)域的語言規(guī)約的貢獻(xiàn)要大于魯迅和卞之琳,前二者的語言范式更多地為本專業(yè)和其他領(lǐng)域的作者所沿用,而后二者較少。即使像魯迅這樣家喻戶曉的人物,他的語言范式仍不能成為主流語文和主流文學(xué)。對(duì)于作家來說,始終有兩種評(píng)價(jià)體系縱橫于他們的心中,一個(gè)是非專業(yè)的、主流的、大眾的評(píng)價(jià)體系,一個(gè)是專業(yè)的、非主流的、同行間的評(píng)價(jià)體系。而文學(xué)領(lǐng)域之外的人士(包括文學(xué)愛好者、業(yè)余作家)一般只有前一種評(píng)價(jià)體系。對(duì)于專業(yè)的作家來說,前一種體系中的強(qiáng)力作家,在后一種體系中可能就成了無關(guān)緊要的甚至遭唾棄的作家。相反,在文學(xué)領(lǐng)域之外的人士眼中較弱小的、不為他們所知曉的作家可能正是作家們景仰的強(qiáng)力作家。那么,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說:那些容易被規(guī)約或者說離規(guī)約較近的作家也容易被后輩作家拋棄呢?當(dāng)后輩作家在前輩作家那里學(xué)不到普及的技藝之外的技藝,后者便“死了”。你的棋路都是棋譜上載明的——即使你是棋譜作者,甚至眾所周知的,哪個(gè)棋手會(huì)向你拜師學(xué)藝?
一般說來,由于對(duì)獨(dú)特性和原創(chuàng)力的要求,文學(xué)規(guī)約的價(jià)值與它的傳播范圍成反比,即傳播范圍越廣,它在寫作者心目中的位置越為次要。當(dāng)它在文學(xué)領(lǐng)域內(nèi)部傳播時(shí),它的生命力仍然強(qiáng)勁,盡管不如它剛剛出現(xiàn)時(shí)那么引人奪目。當(dāng)它延伸至大眾話語空間,成為文學(xué)史學(xué)和大眾審美的對(duì)象時(shí),它就壽終正寢了。一種規(guī)約一旦被普及化,就意味著新的與之相反的規(guī)約即將登場。當(dāng)朦朧詩的“星星的彈孔”式隱喻成為文藝晚會(huì)和卡拉OK里的主題,當(dāng)“口語詩”的語感形式和線型敘述成為千萬網(wǎng)民的自娛日記,它們的命運(yùn)便可想而知。詩性或者說文學(xué)性,正在于對(duì)詩歌(文學(xué))規(guī)約的偏離,當(dāng)這種規(guī)約達(dá)到普及程度,弱小的聲音就開始醞釀反叛,由此會(huì)帶來極端的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我們多次看到一些經(jīng)典詩人陷入同時(shí)身為歷史中的強(qiáng)力詩人和同行眼中的“小詩人”的尷尬境地。他們“泯然眾人”的原因在于眾人在他們的啟蒙下長大了,而他們的“智力”仍然未曾增長。對(duì)這種情形所持的態(tài)度不單單來自布魯姆為之提出六種“修正比”的“影響的焦慮”,更關(guān)鍵的來自作者對(duì)借以言說的語言的焦慮,來自對(duì)意義本質(zhì)及賦意方式、描述規(guī)范的先天性不信任。文學(xué)史上發(fā)生的以“嘮叨”對(duì)抗雄辯,以“噪音”對(duì)抗美聲,以“拼貼”對(duì)抗完整,以及反反復(fù)復(fù)的以朦朧對(duì)抗清晰,以翻新的清晰對(duì)抗朦朧,其原因就在于此。
由于語言是言語中確定的東西,當(dāng)它面臨更新和修訂時(shí),必然要回到言語中去找尋;在個(gè)人的、臨時(shí)的、地域的、方言的、口語的言語中找尋新的可用以規(guī)約的東西,有時(shí)也會(huì)到另一個(gè)語言集體中去找尋——前面提到過,前提是譯文能夠在我們自己的語言中找到對(duì)等形式的言語蹤跡(否則譯文是不被理解的、不可讀的、無效的)。后一種情況說明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異質(zhì)語言可以喚醒我們的言語,或者說可以促使我們?cè)谖覀冏约旱难哉Z中發(fā)現(xiàn)那些與異質(zhì)語言有著某種對(duì)等形式的言語蹤跡。
新文學(xué)史上兩次較大的文學(xué)思潮(一為胡適們的白話文學(xué),一為八十年代的新詩潮、后新詩潮)均標(biāo)示著語言返回言語的“言語化”努力。其實(shí)任何時(shí)代,語言對(duì)言語的向往從未中斷。佛經(jīng)譯文的“不加文飾”、曹氏父子的仿作樂府歌辭、唐中期的“新樂府”、宋詞和金元戲曲對(duì)市井俚語的植用,皆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學(xué)史上的這兩次思潮都發(fā)生在西風(fēng)東漸之際,這其中是否蘊(yùn)含著我們總是遮遮掩掩,羞于承認(rèn)的某種“西化”呢?或者能否直指其實(shí)質(zhì)日:異質(zhì)語言喚醒了我們?以西化為恥的詩人“狄俄尼索斯自欺的強(qiáng)烈程度遠(yuǎn)遠(yuǎn)超出他們身上也體現(xiàn)出來的我們普遍具有的普羅米修斯式內(nèi)疚。”亦即“受恩未報(bào)的負(fù)債感”。。對(duì)佛經(jīng)的吸收是漢語言的第一次“移植”,但“拿來”久了,便也心安理得地視為自己的東西,不再有任何的“內(nèi)疚”和不適;這意味著即使將其視為“那些與異質(zhì)語言有著某種對(duì)等形式的言語蹤跡”也要經(jīng)過一定時(shí)間的“遠(yuǎn)觀”方能被承認(rèn),可見人類的自尊是何等的強(qiáng)烈。
文學(xué)的言語化是沒有終點(diǎn)的旅行,當(dāng)言語中的語匯、敘述和表意方式、語感形式等轉(zhuǎn)化為一種文學(xué)規(guī)約并為普遍采用時(shí),新一輪的言語化便即將開始。當(dāng)然,我們也應(yīng)該看到,就具體作品而言,并非它的言語化程度越高,它的生命力和文學(xué)意義就越大。大白話、白開水式的作品就是反證。在文學(xué)的相對(duì)平靜期,對(duì)文學(xué)語言的規(guī)約只能做局部的修正,除非文學(xué)及其語境迎來一個(gè)翻天覆地的時(shí)代或一個(gè)、一群強(qiáng)力詩人的到來來打破這種平靜。除此之外的大多數(shù)時(shí)候,文學(xué)在言語化的同時(shí)不得不恪守言語化和語言化(對(duì)文學(xué)規(guī)約的遵循)的一個(gè)比值,作品的意義正在于這個(gè)比值的恰當(dāng)。而這個(gè)比值隨著時(shí)代的不同而不同,不存在+恒定的“黃金分割”似的精美的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