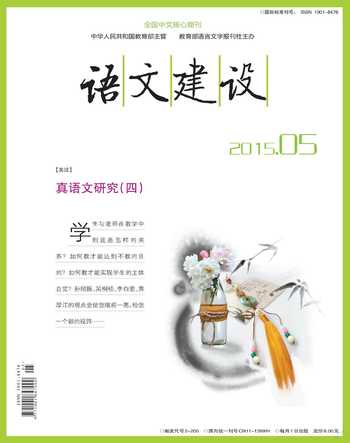葉圣陶編輯國文教材的實踐及啟示
陳振
“時文”,指時下之文,就是當下作者在當前語境中發(fā)表不久的各體文章。作為現(xiàn)代教育制度與學科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現(xiàn)代語文,自上世紀初獨立成科以來,一直是與當下文化互動關系最為密切的學科之一,且根據(jù)學科特點一貫保留著以各類課文為中心開展知識技能訓練和思想文化教育的傳統(tǒng)。選文之經(jīng)典性與時代性的對立,一直是語文教育論爭的焦點,其遴選標準百年來眾說紛紜。進入新世紀以來,在新課改實施及教材更迭過程中,語文教材老篇章的退出和新時文的入選成了社會爭議的熱點。時文,一方面富有時代氣息,貼近生活,是語文教材充滿生機和活力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隨時而動,變化不居,缺乏積淀和檢驗,是教材編制中最難把握的部分。葉圣陶在民國國文教材編輯實踐中注重趨新求變和貼近生活取材,但區(qū)別于人文性、思想性、政治性等內(nèi)容上的考量,他的時文選擇“全從形式上著眼”,追求語文訓練目的的實現(xiàn)。
一
葉圣陶早年先后擔任商務印書館、開明書店的文學編輯,主編或參與編輯《中學生》等十多種雜志。在1949年前共編輯15套語文教材,其中中學語文教材有:《新學制國語教科書》(共六冊,周予同、顧頡剛、葉紹鈞等合編,1923年起陸續(xù)出版),《開明國文講義》(共三冊,夏丏尊、葉圣陶、宋云彬、陳望道合編,1934年出版),《國文百八課》(計劃六冊,完成四冊,夏丏尊、葉圣陶合編,1936年出版),《國文教本》(共六冊,夏丏尊、葉圣陶合編,1937年出版),《中學精讀文選》(葉圣陶、胡翰先合編,1942年出版),《開明新編國文讀本(乙種)》(共三冊,葉圣陶、徐調(diào)孚、郭紹虞、覃必陶合編,1947年起陸續(xù)出版),《開明新編高級國文讀本》(共六冊,朱自清、呂叔湘、葉圣陶、李廣田合編,1948年起陸續(xù)出版),《開明文言讀本》(共三冊,朱自清、呂叔湘、葉圣陶合編,1948年起陸續(xù)出版)。
縱觀葉圣陶參與編寫的教材,在時文選編上有這樣的總體特點。一是時文選篇數(shù)量較多,體裁全備。以1923年起陸續(xù)出版的《新學制國語教科書》為例,民國成立后寫作或發(fā)表的時文篇目數(shù)量較大,占全部篇目的1/3左右,首次被選入本套教材并產(chǎn)生持續(xù)影響時文篇目有:蔡元培的《圖畫》《我的新生活觀》《文明與奢侈》《理信與迷信》《建筑》《雕刻》、胡適的《新生活》、徐志摩的《泰山日出》、魯迅《故鄉(xiāng)》《鴨的喜劇》、冰心的《笑》、任鴻雋的《說合理的意思》、林紓的《記翠微山》等等。葉圣陶所編其他教材,也同樣注重時文的選編。即使是專選文言文的1948年版《開明文言讀本》,也選取俞平伯的《山陰五日記游》、魯迅的《癡華鬘題記》,以及梁啟超、蔡元培、胡適等時人的多篇作品。這些選文體裁繁多,除常見文體外,更側重應用文文體。二是時文選編意旨明確:貼近生活。《開明新編高級國文讀本》開篇的“編輯例言”明確昭示:“我們選編這本書,第一,希望切合讀者的生活與程度。就積極方面說,要選足以表現(xiàn)時代精神的,與當時生活有關聯(lián)的、為當時青年所能了解和接受的。”三是時文選取原則從形式出發(fā),不側重以內(nèi)容取材。這在《開明國文講義》《國文百八課》中得到徹底貫徹。編者在《關于〈國文百八課〉》一文中開篇這樣介紹:“這是一部側重文章形式的書,書中所選取的文章,雖也顧到內(nèi)容的純正和性質的變化,但對于文章的處置,全從形式上著眼。”[1]
以上特點在《國文百八課》中得到更為集中的體現(xiàn)。下面我們以這套教材為例,具體考察葉圣陶作為編者的教材編纂理念和時文選編策略,并結合葉圣陶的語文觀念及教育思想,探究其時文選編理念及策略形成的原因。
二
《國文百八課》由葉圣陶與夏丏尊合編,是一部頗能代表編者語文教育思想且極具特色的初中語文教材,開明書店從1935年到1938年先后印出四冊。教材的文選部分“選文力求各體勻稱,不偏于某一種類,某一作家。內(nèi)容方面亦務取旨趣純正益于青年的身心修養(yǎng)的。唯運用上注重于形式,對于文章體制、文句格式、寫作技術、鑒賞方法等,討究不厭詳細”。四冊72課共有選文144篇,其中,五四新文化運動后產(chǎn)生的時文選篇有94篇,占全部選篇的2/3左右,遠遠高于同一時期多數(shù)教材的時文選編比例。
在時文選編來源的處理上,編者既選擇當時教材通用的代表性時文篇章,又大膽啟用新時文。四冊教材選用的時文中,有15篇文章屬于當時民國中學國文教材最常見的篇章,如:豐子愷的《養(yǎng)蠶》,魯迅的《秋夜》《鴨的喜劇》《風箏》,徐蔚南的《初夏的庭院》,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橋》,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梁啟超的《祭蔡松坡文》《歐游心影錄楔子》,高一涵的《立志》,蔡元培的《我的新生活觀》,劉半農(nóng)的《一個小農(nóng)家的暮》,王光祈的《工作與人生》,許地山的《落花生》。這些文章被多數(shù)教材反復選用,在各版本教材復見次數(shù)達6次以上。筆者統(tǒng)計整個民國時期60余種主流中學國文教材,復見次數(shù)在6次以上的時文選篇總數(shù)為82篇,《國文百八課》中竟占了15篇,大致反映出當時時文選篇的基本面貌。這也符合該教材“編輯大意”所言的“本書所收選文都是極常見的傳誦之作”。
同時,該教材選用的94篇時文中也有33篇是其他教材所從來沒有選過的,它們是:子夜的《黃浦灘》,茅盾的《鄰》,胡適的《我與小說》,田山花袋(作)、夏丏尊(譯)的《新教師的第一堂課》,周作人的《苦雨齋之一周》,佚名的《水手》,佚名的《導氣管的制法》,佚名的《公文標點舉例及行文款式》,常惠、王憲章的《中國大學發(fā)現(xiàn)唐墓調(diào)查報告》,顧壽白的《菌苗和血清》,賈祖璋的《動物的運動》,孟真的《農(nóng)民的衣食住》,趙元任的《科學名詞跟科學觀念》,竺可楨的《二十三年夏季長江下游干旱之原因》,莊嚴、黃鵬霄、金希賢的《點查柏林寺所藏經(jīng)板數(shù)目報告》,佚名的《廢除不平等條約宣言》,佚名的《書虛》,曹聚仁的《“回農(nóng)村去”》,陳布雷的《黃花崗烈士紀念會演說詞》,樊的《釋“三七”》,李良騏的《霜之成因》,林語堂的《廣田示兒記》,劉大白的《整片的寂寥》,茅盾的《再談“回農(nóng)村去”》,孫文的《歡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詞》,田漢的《蘇州夜話》,易卜生(作)、潘家洵(譯)的《娜拉臨走的一幕》,佚名的《希伯來開辟神話》(一、二),佚名的《中學法》,彭玉麟的《與郭意城書》,周作人的《致俞平伯書》,朱自清的《盧參》。
這些獨有的時文選篇,體裁繁多,除常見文體外,更側重應用文文體,包括日記、演講、書信、雜感、隨筆、傳記、游記、宣言、調(diào)查報告、科技小品、法規(guī)條文等。這也是編者在教材《編輯大意》中表明的特色追求:“應用文為中學國文教學上的一個重要綱目,坊間現(xiàn)行國文課本大都不曾列入。本書從第一冊起即分別編入此項材料,和普通文同樣處置。”“古今論文之作及關于文藝上主義、派別的論著向占國文教材的一部分,本書雖也采取純文藝作品,但論文之作及文藝理論概不收錄。一則因每課已有自具系統(tǒng)的特編的文話,不必再依賴此種零星材料;二則編者在經(jīng)驗上深信片段的論文之作及文藝理論對于初中程度的青年并非必要,甚且足以誘致一知半解的惡果。”可見其意見之獨到。
這些選文貼近生活,既有與中學生生活現(xiàn)實密切相關的話題,如《怎樣讀書》《讀書與求學》《工作與人生》《中學法》,也出現(xiàn)一般教材更為少見的,大量的日常生活類說明文,如《農(nóng)民的衣食住》《蟑螂》《動物的運動》《霜之成因》《二十三年夏季長江下游干旱之原因》《菌苗和血清》《蘇打水》《導氣管的制法》《機械人》等。
三
大量時文的選入,反映出編者對語文教學材料選取趨新求變的意識。這也是編者一貫的態(tài)度。早在五四前后,作為新文化運動積極參與者和國語運動的重要推動者,葉圣陶根據(jù)語文教學和編寫教材的實踐經(jīng)驗,即提出革新語文教育和改革教材的主張。他提出語文教材編寫要“順自然之趨勢,而適應學生之地位”,并積極提倡白話文進教材,力主教材選文“力避艱古而近口說”。[2]1935年他告誡說:“切近不切近現(xiàn)代青年的現(xiàn)實生活,才是國文教學成功跟失敗的分界標。”[3]他后來不斷強調(diào)教材應該“切合學生的生活與程度”,就內(nèi)容題材來說,應該是“足以表現(xiàn)時代精神的,與現(xiàn)代生活有關的,為現(xiàn)代青年所能了解接受的”[4]。他嚴厲批評“古典主義”:“舊式教育死守古典主義,讀古人的書籍意在把書中內(nèi)容裝進頭腦里去,不問對于現(xiàn)實生活適合不適合,有用處沒用處。”[5]他認為時代在前進,生活在發(fā)展,教學的內(nèi)容與重點也應不斷變化。他對語文教育之于“固有文化”有著清醒的認識:在國民黨推動“黨化教育”過程中,1932年的《初級中學國文課程標準》把教育目標做了調(diào)整,增加了第一條,即“使學生從本國語言文字上,了解固有的文化,以培養(yǎng)其民族精神”。葉圣陶當時敏銳地指出了這一變化背后的深意:“這新頒布的課程標準顯然帶有一種新的傾向。這新的傾向給我們的認識就是‘復古。”[6]1945年在《〈國文教學〉序》中,他指出語文教學的任務是“傳播固有的和現(xiàn)代的文化”,而當時一般的慣例表述是“傳播固有的文化”,他加上了“現(xiàn)代的文化”。
在語文教材選編“趨新”意識之外,葉圣陶更顯著地表現(xiàn)為“求廣”的追求。1947年他說:“就最廣泛的方面說,凡是我國文字寫成的東西都是國文科的材料”,遠至“刻在龜甲牛骨上的殷墟文字”,近至“現(xiàn)代的新文藝作品”,均是語文學習材料。[7]用現(xiàn)在的話說,這就是大語文觀。l922年,葉圣陶針對當時國文教授“限于教室以內(nèi)”“限于書本以內(nèi)”的弊端,明確指出:“趣味的生活里,才可找到一切的泉源。”他還指出:“學習得跟整個生活打成一片。”[8]對于教材選文原則,他能明確提出:“希望切合讀者的生活與程度。就積極方面說,要選足以表現(xiàn)時代精神的,與當時生活有關聯(lián)的、為當時青年所能了解和接受的。”“要是學生頭腦里有這么一種印象,課本是一回事,實際又是一回事,彼此連不到一塊兒,那就是教學上的大失敗。”[9]正是這樣的語文觀念帶來《國文百八課》選文的題材廣泛和貼近現(xiàn)實生活的鮮明特色。
用大語文觀來解釋人們熟知的葉氏“例子說”,可能更接近其本意,也就解開了其時文選編所表現(xiàn)的獨特眼光和大膽做法之背后因緣。葉圣陶提出過語文教本無非是“例子”。我們來看看他在《談語文教本》一文中的原話:
語文教本只是些例子,從青年現(xiàn)在或將來需要讀的同類書中舉出來的例子;其意是說你如果能夠了解語文教本里的這些篇章,也就大概能閱讀同類的書,不至于摸不著頭腦……所以語文教本不是個終點。從語文教本入手,目的卻在閱讀種種的書。[10]
因此,課文無非是“例子”,乃至后來出現(xiàn)的“憑借”說,并不是將課文限制在某一種特定的用途,也無意貶低或削弱課文的地位和作用,更不是將課文抬舉到經(jīng)典和樣板的高度,而是強調(diào)語文教本不是終點,要由此閱讀和學習更廣范圍的材料。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和出發(fā)點,《國文百八課》才會出現(xiàn)33篇獨有的題材廣泛、文體兼?zhèn)涞母黝愡x文。
選文是“例子”,那么是做什么的例子?編者標榜:“書中所選取的文章,雖也顧到內(nèi)容的純正和性質的變化,但對于文章的處置,全從形式上著眼。”我們來看教材的具體做法,例如第一冊第十二課,為了配合文話“敘述的順序”,文選選了一篇寫人的《武訓傳略》和一篇記事的《五四事件》,兩篇文章內(nèi)容上不搭界,編者指出他們的共同點在于都是按時間順序敘述的。教材導引對武訓的人物精神和五四事件的時代意義不著一墨,習問(即練習)題直接指向文話所講述的“敘述的順序”這一語文知識點。教材設計這樣提問:
1.文選二十二(《武訓傳略》)、二十三(《五四事件》)里面,有時間不相連續(xù)的部分嗎?作者對于這種部分,用著怎樣的敘述方法?
2.文選二十二、二十三里面,有不是敘述性質的文句嗎?如有,試舉出來。
這也是《國文百八課》最大的特色:與同期的教材偏重關注選文內(nèi)容的思想教育功能相比,它的選文“全從形式上著眼”。選文的編排是以語文知識的傳授為序,選擇什么樣的文章,以能否作為文話和文法的范文和例文為準繩,圍繞選文的“習問”設計聚焦文法和寫作知識的訓練和鞏固。葉圣陶曾明確表示:“時下頗有好幾種國文課本是以內(nèi)容分類的。把內(nèi)容相類似的古今現(xiàn)成文章幾篇合成一組,題材關于家庭的合在一處,題材關于愛國的合在一處。這種辦法,一方面侵犯了公民科的范圍,一方面失去了國文科的立場,我們未敢贊同。”[11]這樣的選編理念和處理策略反映出編寫者鮮明的教學取向:淡化語文教學思想內(nèi)容教育的目的,強化語文科特有的目的,即形式的。關于文章的內(nèi)容與形式,《國文百八課》第一課文話《文章面面觀》有這樣的表述:
每讀一篇文章該做內(nèi)容的與形式的兩種探究。文章的內(nèi)容包括世間一切,它的來源是實際的生活經(jīng)驗,不但在文章上。至于文章的形式純是語言、文字的普通法式,除日常的言語以外,最便利的探究材料就是所讀的文章。
中學里國文科的目的,說起來很多,可是最重要的目的只有兩個,就是閱讀的學習和寫作的學習。這兩種學習,彼此的關系很密切,都非從形式的探究著手不可。
內(nèi)容和形式傾向的不同,反映出語文觀念中語文教育的性質和目的等方向性問題,這就是民國頗有影響的內(nèi)容與形式之爭。葉圣陶的觀點明確傾向形式。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現(xiàn)代語文的弊端:“五四以來的國文科的教學,特別在中學里,專重精神或思想一面,忽視了技術的訓練,使一般的學生了解文字和運用文字的能力沒有得到適量的發(fā)展,未免失掉了平衡。”[12]1932年,葉圣陶發(fā)表《國文科之目的》一文,將國文科的目的概括為“整個的對于本國文字的閱讀與寫作的教養(yǎng)”,換一句話說,就是“養(yǎng)成閱讀能力”“養(yǎng)成寫作能力”兩項。此后,他在1940年發(fā)表的《國文教學的兩個基本觀念》、1942年發(fā)表的《略談學習國文》、1948年發(fā)表的《國文》等文章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直到1980年,葉圣陶還堅持這樣的觀點:“學校里為什么要設語文課?這個問題好像挺簡單,但是各人的認識并不一致,甚至有很大的不同。有一種看法認為語文課的目的是讓學生掌握語言文字這種工具,培養(yǎng)他們的接受能力和發(fā)表能力。我同意這種看法。”[13]后來有人將葉圣陶的觀點總結為語文教育思想的“工具本質論”[14]。
一般認為,強調(diào)語文教育的人文性,或注重內(nèi)容的社會認知和思想品質教化作用,會造成時文選編。前者如當前新課標教材的編寫,后者如新中國成立初期和“文革”期間教材中的政治時文。葉圣陶的語文觀念及其在《國文百八課》的實踐證明,語文學科特有目的的強調(diào),形式的需求也同樣催生時文選編。葉圣陶的時文選編經(jīng)驗告訴我們,語文教材選文應重視形式上的價值,取材范圍要廣泛,時文應因其貼近生活、切近時代、貼近學生,具備應用性和實踐性而納入語文教育的視野。
參考文獻
[1]夏丏尊,葉圣陶.閱讀與寫作[M].上海:開明書店,1938:119.
[2]葉圣陶.葉圣陶論語文教育[M].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19.
[3][7][12]葉圣陶.葉圣陶教育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44,156,113.
[4]葉圣陶.葉圣陶集:第十六卷[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1:102.
[5][10]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葉圣陶語文教育論集[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0:87,182.
[6]葉圣陶.葉圣陶集:第十二卷[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1:34.
[8]商金林.葉圣陶傳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142.
[9]商金林.葉圣陶年譜[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1986:186.
[11]葉圣陶.葉圣陶教育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403.
[13]徐林祥,楊九俊.關于語文課程目標百年嬗變的反思[J].課程教材教法,2012(2).
[14]董菊初.葉圣陶語文教育思想概論[M].北京:開明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