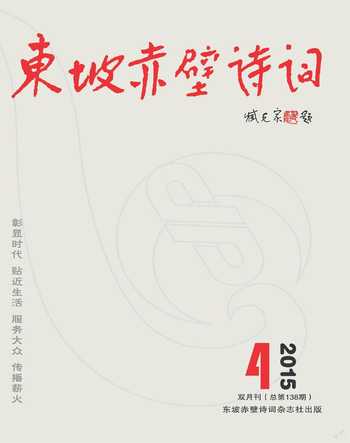山水詩寫法小議
詩人游山玩水,題詩作賦,已成習慣。直到今天,旅游詩仍是我們詩詞愛好者寫作的重要題材。但是我常見到當代的許多旅游詩詞,缺乏個人獨特的感受,抒情極為平庸,經常出現相近乃至雷同的情感。有的單純寫景,成為景點說明書,未能寫出山水景點的特色和精魂。
這里舉幾例當代詩人的作品,試圖對旅游詩詞的創作做一些探討,以供當代詩詞創作者參考。
黃河壺口瀑布,自然是寫詩的好題材。筆者見過很多寫這一題材的詩詞作品。這里介紹四首。
先看星漢的《重游壺口瀑布,旋即歸鄉,先以手機柬從弟》:
臨淵一笑洗牢騷,腳踏宜川第二遭。
春色遠來無鄙吝,誰人到此不粗豪。
源頭青海流泉古,壺口黃河卷浪高。
代我傳言諸父老,心潮東去付狂濤。
詩從空間實處落筆,敘述來此已經是第二次了。頷聯寫感受,黃河與游客,以兩者均無鄙吝之心和都有粗豪之情相映襯,抒發作者的情懷和表明詩人的性格。頸聯追述源頭,并且描述眼前景色,全詩到此差不多已經寫完,忽然尾聯宕開一筆,詩人委托黃河東去給父老鄉親帶個信。此系補敘題中之意,因為作者是山東人氏,黃河入海口即在山東,所以聯想到家鄉,牽動無限思鄉之情。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說:“詩雖奇偉,而不能揉磨入細,未免粗才。詩雖幽俊,而不能展拓開張,終窘邊幅。”袁枚還指出,詩不可“能大而不能小,能放而不能斂,能剛而不能柔。”寫黃河這個大題材,需要大小兼顧,剛柔并濟,能放能收,讀來才覺得有味。此詩以思鄉之情作結,柔中帶剛,剛中有柔。
再看一首陳仁德的《觀黃河壺口瀑布》:
蒼崖斷處怒濤飛,濁影騰空霧氣微。
天造奇觀疑是幻,身臨險境競忘歸。
一番風雨成秋色,萬古雷霆共夕暉。
滾滾驚湍奔眼底,亂濺黃潰上征衣。
詩從大處落筆,前四句一氣呵成,寫黃河壺口景象很有氣勢。頸聯開始收綰,點出時令和時間。“夕暉”,呼應上聯中的“忘歸”。最后突然以“驚湍”收束到“征衣”。從景物到人物,戛然而止,留有余味。古人云:“詩乃模寫情景之具,情融乎內而深且長,景耀乎外而遠且大。”全首詩因為歸結到“征衣”,讀者自然想到作者經歷之多,“奇觀”、“險境”、“風雨”、“雷霆”,原來都不是為寫景而寫景,詩中還是有“我”在也。
然后看一首鄧世廣的《黃河壺口瀑布紀游》:
未計人間長短程,南柯醒處大橋橫。
壺濤仍作雷霆怒,腦海早除宵小名。
兩岸新詩余曙色,一川故事送秋聲。
征塵留待天山洗,跳進黃河洗不清。
全詩始終有作者在。“未計”、“南柯”、“除名”、“留洗”的主人都是作者。詩人邊觀景、邊思考。頸聯另辟蹊徑,似乎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將驚心動魄黃河之景寫得如“閑庭信步”、“今日得寬馀”。所謂一緊一松,一張一弛,節奏感很強。更有趣的是詩人還不愿用黃河水洗“征塵”,決定要回到自己的家鄉“天山”再洗。朱庭珍在《筱園詩話》中說:“律詩中二聯,不宜一味寫景。有景無情,固非好手所為;景多于情,亦非佳處。蓋詩要文質協中,情景交化,始可深造入微。”寫黃河壺口瀑布,情景兼顧,這又是一種寫法。
最后看看筆者的《黃河壺口瀑布》:
卷沙裂石鬼神驚,發出黃河怒吼聲。
天上不應如此濁!人間更得幾時清?
從崖跌落仍昂首,向海奔流又啟程。
我敞風衣壺口立,好教襟袖蓄豪情。
首聯寫景,套用“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頷聯用李白“黃河之水天上來”的意思,詩人由此聯想,然后發問:既然是天上來,為何水這樣濁呢?天上不應該這樣渾濁啊!如果天上這樣濁,人間還能清的了嗎?古人云:“夫情景相觸而成詩,此作家之常也。或有時不拘形勝,面西言東,但假山川以發豪興爾。”所謂“寫景述事,宜實而不泥乎實。”詩有言外意,更好。頸聯用了擬人的寫法,這手法新詩常用。最后收結到作者自己,希望從黃河中借得豪情。作者另有詞句云:“赤子心泉何所似?一座黃河水庫!”此時此處,正在“蓄水”哩!一首詩,需要像折扇一般打開,最后又像折扇一般收攏。
雁門關,也是古來詩人吟詠的對象。元楊載說:“登臨之詩,不過感今懷古,寫景嘆時,思國懷鄉,瀟灑游適,或譏刺歸美,有一定之法律也。中間宜寫四面所見山川之景,庶幾移不動。第一聯指所題之處,宜敘說起。第二聯合用景物實說。第三聯合說人事,或感嘆古今,或議論,卻不可用硬事。或前聯先說事感嘆,則此聯寫景亦可,但不可兩聯相同。第四聯就題生意發感嘆,繳前二句,或說何時再來。”這自然是詩人的經驗之談,但是如果人人都如此寫,山水旅游詩詞就成了批量生產的商品了。這里也例舉四首。
首先看星漢的《癸巳秋登雁門關》:
路轉秋風黃葉村,旌旗影里舊烽墩。
將軍苦戰威猶壯,騷客豪吟句尚溫。
一道長城牽日月,幾聲征雁動乾坤。
揮毫更向天山指,我抱清雄過玉門。
全詩寫詩人一路行來,所見所聞,貫穿始終。首聯實寫,頷聯虛寫,頸聯氣象忽然轉到宏大,尾聯寫作者似乎手中之筆放不下,腳下步伐也停不住。還要一路行去,一路寫去。此首“氣足”。
其次看熊東遨的《登雁門關》:
雁字橫空去漸遙,孤城向晚火云燒。
年光上溯窺胡馬,岳勢西來起怒潮。
九曲河聲閑里聽,百重兵氣酒邊銷。
秋風喚醒關前菊,好共詩人話寂寥。
以“雁字”“火云”襯托“孤城”,顯得雄關一上場就氣概不凡。頷聯寫歷史,寫地形。頸聯著“閑里”“酒邊”,暗示作者將要登場了。果然,尾聯以“風”和“菊”簇擁“詩人”亮相。詩人游覽雄關的感受是“寂寥”。此首“氣閑”。
再來看胡迎建的《雁門關懷古》:
縱眺天連漠北寒,秋高不見雁翔盤。
城蟠嶺脊龍蛇勢,樓扼咽喉鎖鑰關。
底事匈奴驅不盡?當年戍卒夢難安。
笳聲殺氣如縈抱,鐵血猶存紫塞斑。
上一首有“雁”,這一首無“雁”。無論加法還是減法,均在于詩人如何運乎一心。頷聯寫雄關形勢。頸聯寫歷史。尾聯似乎收不住,還是將古來征戰寫得有聲有色。此首“氣壯”。
最后看楊逸明的《登雁門關》:
雁門雄險一登攀,千古兵家爭此關。
日色肩頭添上重,秋風心際透來寒。
群巒入夢追唐宋,萬木揮毫點翠丹。
只愿從今華夏土,無須垛堞保平安。
首聯寫登攀,也是實寫。頷聯寫心頭感覺:肩頭覺得日光之重,心際覺得秋風之寒,將雄關的氣氛渲染的細致入微。頸聯寫景,亦景中有情。尾聯發議論,表達對于祖國和平的良好祝愿。此首“氣穩”。
通過以上兩組同一題材各四首詩的分析,可見要寫好旅游詩,需要抓住景點特色,提高語言概括能力。旅游詩既要有詩味,又要有畫意。要使景點的內涵更加豐腴,更加富有感情色彩和思想色彩。更多地去觸發讀者的藝術聯想,增添讀者的審美情緒。葉燮《原詩》:“游覽詩切不可作應酬山水語。如一幅圖畫,名手各各自有筆法,不可錯雜。又名山五岳亦各各自有性情,不可移換。”不能象復印機一樣把風景機械地復印到詩中。應該見材取意,借題發揮,尺水興波,寄興托意。寫景抒情說理相間,層次波瀾起伏。王國維:“一切景語皆情語也。”人與景在長期相處中形成一種和諧的共振。山光水色,人文景觀,要把他寫得“一丘一壑也風流。”(辛棄疾語)應該特別注重旅游詩的章法,不要總是停留在一個層面上描寫。同時,詩人應該表現自己個性,抒情必須有自己的個性,思想情感必須健康、飽滿、曠達,不要總是抒發一些人人都有,而且人人都能說的想法。不能無病呻吟,也不能抒發一些變態的心理。有的旅游詩除寫了“某某某到此一游”之外,什么實質性的內容和自己的意思也沒有,這樣的旅游詩詞真還不如不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