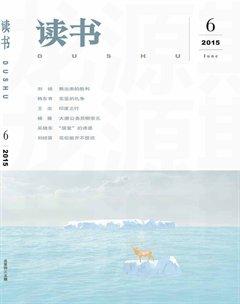從醉漢祥瑞到書店祥瑞
炎仌
搜索欄里輸入“祥瑞”二字,彈出的卻是“祥瑞御免”,讓人有點不知所措。
瑞者,以玉為信也。“祥瑞”本是上天賜予人類美好的一種信約。“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天意既然顯現了麒麟、鳳凰、卿云、嘉禾等等神奇而具體的意象,那就肯定會在現實生活(特別是政治生活)中兌現種種好事,感召若符節。
也許是人心不古導致祥瑞不出吧,中古以后,人變得理性起來,史書上關于祥瑞的記載逐漸減少。另一種趨勢,則是把“祥瑞”從天降的異象,轉義為人間美好事物的開端,類似于今俗所說的“好兆頭”。比如《資治通鑒》記載唐德宗貞元初年的時候連年饑饉,軍民都是瘦黑的樣子,后來終于麥子熟了,街市上出現“醉人”,說明糧食多到甚至可以釀酒,大家都來圍觀,覺得很祥瑞。
由此往下數一千一百多年,一九○三年,似乎不是一個“祥瑞”的年份。這年晚清名臣張之洞進京覲見,逛了一通琉璃廠書店,寫了首詩,提到“醉漢祥瑞”的典故:
畢董殘裝有吉金,陳思書肆亦森森。
曾聞醉漢稱祥瑞,何況千秋翰墨林。
張之洞的官做得怎么樣且不說,他的詩在近代的確自成一家,用典特別貼切。這里的“畢董”(其實應該叫“畢少董”)、“陳思”分別為宋朝南渡以后臨安的收藏家和書店老板。唐朝貞元年間的長安、靖康之亂以后的臨安,以及一九○三年八國聯軍撤走不久的北京,同處經歷大動蕩而剛剛平靜下來的時代。這三個時代的士大夫,都有一種“中興”的期許。張之洞的意思是說,唐朝貞元時候,市面有醉漢就可稱為“祥瑞”,那么,跟隨宋高宗南渡的古董家,臨安書肆的森森書架,甚至當下北京琉璃廠的舊書店,就更應該成為中興的“祥瑞”了。祥瑞不僅從天上降到人間,更從口腹之欲的期待,上升為精神需求的滿足:書業的繁盛也可以成為祥瑞。
然而天不如人愿,琉璃廠見證了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的動蕩,最終連這“祥瑞”自身都難保了。一九五一年,遠在廣州的陳寅恪聽說北京琉璃廠的舊書店開始銷售新書,感慨不已,遂和張之洞的詩道:
迂叟當年感慨深,貞元醉漢托微吟。
而今舉國皆沉醉,何處千秋翰墨林。
從張之洞原詩的“何況”,到陳寅恪和詩的“何處”,一字之差,晚清士大夫的一線希望,變成文化遺民的徹底絕望。“醉漢祥瑞”(文化象征)隨時代淪陷的沉痛感,恐怕是今天在網上到處打“祥瑞御免”、“也是醉了”的我輩所難以理解和深入的。不過有些微末的事情在身邊發生,見微知著,也多少呼吸到一點時趨的變化。比如筆者剛進大學的時候,北大周邊的書店還算比較可觀。有名的“萬圣”之外,“國林風”和“風入松”都在鼎盛期,某圖書城雖然不太上檔次,也不如今日這般蕭條。西門外萬泉河畔有一排書鋪,燕東園后面的斜街上則有一處“布衣”;園子里一些地下室或倉庫也被暫借為舊書店,記得一家叫“暢暢”的真是不錯,從那里買過不少工具書和早年的“三哈”叢書;“漢學”和“博雅堂”也是那時候起來的。就算最不濟,那良莠不齊、充斥盜版的“周末文化市場”,有心人竟也能從中淘出些五六十年代舊版本。
后來呢,海淀橋旁邊冒出兩個龐然大物,一陣惡斗,然后便是拼命打折。隨著網上購書、拍書的流行,舊書店一聯網,再也撿不到漏了。一面是實體書店房租上漲,朝不保夕;另一面卻是我們這些惡劣讀者,逛書店如同觀書展,忙著用手機拍照,好回去網購。再后來,好像紙質書都很奢侈。大家意識到校園空間的狹小,北京空間的昂貴,以及搬家的勞累,于是把想看的書成T成T地裝進硬盤。與此同時的另一個變化,則是看書人變成了查書人,快速鎖定目標,不及其余。以往那種從平日積累流出的學問越來越稀有,數據庫資料堆積而成的論文則俯拾皆是。人文知識的生產、傳播、再生產方式正在發生重大變革,我輩躬逢其盛,真不知是悲還是喜。
聽說,北大當年的老領導喜歡一個說法,叫“出現了非常祥瑞的氣氛”。領導心目中的“祥瑞”究竟是什么,真不好揣摩。我只覺得,除了大樓、大項目、大數據、大改革之外,校園內外的書店,以及師生逛書店的習慣,類似這種或許微不足道,卻往往能起到潛移默化作用的知識氛圍,似乎更應在“祥瑞”的名單之內。畢竟千年以來,“翰墨林”承載了太多文明中興的希望。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京東黃渠村信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