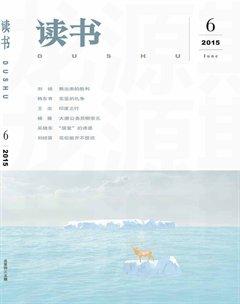危機時刻如何管理國家
方旭
危機時刻如何管理國家?幾乎所有現代民主國家都會面臨這個重大政治問題。
羅斯托(Clinton Rossiter)的《憲法專政:現代民主國家中的危機政府》一書印于一九四八年,又在二○一一年被美國法學界挖掘而“應景”出版,試圖為全球性危機時代的到來尋求解決方案。美國憲法學家奎克(William J.Quirk)介紹道,這是一本對“危機時期的民主國家的經典研究”,通過對德國、法國、英國、美國歷史上的危機時期進行考察,揭示了一個無可逃避的真理:“國家處于生死存亡之際,除了專政之外,其他政體都不能幸存。”作者獨創性地提出—“專政也可以是合憲的”,從而實現“憲法專政”。
何謂“憲法專政”?換句話說,專政是如何植入憲法的?
事實上,“憲法專政”一詞最早為耶魯大學沃特金斯(Frederick M. Watkins)提出。他認為“憲法”與“專政”的結合在理論上看似悖論,但從政治實踐來看,憲法專政與立憲政府共生滅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憲法保障共和國的秩序,專政捍衛共和國的存亡。
我們需要記住,羅斯托寫作該書時,美國才從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陰影走出來,“專政”的話題在“法律必須信仰”的語境中顯得頗為敏感。即便是在“專政”前加上“憲政”這樣時髦的形容詞,“憲法專政”仍是一個刺激神經的詞語—沒有哪一個“憲政”學者愿意承認憲法中“專政”的因素,甚至這樣的表述都顯得聳人聽聞。羅斯托也承認“憲法專政是一個拼湊的術語筐,所有不同類型的緊急政府和程序都可以往里面裝”。但這不只是文字組合游戲,“各種歷史事實已經證明,在維護憲政民主的過程中,憲法專政不斷地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或許現實并不如此,一九 一九至一九三三年魏瑪共和國對《魏瑪憲法》四十八條總統緊急權條款的濫用產生的慘劇無時無刻不刺激著憲政學者的神經—這個本是用來捍衛共和國的條款,最后卻成了毀滅共和國的重要因素,而敵人的摧毀竟全然合法!當然,有人也許會認為,如果沒有《魏瑪憲法》四十八條,魏瑪共和國或許早就已經崩潰了—這本身就是一個聚訟不休的問題。
憲政必定純粹自洽,還是說另外存在著憲法專政的可能性?羅斯托的《憲法專政》一書將這些問題帶入到幾個較大的民主國家的“危機時期”的話語情景中考察,試圖找到答案。 本書共分為六部分,除了討論幾大民主國家運用“憲法專政”解決危機事件的具體事例,他的考察重心仍然放在美國本土應對緊急狀態的問題上。在最后一部分,羅斯托“先知”般地指明了美國“憲法專政”的未來:“更新整個憲政結構,建立一個能夠果斷而高效地應對二十世紀世界各種疑難問題的全國政府。”
談及“憲法專政”的理論來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各個民主國家(城邦),不過當時的理論還未曾上升到制度的高度,如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就提到:“只是所有的規約總不能概括世事萬變,個人的權力或若干人聯合組成的權力,只應在法律有所不及的時候,方才應用它來發號施令,作為補助。”(1282b3-6,吳壽彭譯文)
在蒙森看來,古羅馬時期的“憲法專政”已經成為“共和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項專政的制度設立除了防止新近被推翻的王制復辟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形成各憲制機構的互相制約,尤其是制約執政官的權力。關于羅馬人的“憲法專政”制度,我們比較熟悉的是辛辛那提(Cincinnati)的傳說:一位年邁的農民,種地時受到國家的召喚,賦予他專制的權力以擊退外邦僭主的威脅,他獲得了十六天的絕對統治權,直到國家恢復秩序,他又放下手中的劍,拾起犁重新做回他的農民。馬基雅維里對羅馬人的傾慕毫不吝嗇:“如果他們中任何一個人獲得了專政,他們最大的榮耀在于又一次迅速放棄了這一尊榮。”(馬基雅維里:《論李維》第一卷,135頁)
據說,古羅馬時期的“專政官”能夠自覺放棄專政權力,依靠的是個人的政治德性。其實不然!那是由于一種對“專政官”制度性的約束。我們知道第一任“專政官”法拉庫斯(T. Larcius Flaccus)在其專政時期,城內治權和軍事治權的區分消失,一切權力集中于“專政官”,他有權指揮包括執政官在內的所有行政官員。雖然他享有無可比擬并且迅速采取行動的權力,但也受到制度的重重限制:一是任期六個月,不交出權力可以判處死刑;二是每次只能選舉一名專政官;三是任期不能長于其他執政官;四是護民官對其有監督的權力,可以要求其停止行動,可以在其任期結束后追究其責。
馬基雅維里在《論李維》中專門用一章節來討論“專政官”制度,對羅馬人的這個制度贊不絕口,他認為:“這是羅馬制度中應予以重視的制度,可算作這個大帝國豐功偉業的緣由。” (《論李維》第一卷,135頁)他清醒地認識到—共和國的常規制度動作遲緩,不能迅速救共和國于危機存亡,馬基雅維里這一肯定立場為博丹、盧梭等后世思想家所認可。他也指出了羅馬的“專政官”制度存在的兩難問題:全權的專政官可以處理所有危害共和國的問題,但專政的制度又必然因為制衡的不足有著走向個人獨裁的內在危險。羅斯托認為在共和國危機時刻所謂的制度根本無法約束專政的實施,現代的“憲法專政”更多依靠的是“專政者”的個人政治德性,“專政權掌握在一個好人手上是一回事,被一個壞人掌握又是另外一回事”(《憲法專政:現代民主國家中的危機政府》,65頁,下引此書只注頁碼)。
魏瑪時期的施米特對“專政”問題的思索對羅斯托的啟發不可低估。《魏瑪憲法》于一九一九年制定,兩年后施米特便“恰逢其時”出版了《論專政:從現代主權思想的肇始到無產階級斗爭》一書。該書區分了代表古典專政理論意義上的“委托專政”與代表現代人民制憲權的“主權專政”,并專門輔以一篇長文對《魏瑪憲法》四十八條進行解讀。可見,時在一九二○年左右—或者更早的時間,施米特就在思考“憲法專政”問題,并以《魏瑪憲法》第四十八條為例,以捍衛共和國的統一,復興古典的“委托專政”為己任,豐富現代專政理論。吊詭的是,在《論專政》出版一年之后,在其《政治的神學:主權學說四論》一書中,他又旗幟鮮明地支持“主權專政”,從而在一九二七年出版的《憲法學說》中將魏瑪共和國召開的制憲會議明確為“主權專政”。有人將施米特的法學稱為“情勢法學”,認為施米特是基于不同的政治背景來解釋他所謂的“專政”理論—恐怕是以為施米特犯了政治幼稚病。
羅斯托尊重他所處的時代與魏瑪時期“政治現實”的區分,他這本書論及德意志共和國中《魏瑪憲法》四十八條,并在開篇提到:“德意志共和國的生與死,很大程度上是使用和濫用《魏瑪憲法》第四十八條的歷史。”
一九三二年的普魯士訴魏瑪中央政府違憲一案被羅斯托視為“第四十八條最后的濫用”。值得一提的是,施米特當時擔任魏瑪共和國中央政府的法律顧問。早在一年前,他出版了一本富有爭議(或者可以說是臭名昭著)的著作《憲法的守護者》,其中寫道:“總統是憲法體制的軸心,凌駕在其他機構之上的、捍衛憲法并維護國體的、中立的、斡旋的、調控的、保護的權力,總統是由全國人民選舉產生的,因此他有權宣稱代表人民。他是超越黨派的、無黨派的、是一個中立的、調整議會制的實踐行動仲裁者;當議會解散時,他根據四十八條和一個總統內閣治理國家。”(施米特:《憲法的守護者》,190頁)我們由此似乎明白了施米特的思路:按照民主制原則行使人民制憲權,魏瑪共和國得以建立,人民的意志乃是“最高法”,這便是所謂的“主權專政”。隨后在共和國危機時期,自由民主政制無法應對國家面臨的危機,《魏瑪憲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在“公共秩序與安全受到嚴重的威脅”,總統代表人民行使專政權力,懸置“憲法規定七項基本權利”,以“委托專政”挽救共和國于危機,根本上靠的還是主權的決斷—在法理上這似乎并不矛盾,總統的意志就是共和國的意志,人民出場后歸隱于私人生活后,應該由總統代表人民意志出場,一切對總統權力的制衡都應該為共和國存亡這一最大底限讓步。施米特在最高法庭做的最后陳詞中說:“普魯士的確有其榮譽和尊嚴,可是在今天,這種榮譽的受托管理者和捍衛者乃是共和國。”(施米特:《在萊比錫憲法法院審理普魯士邦起訴民國政府案時的最后致辭》,184頁)
然而,即便是如此講究“具體政治處境”的施米特(也包括那些參與《魏瑪憲法》制定的法學家)未曾預料到“德國憲法德性和議會民主會墮落得如此徹底,以至于允許被可恥地、違憲地濫用”(65頁)。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臺執掌權力后,便利用專政條款掃清法理障礙,并將《魏瑪憲法》其他部分扔進了垃圾堆。
羅斯托顯然認為施米特高估了政治哲學的邏輯推理卻忽視了政治德性這一維度,《魏瑪憲法》的失敗在于專政條款并非訴諸“一位善良的、獻身于共和事業的民主人士”。羅斯托寄希望于政治德性上的“好人”使用憲法的專政條款—或許是林肯,抑或威爾遜、羅斯福。羅斯托提醒“永遠不要讓民主的敵人掌握民主的武器”,“政治正確”地將美國視為“憲法專政”制度成功的典范。
在論述“林肯專政”這節時作者可謂“煞費苦心”—作者進入文本之前大肆贊美美國憲法至高無上的地位以及其擁有的無可比擬的完整性。“美國憲法從未被中止過,一直保持著完整的效力和效果—不像《魏瑪憲法》—沒有明確規定自身的中止。”(9頁)他也提到一八六六年最高法院在米利根(ex parte Milligan)案中戴維斯大法官(Justice Davis)對緊急狀態下中止憲法的批判這段經典的論述,戴維斯大法官的振聾發聵的論述顯然是對公民基本權利的捍衛。
當我們進入文本時,卻發現羅斯托“筆鋒急轉”—通過分析內戰、“一戰”、大蕭條和“二戰”時期的總統行為,用一個個生動的事實證明,在維護憲政民主的過程中,“憲法專政”扮演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每一個生存下來的民主國家,都有一種機制—要么是明顯的,要么是隱含的—在遵守常態規則會危及國家存續之際中止憲法。”(9頁)
面對一八六一年美國南方七個州脫離聯邦對國家造成的危機,林肯無法用所謂的常態治理國家的方式來解決,也沒有任何緊急統治的先例供其參考,他只有訴諸戰爭的權力。在此期間,林肯完全沒有考慮古羅馬辛辛那提的“專政美德”,自我任命為“憲法專政者”,同年四月十五日頒布一項行政聲明,宣稱該七個州為叛亂,要求國會兩院在七月四日召開特別會議,征召民兵,鎮壓叛亂。除此之外,在招募軍隊、封鎖港口、濫用財政等方面將其專政權力發揮到了極致也屢屢突破憲法之限制:由于林肯對政府各部門充斥著缺乏忠誠之人的懷疑,以“政府之必須的、軍事措施直接引發的需求”為由,要求財政部長追加兩百萬美元財政部機動基金撥給三名“能力出眾、忠心耿耿和熱愛國家”的紐約市民,這公然違背了憲法“除了法律規定之外,不得從國庫提取款項”之規定。針對一八六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巴爾的摩的暴民阻撓費城到華盛頓的列車運送軍隊,林肯授權軍方“中止賓夕法尼亞、特拉華、馬里蘭和哥倫比亞特區的人身保護令權”。當首席大法官坦尼判決林肯沒有權力授權時,林肯不但無動于衷,還于一八六三年三月將此中止令擴大到所有的州—且不說此后他以“國家安全”為理由,授權郵局中斷涉嫌叛國的通信,并有權查看相關信件,可以通知軍政機關逮捕發現有叛亂活動跡象的人,諸如此類“違憲行為”不勝枚舉。
這便是— “林肯專政”。
我們可以看到,在捍衛憲政民主國家這一最大“正當性”理由的支撐下,“林肯專政”的“合法性”蕩然無存。“未經批準的逮捕,未經審訊的拘留,未經懲罰的釋放,時時制約著內戰期間的公民自由。”
眾所周知,林肯在就任總統一職時曾以“上帝之名”起誓,以保護憲法為己任,但在內戰期間,他確實中止了憲法。林肯在一八六三年七月四日召開的國會演說中,他公開地以“必要性”為理由,“正當化”他違憲的行為,他宣稱:“為了防止某一部法律遭到侵犯,難道要使其他法律都無法執行、政府本身也土崩瓦解嗎?如果我們明知違背某一法律可以保住政府,卻聽任政府被人推翻,這難道不是違反了誓言嗎?”他顯然清楚地認識到“聯邦比憲法重要得多,沒有聯邦,憲章也就毫無意義”。
威爾遜面臨的國家困境與林肯截然不同—前者面臨的是內戰危機,而后者則在“一戰”期間“必須征召、裝備一支能夠在海外作戰的龐大部隊”,盡管不存在國家內部的暴力威脅,但這仍然不能阻止總統專政權力得到不斷的擴張。威爾遜通過頒布一系列例外法案授予實現總統對于國家行政的完全控制,曾有一位權威美國作家在一本雜志中將威爾遜描述為“集國王、控制立法機構的首相、武裝力量的總司令、活躍的政黨領袖、經濟領域的專政者、外交部長和行政機構的大總管諸多角色為一體的人”。
西奧多·羅斯福則將應對軍事危機的專政權用于對付經濟危機,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六日的《國家復興法》則以“軍事戒嚴”的方式幫助美國度過經濟蕭條的危機,從而實現總統對經濟調節的無限權力。戰爭期間,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基于“防止間諜和陰謀破壞的理由”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九日將居于美國西海岸的七萬日裔美國人驅逐進集中營統一管理,這被視為對總統專政權力的最大濫用。
羅斯托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正好是“二戰”結束之后,此后的六十多年,美國經歷了不下十五次危機時刻。在他完成本書寫作后,美國“至少參與了十二次海外冒險行動,分布的范圍從朝鮮和越南直到海灣戰爭和科索沃”。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世貿中心崩塌,五角大樓濃煙滾滾。三天后,小布什總統通過行政令宣布美國因為遭受恐怖襲擊而進入全國緊急狀態—這是一場永久的戰爭,可以說,“九一一”事件標志著總統專政權走向頂峰。這是否表明,美國正走向羅斯托筆下的“憲法專政”時代?
作者心里清楚:“專政絕非醫治民主國家之災患的萬能藥。”但在危機時刻來臨之際,似乎只有“專政”最為行之有效。對于羅斯托而言,問題的關鍵在于:“專政者”是誰?“專政者”具備的政治德性如何?在作者看來,美國非常幸運,在歷次的重大危機中,都擁有強勢能干又極具“政治德性”的總統—這既是對“古典專政”理論的一種反叛,又是對魏瑪共和國失敗的一種回應。但是,誰又能保證美國永遠都會有這樣的好運呢?所以羅斯托寫作本書的目的并非為“專政”辯護,而是為專政立法,盡量避免“憲法專政”變為絕對王權的墊腳石—盡管他知道,一旦危機來臨,美國的總統們依然會將他所設立的原則棄之不顧,正如他寫下的:“如果我們在憲法專政一事上果斷行動,未來可能會比我們迄今為止所能想到的還要光明。”
(《憲法專政:現代民主國家中的危機政府》,羅斯托著,孟濤譯,華夏出版社二○一五年版,5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