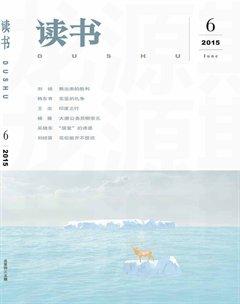日常抗爭與中國研究
羅東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以研究前資本主義的農村社會而著稱于西方政治科學界。他在《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一書中提出的“日常抗爭”(everyday resistance)是解讀底層抗爭的一個研究范式,同時也將他推向了學術爭議的中心。
先來看看斯科特提出“日常抗爭”這一范式的基本脈絡與邏輯。
該書源于斯科特在馬來西亞一個村莊為期十四個月的田野調查。他把它取名為塞達卡(Sadaka)。塞達卡在一九七二年引入雙耕(double-cropping),同許多地區的“綠色革命”一樣,這里的富人更富、窮人更窮。嚴重的階層分化使窮人(小農)不斷被邊緣化,也加深了他們的階級矛盾意識,但令人意外的是,這里并未就此而出現集體的反抗、斗爭、運動或革命。那么,這是否就意味著它是一個沒有任何抗爭印跡的和諧村落?斯科特敏銳地察覺到,沒有看得見的反抗并不是就沒有抗爭行動。看似寧靜,但已暗流涌動。抗爭正在默默地進行—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人們利用偷懶、裝糊涂、開小差、假裝順從、偷盜、裝傻賣呆、誹謗、縱火、暗中破壞等形式進行著持續的、不斷的日常抗爭。他們幾乎不需要協調或計劃,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網絡,以一種個體的自助形式,非直接地與權威對抗,同時規避了來自利益集團的政治風險。
從斯科特的論述中可以看到,弱者的武器經常是奏效的。用他的話說,正如成千上萬的珊瑚蟲雜亂無章地形成珊瑚礁一樣,成千上萬的以個體形式出現的不服從與逃避行動構建了自身的政治或經濟屏障。
但遺憾的是,這種對抗形式在以往的抗爭研究卻是被集體性忽略的。在西方中心主義下,有關抵抗或抗爭的一切圖景限于社會運動、革命等集體行動。
斯科特的研究功不可沒。他把底層社會微觀權力的運作邏輯與過程首次完整地呈現出來,這樣的敏銳洞察使得那些“未被書寫的反抗史”得以見天日。權力與政治不再僅是宏大的、組織化的敘事,還可以是微妙的、隱藏下來的日常抗爭策略。后者扎根于日常生活和支配中,持續性和耐性更強。
但另一方面,斯科特和他的“日常抗爭”框架也遭到了西方學術界的批判。
比如,科隆-漢森(Christian Krohn-Hansen)就指出,斯科特在得出他這一解釋框架前就預設了一個非常值得商榷的假設:社會中的成員個體是能動的(詳見Dialectical Anthropology雜志一九九五年第一期,71—94頁)。巴亞特(Asef Bayat)提出了同樣的批評,即由于沒有對抗爭的清晰定義,對底層日常行動可能會出現過度解釋或過高估計的問題。這似乎可以給人一種錯覺—任何行為都可以被視為抗爭(詳見International Sociology雜志二○○○年第三期,533—557頁)。換而言之,連偷懶、開小差或取綽號等這樣的行動都可被視為一種反抗,那還有什么不是抗爭呢?是否過于高估了農民的能動性?這或許是讀者最大的一個疑問。
對于科隆-漢森和巴亞特的質疑,斯科特在他“何謂反抗”一章已經給出他的預設性答復,他一直在努力走出現有的“反抗”定義。他認為,階級的反抗包括從屬階級成員所有如下行動:有意識地減少或拒絕上層階級(如地主、大農場主、國家)的要素(如租金、稅款、聲望)或提高自己對于上層建筑的要求(如工作、土地、慈善施舍、尊重)。賽達卡的行動是有反抗意義的,盡管他們有時是為了基本的生存而采取的類似偷竊這類行動—他在更早即一九七六年的《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中譯本可見譯林出版社二○一三年第二版)中將之表述為一種“道義經濟學”(moral economy)。抗爭是一個社會事實,但不再局限于西方知識架構中的集體行動,而是有了一個更為開闊的外延。斯科特的預設答復還不止于此。接下來的問題是,何種意義上,個體的反抗才可以成為一種抗爭行動或日常抗爭?斯科特用“珊瑚礁”做了一個比喻,“珊瑚匯聚成珊瑚礁”,也就是個體抗爭不再是孤獨而是普遍存在的歷史時刻。從斯科特的考察來看,盡管日常反抗的形式是個體在行動,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相互間沒有協同。作為個體的農民,日常抗爭的使用,總是有一套約定俗成的契約,同家人、親戚朋友等群體成員的態度是密切相關的。行動不再局限于個體的意義。如此看來,日常抗爭不是別的,或正是社會運動或階級革命的前奏。到那時,這些細小而零散的武器不再是無組織、非系統和個人的,不再是機會主義的和自我放縱的,不再是沒有革命性的后果。比如,有學者如阿德南(Shapan Adnan)在研究孟加拉的農民抗爭中就看見了這種向革命行動轉換的存在(詳見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雜志二○○七年第二期,183—224頁)。
中國學者在借鑒“日常抗爭”這一范式(或視角)的同時,也對它表達了質疑。
對于海內外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而言,這么一項外來的研究范式,首先將面臨它解釋力的邊界問題。郭于華在二○○二年將尚未有中譯本的《弱者的武器》介紹到中文學術界的兩年后,于建嶸就根據他在湖南的調查而提出,斯科特的解釋框架固然是十分有效的,但他的研究對象為東南亞地區,在具體的借鑒之中存在文化的差異問題。中國農民的抗爭已不再是日常抗爭(詳見《社會學研究》雜志二○○四年第二期,49—55頁)。這同歐博文(Kevin O’Brien)和李連江提出的判斷一脈相承,中國農民的抗爭不是日常的形式,而表現為一種依法抗爭,即外在的、理性的,且偶或還表達為組織化的行動。法律、國家政策文件等已成為他們的武器。于建嶸還將這一判斷繼續推前,中國農民的抗爭不僅不再是“日常抗爭”,還超越了“依法抗爭”,而進入了他稱之為“以法抗爭”的階段。抗爭不限于具體的權益,還表現出了一定的政治性。兩年前,筆者本人基于社會化媒體時代的到來,也具體地對斯科特“日常抗爭”及“公開的文本”、“隱藏的文本”的二分法提出了解釋力的適應性問題(詳見《香港社會科學學報》二○一三年秋冬號,33—67頁)。近來,在網絡討論中,有觀點認為,在中國鄉村秩序之內,“鄉村混混”是一個影響力頗大的群體,一旦他們當權,以暴力執法、統治,這時的農民表現出來的不是反抗而是服從。這是因為,這些混混出身于農民群體,對后者的行動邏輯或策略十分熟悉,以至于日常抗爭不再發生作用。但事實上,這樣的一些質疑,莫不是基于一定的空間、時間等維度的,是否擁有較為普遍的意義,還不得而知。這是因為,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狀況仍然沒有改變,社會空間非常狹小,強大的國家致使抗爭的合法性困境仍未改變。只不過,鑒于中國國土的遼闊與區域情況的差異,底層抗爭或可能出現“依法抗爭”或“以法抗爭”。正是因為存在這樣的差異,同是研究中國抗爭政治的另外一位學者應星又根據他的調查,對“以法抗爭”提出了他的質疑,認為于建嶸的政治熱情致使他過于高估了農民行動的組織化和政治性(詳見《社會學研究》二○○七年第二期,1—23頁)。孰是孰非?情況的復雜和差異可見一斑。這里的問題在于,他們尋找和研究的個案仍然脫離不了中國的“國家—社會”關系。除了個案的特殊性以外,筆者這樣說,還因為于建嶸等將日常抗爭與他們發現的抗爭形式在理論框架上對立起來,非此即彼,但事實上,即使是同一個區域,在不同的抗爭對象或事由中也可能存在不同的反抗形式。因此,對于鄉村混混消逝了日常抗爭這一判斷來說,這樣下定論還為時尚早,這在于:(一)“日常抗爭”本身是一個策略性的反抗,這里的服從是否意味絕對的服從,還是說只因研究者沒有發現服從背后的反抗形式,都還有待商榷,否則又將重蹈覆轍地將人民大眾置于無效的地位;(二)“弱者的武器”的內容是豐富的,在斯科特看來,意識形態也是這些武器中的一部分,如流言、起外號等。它們同樣可以銷蝕這些鄉村混混的合法性。
除了解釋力的邊界問題外,有關理論及方法論,中國學者同樣提出了對斯科特及“日常抗爭”這一范式的質疑。這樣的質疑甚至來得更尖銳。趙鼎新在他的《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一二年版)中就提出,斯科特歸納出的這一范式,屬于典型的解讀傳統(interpretation tradition),限于用特定概念來“說故事”,這些概念往往只能抓住事物或現象的一個或數個不太重要乃至是錯誤的側面。換言之,在他看來,“日常抗爭”是一個靜態的描述,無助于加深對一場具體的農民運動動態的整體性理解。他同時不屑地在該書第十一頁中寫道:“我不相信每個智力正常的人會沒有注意到這一無處不在的社會現象—如果我們沒有注意到這類現象的話,像磨洋工、怠工這類詞匯就不會成為日常用語。”在筆者看來,趙氏的質疑或批判實則折射出的是一個更大層面的討論,即解釋(explanation)與解讀(interpretation)之間長久以來的爭議。孰優孰劣,各執一詞。同時,這樣的批評還因為他們研究的反抗類型不同。趙氏熱衷于政治運動、革命等外顯的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s),斯科特關注的則是日常抗爭等隱形的個體行動。事實上,兩種行動表現,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也談不上相互矛盾。
回過頭來,再來看中國學者對斯科特及其“日常抗爭”的質疑或批判,無論是圍繞理論邊界還是方法論等問題,都沒有置于“國家—社會”這一根本關系下。這樣的后果在于,對于圍繞理論邊界來討論的研究者來說,他們的質疑僅僅是基于不同的空間或時間維度,但貿然地得出日常抗爭已經消失或失效的結論,重新將人民大眾看作無效的、被動的階級;而關于方法論的批判,則沒有注意到日常抗爭這一弱者的武器在中國語境下的現實意義,在中國當下的“國家—社會”關系框架下,它絕不是毫無價值的“解讀傳統”。
在筆者看來,斯科特的“日常抗爭”對中國研究正保持有不可低估的解釋框架作用。它同中國情況保持了極高的契合性。
這至少是因為:(一)“國家—社會”關系中,中國社會行動空間十分受限,國家處于絕對的優勢地位,因而對于訴求、維權或抗爭行動中的人們即行動者來說,合法性困境仍然是他們面臨的首要問題。(二)同時,同自由等西方權利不同,中國人的權利觀念是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歸納的“道義的經濟學”,即對生存權、福利的追求(詳見Perspectives on Politics二○○八年第一期,37—50頁),這種觀念支撐下的訴求或抗爭,是基于個人的生存而不是針對國家的權威挑戰,同日常抗爭這樣的抗爭形式有著高度的親和力。正是如此,它仍然在被人們艱難而又策略性地使用著。對于學術研究來說,合法性困境始終是理解中國抗爭政治一個十分關鍵的節點。這當然不意味著日常抗爭作為解釋框架是普遍可行的,但至少,它不該在還保持解釋力的地方被低估、被拋棄。我們仍然看到,斯科特提供的解釋框架及敏銳的洞察力,將有助于中國學者更深刻地理解處于轉型期中國的諸多社會問題。
盡管筆者并不贊同趙鼎新對于該框架提出的近于刻薄的批評,但他同時又說了這么一個令人深思的意思,即這種類似日常抗爭的解讀傳統下的第一本書或還有它的價值,但是“后面照貓畫虎的工作馬上就會變得越來越無聊”,這一說法有它的一些道理。當偷懶、取綽號等反抗形式已被概化為日常抗爭,接下來的工作多是尋找案例來驗證,如果研究止步于此,結果將是受制于既定的解釋框架,難以在理論中突破。多年來,對于那些借鑒斯科特及其日常抗爭的研究而言,鮮有實質性的突破。但中國香港學者潘毅(Pun Ngai)在對“長三角”的勞工研究中就令人稱奇地提出了日常抗爭的另一種形式—“身體抗爭”,即女工阿英在遭遇現行體制、全球資本主義和父權制三重壓迫下,在夜晚睡夢中的尖叫與夢魘。潘毅稱之為“抗爭的次文體”。該文先后以英文和中文發表,后收入到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Duke University Press and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5)一書中。盡管潘毅沒有說明是否受到斯科特的影響,但所揭示的這一抗爭形式已超越了斯科特定義的日常抗爭,拓展了它的外延。這種超越體現在,如果說偷懶、開小差或取綽號等形式還是行動者有意識的反抗,“抗爭的次文體”則進一步突破了意識的界限,已不再是意識層面的行動,按潘毅的說法,尖叫或夢魘等次文體介于意識與無意識之間。日常抗爭的形式或外延得到了拓展和豐富。潘毅的超越給了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這樣一些學術啟示,日常抗爭不僅出現在農民反抗中,還可能廣泛地存在于勞工等其他領域,同時它的形式并不局限于斯科特書寫的那些基本類型。如果將這些日常抗爭的形式在類型學上歸為一般形式與意識形態生產兩類,對于中國研究的現實意義就更加明了了。正像斯科特所言的那樣,一般日常抗爭形式將可能是矛盾集中爆發的前奏,在集體行動出現前就洞察到存在的反抗問題,有助于緩解和解決矛盾。同時,至于意識形態,它同樣是日常抗爭重要的一環。特別是社會化媒體空前發達的當下,大眾通過網絡匿名化表達出來的謾罵或綽號,同是觀察中國矛盾的一面鏡子。
日常抗爭根植于特定的“國家—社會”關系模式,為的是規避“強國家與弱社會”帶來的可能風險,而不是挑戰國家政治。
(《弱者的武器》,詹姆斯·斯科特著,鄭廣懷等譯,譯林出版社二○○七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