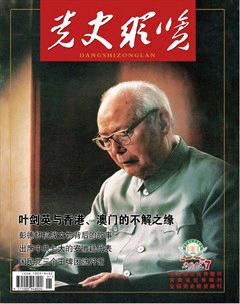袁殊:“與狼共舞”的紅色特工(下)
盧荻
周旋于兩國四方之間
1937年4月,中日關系日趨緊張,日本排華事件不斷發生,袁殊決定立即回國。巖井也找到袁殊,希望在日中關系“破裂”后袁殊能繼續和日方合作。但袁殊回到上海后,首先去找馮雪峰,匯報了自己在日本的情況,希望黨對他今后的工作有所指示。鑒于袁殊的情況特殊而又復雜,馮雪峰一時也不知道如何安排為好。當時不少同志都認為袁殊早已是“轉向”人物,不能輕信。馮雪峰于是讓袁殊先利用舊關系找點事情做起來再說。袁殊只好獨自行動,他找到舊幫會的關系,由杜月笙資助他辦了一個并不起眼的“時事刊行社”,實際上不過是做了杜月笙門下的一個食客。一貫雄心勃勃、熱衷于追逐政治浪潮的袁殊,一時間竟成了一個沒有政治立足點的“盲流”,他感到十分彷徨。
不過,沒有多久,他就找到把他引上革命道路、引上情報戰線的領導人潘漢年。潘漢年1933年離開上海,先到江西中央蘇區,其后參加長征,后來輾轉于莫斯科、南京、陜北等地。1936年秋后,他以中共代表身份,回到上海,與國民黨代表開展第二次國共合作談判,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不久,潘漢年擔任了中共上海工委主任,抗戰爆發后又擔任了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全面擔負起了指導整個上海黨的工作。
袁殊向潘漢年匯報了自己近幾年的大體經歷,懇切地表示希望能夠在黨的領導下為抗日盡一份力。為了表示真心和誠意,他將一份從日本帶回來的日本軍用地圖作為情報資料交給了潘漢年。當時馮雪峰、夏衍仍對袁殊頗具戒心,認為他難以信任。但潘漢年從黨的戰略與策略高度出發,經過慎重考慮,排除了夏衍等原先表示不宜用袁殊的意見,決定接受袁殊的要求,恢復了與他的聯系。與此同時,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國民黨軍統頭目戴笠急需日軍情報,而他一時找不到熟悉日本問題、又有相當的日本關系的人。后來,杜月笙提醒他,有一個叫袁殊的日本留學生與日本領事館副領事巖井英一關系不錯。戴笠聽了很高興,于是親自登門拜訪,表示要委以重任。當袁殊將這一情況向潘漢年匯報后,潘漢年認為這是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從當前看,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參加軍統敵后工作有利于抗日;從長遠看,在軍統打入一個楔子,以后在情報方面也可以發揮積極作用,因此,潘漢年同意袁殊加入軍統工作。于是,袁殊接受了戴笠的任命,一躍而成為軍統上海區國際情報組的少將組長。戴笠給袁殊安排了兩項任務: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報;二是堅持留在上海,不管時局有怎樣的變化。從此,袁殊通過各種關系,大量獲取日本情報。自然,首先是向潘漢年匯報,然后,有選擇地給軍統匯報——畢竟是國共合作時期,雙方有共同的民族利益。
“八一三”淞滬抗戰期間,袁殊置生死于度外,化裝成日本學生,越過戰線,深入到了日軍陣地偵察,提供了至關重要的軍事情報,使中方避免了很大損失。
上海淪為“孤島”后,潘漢年撤離上海前往香港,暫時中斷了與袁殊的聯系。袁殊奉戴笠之命繼續留在上海。他不僅大搞情報,而且成立了秘密行動小組,組織了一系列的暗殺活動,打擊日本侵略者和漢奸頭面人物,其中最為成功的是炸毀了日本在虹口的海軍軍火倉庫。為此,軍統給袁殊記了大功。
1938年秋天,袁殊被召赴香港參加戴笠召開的軍統骨干工作會議。會上,戴笠對潛伏敵后有功人員恩威并舉,一面對他們大大獎勵一番,并當場送給每人兩把最新式的加拿大手槍,一面又以冷峻的口吻警告他們,誰如果對我們的團體不忠,你們也可以拿這個去對付誰。聽了戴笠的話,袁殊內心有些惶然,他知道戴笠對他這樣非黃埔嫡系的人是不會完全信任的。會議結束前,戴笠還單獨接見一次袁殊,親自向他交代任務,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要他回上海后設法將已經投敵充當漢奸特工頭目的李士群除掉。
在香港開會期間,袁殊秘密會見了正在香港活動的潘漢年,向潘匯報了自己一年來在上海的工作。潘漢年語重心長地對袁說:“你這次來開會說明戴笠待你不錯。現在雖說是國共合作,但本質上兩黨是對立的。一個人的前途是在關鍵時刻決定的,向右,你可以跟著戴笠干下去,成為他的紅人。但我看你成不了他的紅人,軍統是清一色的黃埔派。這就要看你自己的決定了。”
袁殊從香港回到上海后,即按照戴笠的部署,策劃暗殺漢奸特工總部頭目李士群的計劃。誰知這一計劃尚未來得及實施,就因軍統上海區區長王天木和另一位軍統頭目陳恭澍被李士群的“特工總部”捕獲叛變告密而敗露。袁殊也因此而逮捕。李士群和袁殊過去就很熟,而且關系不錯。但這次袁殊直接指揮暗殺自己,不能不使李士群十分惱怒。在審訊袁殊時,李士群嚴厲地向袁殊交底說:“要么你就歸順我,和我合作,做我的幫手;要么我就按日本憲兵司令部的指令,將你處以極刑,希望你盡快做出選擇。”
在如何處置袁殊問題上,汪偽特務頭子之間發生了意見分歧。特工頭子丁默邨主張殺掉袁殊,而李士群因與袁殊在中統“干社”共過事,知道他是個日本通,認為此人有“可用之處”,主張刀下留人。在這千鈞一發之際,袁殊趁其妻馬景星到牢房送換洗衣服之機,暗示她去找潘漢年求助。潘漢年知道袁殊與日本特務頭子巖井英一有情報關系,不慌不忙地寫了一個電話號碼:“打個電話通知巖井救人。”巖井聞訊后,立即帶了兩個助手來到汪偽特工總部76號魔窟,以領事館名義和以袁殊是外務省系統情報人員為由,向丁默邨和李士群要人,丁、李不敢得罪主子,只得將袁殊放了。
袁殊脫險不久,巖井就要求他盡快寫出一篇論述中日關系的文章發表,要他公開表態。迫于無奈,袁殊便以“嚴軍光”的名義寫了一篇《興亞建國論》,內容大體符合日本人所謂“大東亞共榮”的論調。此文得到了巖井英一以及“梅機關”機關長、汪偽政府最高軍事顧問影佐禎昭少將的認可,被譯成日文在中日多家報刊上公開發表。這樣,就把袁殊從幕后推到了前臺。
臥底日特巖井公館,大量獲取日本情報

1939年9月,時任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兼華南情報局局長的潘漢年,在組織香港情報工作的同時,又奉命著手加強上海的情報工作網絡。他要搜集延安中樞機構急需的有關日偽以及美、英與蔣介石政府關系方面的情報,自然想到了與國民黨軍統、日本情報部門有聯系的袁殊。而袁殊更希望從潘漢年那里獲得對今后工作的指示。見面時,袁殊將自己近一年來的情況向潘漢年作了匯報。他說,巖井在領事館以外的地方弄一座樓房以巖井公館的名義搞了一個情報攤子開展活動,要他參與此項工作。潘漢年經過認真思考并報請中央批準后,決定讓袁殊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他對袁殊說:“你可以答應巖井的要求,將計就計,在敵偽之間建立一個親日的團體,既可干擾汪偽政權的建立,又可為我黨所利用。”
根據潘漢年的指示,袁殊按照巖井要求,于1939年11月在巖井公館掛起了“興亞建國運動本部”的招牌,成立“興亞建國運動委員會”的機構。袁殊擔任主任干事和《新中國報》《興建》雜志社的社長。潘漢年在幕后給袁殊以積極的幫助。他從香港把改組派的舊人,經何香凝、廖承志做工作,表示愿意為抗日做些有益工作的陳孚木弄來擔任“興亞”的主任委員;又從桂林《救亡日報》把袁殊的舊友、中共黨員的翁從六調來當《新中國報》經理;將進步記者葉文津派到報社工作;還把從延安來的情報干部劉人壽安插進巖井公館擔任機要工作。“興亞”本部主要人員均由中共秘密黨員充任。所設電臺,亦由黨員掌握。“興亞”本部實際上成了中共在敵占區的一個重要情報機關。由于延安遠離情報中心上海,急需掌握日本大本營動向及日、汪、蔣三方相互勾結又相互矛盾的微妙關系與變化,袁殊則利用這個機構,通過與敵方首腦人物個別接觸、參加宴會、定期出訪、閱讀文件等多種渠道,搜集到許多很有價值的戰略情報,經劉人壽、翁從六,轉給潘漢年坐鎮的華南情報局本部,然后由潘漢年和張唯一綜合整理及時發給延安中央社會部。
為保持與軍統的聯系,潘漢年還讓袁殊給戴笠寫了一封親筆信。袁殊在信中說明由于王天木出賣,爆炸76號事敗露,被日憲兵司令部判死刑。因巖井出面營救,不得已與日本人“合作”,并表示自己身在曹營心在漢,希望繼續為抗日做貢獻,請戴笠予以諒解。潘漢年請一位與戴笠交情甚篤的人士親赴重慶,將此信送交。戴笠鑒于蔣日之間的微妙關系和情報工作的需要,遂親筆回信對袁殊表示理解和安撫,勉勵他繼續為軍統效力。
據劉人壽、何犖等回憶,潘通過袁殊等人的關系,從“巖井機關”獲得的重要情報有:“(1)1939年英法企圖犧牲中國對日妥協的遠東慕尼黑活動;(2)1941年6月13日德蘇戰爭一觸即發的報告,南方局早幾天亦有類似報告,為此蘇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謝;(3)德蘇戰爭爆發后,日本動向是南進而非北進,以及日美談判的情報等。這是個涉及蘇聯遠東紅軍能否西調的事情,對國內的階級動向也很有關系。”
1941年6月22日德軍進攻蘇聯,蘇軍倉促應戰,節節敗退,日軍下一步究竟是北進配合德國夾擊蘇聯,還是南進和英美作戰,這對中國和世界局勢都會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據說當時的毛澤東為此三天三夜沒有合眼。正是在這個緊要關頭,袁殊提供的日軍南進戰略情報,不僅為潘漢年,而且也為毛澤東解了燃眉之急。從1941年7月到9月間,潘漢年及時將袁殊等人提供日軍南進的戰略情報報告給延安。潘漢年侄子潘冠儒在接受采訪時說:“所以主席說了一個就是終于可以睡一個好覺了,而且還讓康生給小開(指潘漢年)回電,寫一個最大的好。康生說,在電文里體現不出這個最大的好,主席說那你就寫好好好好好,就五個好。”
在歐戰全面爆發之后,蘇聯始終擔心腹背受敵。在獲得中共提供的日軍南進可靠情報后,斯大林這才放心大膽地從遠東調出了幾十萬人的兵力到西線。后來,蘇聯歷史文獻紀錄片《莫斯科保衛戰》解說:“根據來自中共的可靠情報,斯大林果斷調兵”,從而擊退納粹德國軍隊,取得莫斯科保衛戰的重大勝利。袁殊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勝利,做出了相當的貢獻。
利用職務之便從事秘密工作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攻香港。中共中央和周恩來緊急致電廖承志、潘漢年、劉少文和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等,指示立即幫助宋慶齡、何香凝等在港文化與民主人士安全離港。這年12月8日,袁殊自寧返滬,向潘漢年報告,汪偽陳璧君、陳君慧、林柏生等已飛抵香港,意圖誘騙滯港名士與南京合作。此后,300多名在港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如宋慶齡、柳亞子、陳濟棠、鄒韜奮、茅盾、胡蝶等,經各方努力,被成功轉移內地。
其時,袁殊頗得汪偽信任,先后擔任了汪偽國民黨中央委員、汪偽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偽清鄉政治工作團團長、偽江蘇省教育廳長、偽鎮江清鄉專員以及偽保安司令等職。他利用職務之便,及時向中共中央提供了日偽內部的人事更迭;蘇南日軍的兵力部署、清鄉行動等情報;建立通往根據地的秘密交通路線;營救新四軍被俘成員,掩護范長江、鄒韜奮等進入根據地等。袁殊任清鄉政治工作團團長后,暗中開展“反清鄉”活動:他首先向黨組織報告了日軍清鄉的重點區域劃分,粟裕部隊得到消息后,用門板搭在桌椅板凳上,連夜跳出籬笆墻轉移。他還利用職務之便營救被俘的新四軍、釋放被關押的地方黨群干部30余人。
1942年9月,中共中央電示仍留在上海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劉曉和潘漢年,考慮撤退問題。為保證劉曉和潘漢年安全轉移到新四軍根據地,袁殊接受了掩護撤退的任務。鎮江,本為連接蘇北的交通要道。他利用職權以及與汪日人員的關系,套取情報,使他任偽職的鎮江成為中共人員轉移的要道。此外,袁殊還為潘漢年從巖井處取得由領事館簽發的一張特別通行證,上書:“凡駐滬軍、憲、警等人對此證持有者有所檢問,務須與日本駐滬總領事取得聯系,不得造次!” 這無疑是一張護身符,保障了潘漢年的往來安全。
秘密轉移到解放區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已成不可逆轉之勢,日汪氣數將盡。袁殊辭去了其他漢奸偽職,只保留一項偽上海市政府參議的頭銜。這時,潘漢年已離開上海兩年多,接替他在上海工作的人雖和袁殊仍有一些聯系,但已很少。當此歷史又將發生重要轉折的關頭,袁殊再一次面臨了今后去向的選擇。
按后來袁殊自己的說法,當時面前有3條路:第一條路是攜帶家眷前往日本,做一個海外寓公。這樣一來,他就成了名副其實的漢奸,但他不想走當漢奸的這條路;第二條路是接受國民黨的收編,仍然可以高官厚祿。抗戰剛一勝利,軍統的王新衡就趕到上海,代表軍統任命袁殊為“忠義救國軍”新編別動軍第五縱隊指揮和軍統直屬第三站中將站長。然而,袁殊深知軍統內部派系林立,互相矛盾傾軋甚深。像他這樣非黃埔嫡系的人稍一不慎,是什么情況都可能發生的。
于是他選擇了第三條路,回歸他早年就曾經追求過,中間又經過了反復曲折的革命之路。臨走前,他著手清理“巖井公館”所屬的財產,將3大皮箱的金條、美鈔、英鎊以及大批房契、地契、銀行單據等價值近千萬元的財產,轉交給了上海秘密黨組織,顯示出了共產黨員的高風亮節。
1945年10月7日凌晨,在上海中共秘密組織和華中局聯絡部的精心安排下,由交通員黃煒護送,袁殊與翁從六、梅丹馨、李欽方等人通過新四軍浙東縱隊淞滬支隊駐地,又穿越國民黨軍隊管轄的狼山地區,從水路進入淮陰解放區。華中局聯絡部部長楊帆親自到碼頭迎接袁殊一行的到來。到達駐地后,陳毅、饒漱石分別宴請袁殊,歡迎他來到解放區,然后袁殊安全轉移到蘇北解放區,結束了長達15年的秘密情報生活。而直到第二年初,國民黨方面才知道了袁殊回到解放區的消息,不由得勃然大怒,于是,“抗戰有功人員”立即變成了“共黨漢奸”,軍統還對袁殊下達了通緝令,并派人去蘇州抄家。
袁殊投奔解放區受到了熱烈歡迎。數月之后,組織部門讓袁殊重新登記入黨,并任命其為華東局聯絡部第一工委主任,定為旅級,負責國統區寧滬一帶的策反工作。華中局組織部長曾山親自找袁殊談話,考慮到各種關系,建議袁殊暫時改名,對外改姓曾。從此,袁殊改名為“曾達齋”,一用就是近40年。在3年解放戰爭中,袁殊先后在蘇北、膠東、大連從事內勤工作。
坎坷的晚年歲月
1949年2月,北平解放。李克農親自調袁殊到國務院情報總署與中央軍委聯絡部工作,這是袁殊一生中最為紅火的日子。他每天工作到深夜,專門從事日本問題的研究,定期為《世界知識》撰寫有關日本問題的政論性文章,在部里被稱為“日本問題專家”。袁殊曾應邀為部里的干部和年輕同志作情報工作報告,朱德在聽了他的報告后,夸他是“我黨情報工作戰線不可多得的人才”。

1954年軍委在審干中給袁殊正式做了政治結論:1935年被捕時自首變節有嚴重政治錯誤,后來為中共做情報工作給予充分肯定。誰知“結論”的墨跡未干,1955年4月發生了潘漢年冤案,當年曾在上海為潘漢年工作過的秘密黨員幾乎無一幸免。同月26日,44歲的袁殊亦被捕入獄,1965年,袁殊被以“軍統特務”“日本特務”和“漢奸”罪名被判15年徒刑。1975年5月離開秦城監獄后,袁殊的行動仍然受限,被送到武昌大軍山的一個農場,參加學習和勞動改造。
在20年的牢獄生涯中,袁殊通讀了《資本論》、馬列著作、《毛澤東選集》,翻譯了大量日文書籍,撰寫了史料性傳記《大流氓杜月笙》,并仍然關注著黨的情報事業,寫下了近8萬字的《南窗雜記》,總結敵后情報工作的經驗。
1978年10月,袁殊第二次回京探親時,到中組部遞交了要求重新復查自己問題的信函,向高級人民法院遞交了申訴材料。他表示:“就是把我燒成灰,我也是心向共產黨的。”回到農場后,袁殊繼續進行申訴。他在給兒女的信中說:“監獄里的審訊記錄,都是我賴以平反的依據……政治上我對黨問心無愧,這一點我死可瞑目。”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袁殊等大批受潘案牽連的人也得到了平反。9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判決,撤銷1965年判罪,宣告袁殊無罪。同日,公安部、調查部復查袁殊政治問題,確認他于1931年加入中共,恢復其黨籍,批準他從國家安全部離休,享受原定級別待遇。原沒收財物折價歸還,于北京西苑分配新房一套。當一切都成為歷史之后,他向黨組織提出恢復原名,他認為“用袁殊這個名字沒有什么可羞恥的”。
此后,年逾古稀的袁殊曾回到潘漢年的家鄉,悼念逝去的戰友,緬懷過往的崢嶸歲月,寫下了《履痕重印江南路》的文章。1987年11月26日,袁殊在北京解放軍309醫院病逝,享年76歲,葬于八寶山革命公墓。
(責任編輯: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