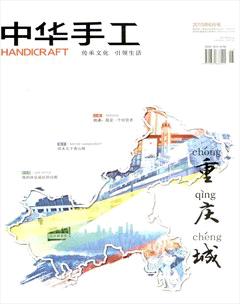磁器口向左
姜宇
磁器口古鎮(zhèn),這座始建于宋代,曾經(jīng)“白日里千人拱手,入夜后萬盞明燈”的水陸碼頭,歷經(jīng)千年變遷,現(xiàn)在已成為重慶重要的人文景區(qū)。在歷史與時代的交替中,磁器口古鎮(zhèn),被時代烙上了太多的印記,但它似一位睿智寬容的老者,一直固執(zhí)地堅守著都市時尚稀缺的特質(zhì),默默前進。
追憶磁器口
作為重慶的一張名片,磁器口古鎮(zhèn)在山城人民心中的分量著實不輕。然而,在旅游業(yè)的發(fā)展和刺激下,原本幽靜的老街小巷也不免被商業(yè)的硝煙浸染。無論周一還是周日,磁器口似乎永遠人頭攢動、人聲鼎沸。過往的游客可以在這里品嘗地道的重慶小吃,可以購買心儀的小玩意兒,也可以尋覓歷史人文遺跡留念合影。
悠長的石板路,青瓦灰墻,隱藏在木板房背后的幽深院落;文人酒肆,古玩字畫,茶館書場……“啪”,一聲響亮的醒木,“一條石板路,千年磁器口……”不在磁器口聽一回書,永遠品不了古鎮(zhèn)的意境。幾步之內(nèi),必有書場。落座,一杯濃釅的老沱茶,在清洌的香氣里,剝一盤鹽水花生,聽人幽默詼諧地講:“唐三千,宋八百,說不完的三列國。”老街的味道,自然還有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毛血旺,豆腐腦,千張皮,椒鹽花生,絞絞糖……毛血旺,椒鹽花生,千張皮,已被列為“古鎮(zhèn)三絕”,其實無非都是民間常見的食品,卻成為最具代表性的美食,彰顯著古鎮(zhèn)的性格與風俗。
如今,要追憶清幽的古鎮(zhèn),只有在曲盡人散的黃昏。褪去了白日里的繁華喧囂,此時的古鎮(zhèn),才肯卸下商業(yè)化現(xiàn)代化的浮華外衣,將過往娓娓道來。
隱人隱市
磁器口古鎮(zhèn)作為抗戰(zhàn)時期沙磁文化的發(fā)源地,聚集了無數(shù)名流精英,徐悲鴻、吳冠中、豐子愷等美術(shù)名家都與古鎮(zhèn)有著深厚淵源,還有教育家高顯鑒先生艱苦辦學,國學大師吳宓在磁器口的“隱居奇聞”,皆為人樂道。
到現(xiàn)在,古鎮(zhèn)的老街小巷,也隱藏著不愿離開的畫家文人。即使熟悉的磁器口已越來越遠,他們?nèi)匀辉谶@里,游江的閑畫藝術(shù)雜貨鋪,開在古鎮(zhèn)的標志性景觀——華子良接頭處。之所以叫“閑畫”,是因為游江的畫充滿著閑散的意味,那種對慢生活的展示和描摹,是經(jīng)歷了大半生的奔波而沉淀了又飄散了的意境。游江也是“閑人”,他的生活狀態(tài),就是看書、畫畫,與朋友聊天、喝茶。在這樣閑散的理想生活之前,游江當過工人,做過攝影,干過記者,最后來到這古鎮(zhèn),租了這間不大的民房做畫室,這一住,就是八年,再也沒離開過。
同游江一樣的“釘子戶”,還有“老重慶畫坊”的姚敘章,坐鎮(zhèn)十年的李春泉等等。除開這些老人,那些來自全國各地的年輕文藝青年,也被古鎮(zhèn)獨特的韻味所吸引,陸陸續(xù)續(xù)地來到這里,成為了名副其實的“磁漂”。
向左向右
實際上,今天的古鎮(zhèn)也并非處處繁華熱鬧,左街和橫街略微冷清,鮮有行人。聚集在這里的,是那些深藏不露的年輕手藝人和他們的文藝小店。門口隨意堆滿綠植的手工小店,店里的商品,全是主人親手制作的小玩意兒,好看的,實用的,不知道用來做什么的,無不凝聚主人的用心。在街的最深處,門口精心擺設(shè)的多肉植物和龍貓仿佛在招手,走進店里,被滿目的綠植和圓玻璃里的微景觀迷離了雙眼,這里是“懶魚時光”,算是橫街的一個標志了。作為一家頗受歡迎的微植物景觀手工店鋪,它帶動了左街和橫街的文藝手工氛圍,成為文藝愛好者的風向標。有時候,一些巧合,會讓一片土地孕育出令人意想不到的美麗。
在這里,有流浪他鄉(xiāng)只為尋找一處心靈棲息的游人;有厭倦了浮躁繁忙的城市生活,愛上了遠山靜水,江岸孤鳥的都市白領(lǐng);還有那從未更改,只求潛心創(chuàng)作的手藝人……不論何人,來自何地,有何過往,在這里,他們可以隨心隨性,不忘初心。
是的,如果恰好你也有一顆文藝的心,或者你也對手作感那么一點興趣,不妨避開熙熙攘攘的人流,轉(zhuǎn)身向左或向右,去看看那些年輕的執(zhí)著與堅守。
一座城市的縮影
透過磁器口古鎮(zhèn),我們看到的,其實是一個時代的變遷和發(fā)展。當城市走得越來越快,飛得越來越高,那些漸漸被遺忘的舊時人文,因磁器口古鎮(zhèn)的“抱守殘缺”,得以在人們的心里,留存都市繁華里安靜的一角。這些舊時光景,也只有在這里,還能依稀辨別回憶。這是磁器口的獨特氣質(zhì),正是這由歷史沉淀和文化內(nèi)涵構(gòu)成的獨特氣質(zhì),磁器口才能在快速前進的時代,堅持自己的風貌,滿足人們?nèi)找娓邼q的精神需求。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