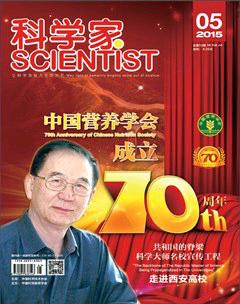中華文明向何方?
應行仁
美國華盛頓大學系統科學與數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智能控制、博弈理論和復雜系統。
中華文明正在三叉路口上,一邊是堅持傳統吸納消化西方文化的精華,一邊是徹底改造文化基因成為西方的同類。
在漫長的幾千年,我們曾被外族入侵統治過,但中國傳統文化都能包容吸納外來的異端。百多年前我們被打痛了,輸入革命圖強,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血火戰亂,折騰除舊,在滿目瘡痍的廢墟上驀然醒來,回到務實的中庸傳統,不爭議,不拘一格,埋頭建設,取得了不俗的物質成果,精神上卻前所未有的空虛,在涌來的影視、廣告、評論、新聞等西方意識形態的洪流中,急于跟上潮流的先進知識分子已經沒有傳統文化的底蘊和自信了。
中國經濟和國力在200多年前的歷史中大多領先世界,科舉和官員選拔制度曾被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所盛贊,形成了現在通行的文官制度,伏爾泰甚至鼓吹過“全盤華化”。即使在笛卡爾、培根、牛頓、盧梭和啟蒙運動之后,在清朝腐朽統治下的18世紀下半葉,中國仍然是相對成功的,所占的全世界制造業份額從1750年的32.8%,增加到了1800年的33.3%。轉折點發生在英國的工業革命,中國從1800年的33.3%,下滑到1830年的29.8%,再下滑到1860年的19.7%;而英國則從1800年的4.3%,激增至1830年的9.5%,并于1860年以19.9%的份額首次超過中國,成為全球第一。
到了這時,中國不再具有明末一個海盜鄭芝龍,便能夠打敗荷蘭和歐洲所有國家海軍的軍力了,兩次的鴉片戰爭和大炮巨艦讓天朝驕子淪落為東亞病夫。戰爭是轉變人們思想的暴力,這被歸結為中國需要“德”先生和“賽”先生。科學研究不僅促進經濟發展,提高生活水平,也造出武器以力服人,這最終展現出的威力,以致命的說服力成為必須跟隨的對象。
為什么歷史上中國一直領先的經濟和輝煌的文化沒有結出科學之果呢?中國傳統文化能否兼容科學思想,還是必須徹底拋棄才有希望?這得了解歷史是怎么走來的。
與蘇格拉底、芝諾、亞里士多德、歐幾里德同時期,中國正處春秋戰國,幾個學派都對“名”和“實”的關系提出自己的看法。“名”是抽象的觀念和語言能指,“實”則是具體的事物和語言所指。儒家有“必也正名乎”,法家有“綜核名實”,墨家有“以名舉實”。名家提倡“循名責實”的學說。“正名實”,是要“正彼此之是非,使名實相符”,公孫龍(320BC-250 BC)是名家的代表人物,用邏輯思辨來分析事物,研究如何精確地運用概念和語言,這是基礎領域的研究,但與現實和政治應用無關。
趙孝成王十年,齊鄒衍過趙,平原君使與公孫龍論白馬非馬之說。鄒子曰:“不可。夫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敦,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后息,不能無害君子,衍不為也。”座皆稱善。公孫龍由是遂絀。
這是個標志性的事件,發生在公元前256年,公孫龍游歷列國,以其學術研究相詢,各家莫與能辯,門客三千的趙國權相癡迷于公孫龍的邏輯悖論,請創立陰陽五行學說的大師鄒衍與公孫龍進行學術辯論,鄒衍對此不感興趣,認為辯論目的只要分辯意思明白所指就行了,糾纏于語言和邏輯的嚴謹性思考,于解決實際問題無益,對國家治理和個人修養有害。這觀點得到大家的認同,從此公孫龍為代表,對抽象概念邏輯分析的研究退出中國學術舞臺,他的思辨被斥為詭辯。而陰陽五行學說,因為對政治,軍事和醫學的實踐有指導意義,成為研究系統變化規律的通用模型。
與這事件差不多同時代的希臘,亞里士多德(384BC-322 BC)得知芝諾的悖論時,卻極感興趣,與他的學生們認真探討,用以磨礪充實形而上學理論。傳至歐幾里德(325BC-265 BC),終于奠定了用抽象邏輯推理方式來證明定理的西方數學基礎。
人腦中神經網絡決定了智力的基礎是模式識別,推理的本能是聯想記憶,邏輯不是人固有的能力,也不是世界運行的方式,而是人腦依照規則訓練出來的技能,用它來作為精確知識傳遞的工具。它不能遺傳,只能通過學習訓練來獲得。悖論的思辯則是嚴謹邏輯推理的必經之路。
中國傳統文化錯過了名家為代表的思辨研究,沒有建立起嚴謹的抽象和邏輯推理學術基礎,只依賴于本能的模式識別類比推理。這局限了數學的發展,在西學東傳前,中國只有針對具體問題的算法和例示的結論,沒有針對一般問題的公式和定理。對物理的研究缺乏精確的定量結果,只有定性的變化模式。這讓我們在歷史上只有技術發展,沒有公式理論。這是我們文化必須補上的課。
嚴謹的概念抽象和邏輯推理只是一種訓練,這個來自古希臘的思想精華可以被任何文化所兼容吸納,過去的羅馬帝國和后來的歐洲文化對它是這樣吸收的。現代中東、印度和中國學生一但接受數學訓練,數理成績都不比浸淫在其中幾百年的西方差。所以傳統文化不成為吸納它的障礙。
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真正的不同是對“真理”的態度。這個本質的區別源于文化的基因。
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盡管教義不同,但都崇拜一個唯一正確的神,這個一神的觀念排斥了任何與之不同的權威,其直接的推論是:世上有著唯一正確的客觀真理,這個真理指的是上帝的意旨,后來在科學里被解釋為自然規律。追求真理是信仰崇拜的表現,深植在西方文化中,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美德。
中國文化是務實的,當西方致力于上帝崇拜時,儒家對鬼神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只是不感興趣:“敬鬼神而遠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強調“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中國人求知的動力是人在生活、經濟、戰爭和政治上的競爭博弈。中國傳統應用知識的方式是:理解事物變化模式和用試錯反饋方法在實踐中來尋找平衡和控制,從烹調、醫療、治國、軍事到數學計算的迭代算法無不如此。我們不關心世界到底是什么,只關心怎么變成和保持所希望的狀態。達者和高人追求的“道”是對變化和技能哲理的領悟,而不是一種絕對答案的信仰,可悟不可教。西方愛好自然科學理論,中國喜好控制和博弈技術。前者窮究細節追求絕對正確的真理,后者用簡單黑箱模型描述系統,尋求恰到好處的控制,達到不偏不倚的中庸狀態。這務實的態度,讓我們在經濟和管理上保持歷史上長期的優勢。
歷史上西方不事生產的神職人員,出自對真理的追求,應用演繹推理,醉心于理性思辨。自基督教開始流行一千多年中,雖在數學、文藝和哲學上有些發展,但追求的是對上帝意旨的詮釋。即使伽利略和哥白尼的研究更符合實際,也因不符教義而遭禁止和迫害。真正改變這個局面是在人文主義對神學反叛后,培根(Francis Bacon 1561年-1626年)提出以觀察和實驗來發現和檢驗的科學方法,這才將理性思辨落力在現實世界上,發展成對生產技術實用的科學研究,在工業革命的推動和戰爭軍方的需求下,科學研究才開始飛速的發展。
如今我們繼承務實的傳統,以經濟發展、生產需求為動力,接受西方學術成果,致力科學研究,發展技術,希望像歷史上一樣,用我們豐厚的文化來包容、吸收西方文化的精華,復興中華文明。為什么滿腹西學的精英對此十分反感?
因為西方的文化基因是一神論,只有一個真神,只有一種真理,不容許異端。為這理念奮斗才是“追求真理”。從西方文化的角度來看,你與我不同的部分都是錯的,中國文化只有能在“先進”文化中有投影的部分才是可取的,其他都是必須剔除的糟粕。他們認為兼容并蓄容忍矛盾是缺乏信仰,只重功利的山寨行為,認為這不是追求真理的態度。依此來看,以中國傳統學術理論為基礎的中醫,各種技術和歷史經驗,則是缺乏科學根據,因為用現在科學知識不能解釋,所以必須拋棄或改造。
在西方的真理中,人曾經只是神的玩偶,被壓抑了一千多年后才反抗,整個西方的思想史幾乎是信仰與人性的搏斗史。對上帝的崇拜深植在西方文化中,是他們痛苦和驕傲的根源。所以無法容忍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早就僭據了世界的中心,對鬼神敬而遠之,即使村夫愚婦對神靈的態度也是在敬畏中役使,遇事求神拜佛,供奉膜拜只為祈福護佑,殊無崇拜的虔心。西方傳統道德觀念來自圣經的教誨,所以無法理解沒有信仰如何有道德。對儒家以祖先和宗族崇敬,光宗耀祖為榮不使蒙羞的動力,禮義廉恥的道德觀念,認為是愚昧落后的封建糟粕,而對于西方的基督教,雖然具有明顯的奴隸制色彩,卻寬容地不妨略其詳而取其意,著眼于美好的精神追求。
西方習慣懾服于神的權威,認為權力和權利必須來自神的恩賜或神圣的天賦,所以帝王需要教皇的加冕,總統要用契約的權利讓渡來證明其合法性,至于這個契約是坑蒙拐騙來的,還是城下之盟并不深究,只求據此心安。而務實的中國百姓千年前就懂得成王敗寇,有誰讓我們生活好就擁戴誰的心態,有識之士大多不信忽悠,有穿越“假裝被嚴肅對待的謊言”的能力,連君王都知道“水可載舟也可覆舟”,政權既不靠神也不可能靠契約來保障的本質,其興替取決于執政的效率。
西方的“追求真理”注定了,喜好強加于人的侵略性。而對應于中國務實文化基因的追求,則是中庸,包容矛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個人能否做到則是修養的問題。
研究科學要“追求真理”,如果指的僅僅是探索中的執著精神,這類同于我們傳統文化的求知悟道,在各種文明中都是被視為美德的。但如果特指堅持一種絕對正確排它性的“真理”,就要思考這個信仰中的觀念是否真實。
世上許多習以為常、十分神圣的觀念,不過是經過長期灌輸視為真理的謊言,其實都經不起邏輯的推敲。例如:將自由民主與排它性信仰共治一爐的現代西方意識形態。自由是不受約束,民主是容忍分歧;它們與信仰排它性的組合,依照邏輯是個矛盾。堅持后者,則對前者只會是策略性的容忍;相信前者,則要放棄追求排它性真理的信仰。科學是一個不斷改變其定義的概念,許多客觀規律也許只是用語言的概念鉤織出來的幻象,我們卻視為永恒不變的絕對真理,用它作為標尺排斥一切異類。
中國傳統學術研究思想有否價值,這要先問:以還原論為基礎的科學研究,真的能從微觀機制中了解宏觀系統嗎?我們知道對計算機硬件的研究,不可能了解軟件的功能,那么怎么可能從解剖和分子機制中,就能完全了解人體和維持健康?現代科學所了解的世界不過是用“合法的”研究方法在大地上開辟出的公路網,大道之外是更廣闊的未知世界。為什么我們不允許離開大道,用現在科學還不能理解的方法來探索自然的秘密?
從更大的視角來看,造成偉大進步的思想方法不一定是一樣的,真實的世界未必是在現在文化知識下我們所感知的那個幻象。文明發展的一時優劣并非完全是由其內在的因素所決定,偶然的因素和環境會起很大的作用,中國兼容性與西方排它性的文化基因不同,就像進化中的不同生物一樣,只要不被扼殺,中華文明未必不能發展出更富有創造性的理論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