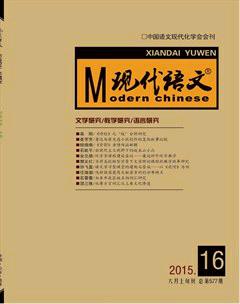從小說回目管窺金梁武俠小說的現代轉型


摘 ?要:金庸、梁羽生是新派武俠小說的兩大宗師,但二人小說回目卻有很大差異。在形式上,梁羽生的回目大多格律嚴謹、工整規范,而金庸的回目卻形式多樣,灑脫不羈;在功能上,梁羽生的回目主要繼承了中國古典小說的敘事功能,而金庸的小說回目則更多地轉向了西方小說標目的提示功能。二人的小說回目理念也與其整個的武俠小說創作相一致。梁羽生的武俠小說雖有新變,但其創作終究未能脫離傳統小說的窠臼,而金庸的小說則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大量采用西方小說技法,融匯現代意識,由此實現了武俠小說的現代轉型。
關鍵詞:金庸 ?梁羽生 ?新派武俠小說 ?小說回目 ?現代轉型
金庸、梁羽生是新派武俠小說的兩大宗師,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被稱為“一時瑜亮”,但最終金庸聲名日熾,而梁羽生則相對“門前冷落鞍馬稀”。這一文學現象值得我們深思。其實,二人的武俠小說雖然同為“新派”,但呈現出較大差異,從二人的小說回目便能窺見一斑。金庸的小說回目呈現出形式多樣的特點,其思想內核也融匯了明顯的現代意識,回目功能更多的是西方小說標目的提示功能,而梁羽生的小說回目在形式上趨于工整規范,并延續了中國古典小說的敘事功能,雖然也有求新之處,但基本上未能脫離傳統的窠臼。從小說回目這一角度,我們能管窺金梁整個武俠小說的創作思想,并從小說現代轉型的角度為二人武俠小說的不同命運作出一個合理的解釋。
一、回目形式:規范與灑脫
梁羽生35部武俠小說的回目風格較為統一。(參見表1)他的小說回目,大多數是七言單對、七言雙對、八言雙對、九言雙對的回目形式,句式整齊,屬對工整,并且平仄葉韻,頗堪吟詠。其實,古典小說回目在句式、對仗、平仄方面并沒有這么嚴格,而梁羽生運用自己深厚的舊學造詣,以詩詞格律對古典小說回目進行了嚴格的規范,從而使得其小說回目整齊修葺,音韻和諧,在形式上趨于完美,呈現出規范化和模式化的特點。這是他對古典小說回目的一次有意識的改造。他也有一些小說的回目,句式并不整齊,往往一篇之中,七言、八言、九言、十一言、十二言等回目交錯排列,而表現出一種參差之美。這些小說的回目,雖然有所變化,但仍然屬于舊式回目的范疇。另外,梁羽生還有一些小說的回目突破了傳統的形式,采用白話的新式回目,回目字數不定,如《飛鳳潛龍》《塞外奇俠傳》,但那只是其小說作品的極少數情況,并且梁羽生本人對這一類回目也未加以重視。譬如,《草莽英雄傳》最初在《新晚報》連載時,第一章回目為新式回目“不近人情的女俠”,后梁羽生覺得不妥,從第二章開始又改為舊式回目,復歸于傳統,由此可見梁羽生本人對舊式回目的獨特偏好。
與梁羽生規范至完美的小說回目不同,金庸的小說回目往往是灑脫至極致。(參見表2)金庸早期的作品諸如《書劍恩仇錄》《碧血劍》等仍然沿用舊式回目的形式,分別為七言雙對回目和五言雙對回目,但是相對于梁羽生而言,這些回目在對仗、平仄方面都顯得拙劣。梁羽生就曾經揶揄金庸說:“金庸很少用回目,《書劍》中他每一回用七字句似是‘聯語的‘回目,看得出他是以上一回與下一回作對的。偶爾有一兩聯過得去,但大體說來,經常是連平仄也不合的。”[1]金庸在《書劍恩仇錄》的《后記》中也承認說:“本書的回目也做得不好。本書初版中的回目,平仄完全不葉,現在也不過略有改善而已。”[2]后來金庸揚長避短,其小說回目創作不斷進行探索新變,逐漸擺脫了舊式回目的束縛,從而使其回目形式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譬如《笑傲江湖》的回目是兩字詞語,《射雕英雄傳》和《神雕俠侶》的回目是四字詞語,在《倚天屠龍記》中,他仿作柏梁體詩,在《天龍八部》中則填詞五首作為小說回目,在其收官之作《鹿鼎記》中,他集句清代査慎行的詩作為小說回目,可謂異彩紛呈,不一而足。更為瀟灑的是,在《飛狐外傳》《連城訣》《俠客行》中回目字數無一定之規,完全隨性自然,而在《雪山飛狐》《白馬嘯西風》《鴛鴦刀》中則直接摒棄了回目,僅分章回而無回目。由此可見金庸在擬定小說回目時的灑脫不羈。
表1:梁羽生35部小說回目形式表
書名 回目形式
《女帝奇英傳》《冰魄寒光劍》《還劍奇情錄》 七言單對,相鄰回目對仗
《大唐游俠傳》《龍鳳寶釵緣》《慧劍心魔》《狂俠天驕魔女》《鳴鏑風云錄》《瀚海雄風》《廣陵劍》《武當一劍》《云海玉弓緣》《冰河洗劍錄》《風雷震九州》《俠骨丹心》《牧野流星》《彈指驚雷》《絕塞傳烽錄》《草莽龍蛇傳》 七言雙對
《劍網沉絲》《幻劍靈旗》 八言雙對
《萍蹤俠影錄》《散花女俠》《聯劍風云錄》《白發魔女傳》《江湖三女俠》《冰川天女傳》 九言雙對
《武林天驕》 四言回目
《風云雷電》 以四言回目為主,間有五言、七言、八言
《武林三絕》 除首回為七言回目外,其余回目為四言回目
《游劍江湖》 除第六十三回為五言回目外,其余為四言回目
《七劍下天山》 以十一言雙對為主,兼有九言、十二言雙對回目
《龍虎斗京華》 五言雙對
《飛鳳潛龍》《塞外奇俠傳》 字數不定,在兩字到八字之間,語言為白話
(注:本表據中山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全套《梁羽生作品集》制定。其中《武林三絕》沒有正式出版,所以該書依照梁羽生家園網站http://www.yushengbbs.net/book/lys/00ml.htm提供的回目)
表2:金庸14部小說回目形式表
書名 回目形式
《笑傲江湖》 二言回目
《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 四言回目
《碧血劍》 五言雙對
《書劍恩仇錄》 七言雙對
《鹿鼎記》 七言雙對,集句査慎行詩
《倚天屠龍記》 七言單對,押韻,仿柏梁體詩
《天龍八部》 字數不定,填了五首詞作回目
《飛狐外傳》《連城訣》《俠客行》 字數不定,基本上在兩字到七字之間
《雪山飛狐》《白馬嘯西風》《鴛鴦刀》 無回目
(注:本表據廣州出版社、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全套《金庸作品集》制定)
二、回目功能:敘事與提示
中國古典小說回目的主要功能在于敘事,即用回目概括本回的主要故事情節。而西方小說標目的主要功能在于提示,即通過核心詞的提示來引導讀者進入正文故事的閱讀。梁羽生的小說回目主要繼承了傳統小說的敘事功能,而金庸的小說回目則轉向了西方小說的提示功能。
譬如,在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第六回和金庸《笑傲江湖》第十八章都有聯手抗敵的情節。梁羽生擬定的回目是“聯劍懲兇奇招啟疑竇;抽絲剝繭密室露端倪”,當時的主要情節是,張丹楓和云蕾在危急情況下雙劍聯手,抗擊黑白摩訶。在抗敵的過程中,他們發現對方的劍法似曾相識,二人聯劍配合得出奇一致,不覺威力大增,最終大敗黑白摩訶。待到黑白摩訶離開之后,張丹楓和云蕾獨處密室之中,張丹楓的真實身份便開始隱約浮出水面。可以發現,梁羽生的回目便是對這次雙劍聯手的故事情節的粗略概括,主要體現的是回目的敘事功能。而金庸《笑傲江湖》這一章擬定的回目只有兩個字“聯手”。誰和誰聯手?為什么聯手?聯手過程如何,勝敗又如何?我們都一無所知。直到我們讀完本章故事,才知道,原來是令狐沖與向問天聯手,共同抵抗追殺向問天的武林人士,最終二人順利逃脫追擊,還因此番聯手意氣相投,結拜為兄弟。此處主要體現的是回目的提示功能。
再如,梁羽生《七劍下天山》第十二回和金庸《天龍八部》第四十五章都有締結鴛盟的故事情節。梁羽生《七劍下天山》第十二回寫到桂仲明和冒浣蓮日漸情篤,暗自傾心,最終在傅青主、凌未風、石大娘等人的撮合之下,二人在幽谷之中交換信物,正式訂婚。這一回梁羽生擬定的回目是“幽谷締良緣喜有金環聯彩筆;江湖偕儷影爭看寶劍佩神砂”,是對這一故事情節的基本概括。在《天龍八部》第四十五章中,段譽和王語嫣相繼墮入枯井之中,王語嫣幾番遭遇慕容復的冷漠無情,逐漸心灰意冷,同時也為段譽的癡情所感動,最終對段譽以心相許,二人結鴛盟之誓。金庸這一回的回目為“枯井底,污泥處”,只是粗略點出故事發生的地點,以激發讀者繼續閱讀本章回故事的興趣。
由此可見,梁羽生的小說回目基本上屬于傳統路數,而金庸小說的回目,雖然也常從古典詩詞中汲取營養,但其思想內核卻轉向提示功能,是對古典小說回目的一大突破。正如李小龍所言:“金庸的回目恰是以最中國化的古典詩句形式包裝了西方式標目的內核,是一種中西小說標目的融合形態。”[3]從這一意義上來說,金庸在小說回目方面的探索比梁羽生要走得更遠。
三、現代轉型:漸變與突破
其實梁羽生的小說回目對舊式回目也有一些現代意義的新變,這主要表現在回目的心理描寫上。他善于在回目中融入人物的心理描寫,以《萍蹤俠影錄》為例,其中第二回“禍福難知單身入虎穴;友仇莫測寶劍對金刀”中,“禍福難知”“友仇莫測”便生動摹寫了云蕾初見張丹楓時的細膩心理。第四回“鑄錯本無心擂臺爭勝;追蹤疑有意錦帳逃人”,“鑄錯本無心”“追蹤疑有意”細膩地寫出了云蕾誤打誤撞成為黑石莊乘龍快婿后敏感而復雜的心理狀態。梁羽生在回目上的這一突破與其小說創作擅長心理描寫是分不開的。梁羽生自己也說:“梁羽生也有受到西方文化影響之處,如……近代心理學的運用等等。”[4]但是總體而言,梁羽生的新變只是緩慢而克制的漸變。中國古典小說的回目,到了梁羽生的手上,主要還是走向了規范化和模式化。
但是金庸卻以巨大的魄力對舊式回目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回目形式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向,既汲取了傳統文化特別是古典詩詞中的豐富營養,又融匯了現代意識,其回目功能則由古典小說回目的敘事轉向了提示。因而金庸的小說回目是對古典小說回目的一大突破。金庸創作回目的思想正與他小說創作的思想相一致。金庸在武俠小說的創作過程中,更多地運用現代的小說技法。其小說的語言靈動活潑,貼近自然,“努力創造出一種中國化的現代小說語言”[5]。其小說的結構,“是一種多重矛盾、多條線索、縱橫交錯而又相互制約的網狀結構,它適宜于表現比較宏大復雜的內容,較之章回體那種通常是單線行走的結構方式有大的突破。”[6]其小說刻畫的人物形象,或正或邪,隨意點染,皆有深度,而梁羽生小說的人物形象則多為名流俠士,類型單一,由此相形見絀。
因而,從金庸、梁羽生的小說回目創作,便可管窺出二人小說現代轉型的概況。梁羽生的小說固然有所新變,但總體上仍屬于傳統路數,因而逐漸落伍于時代潮流,而金庸則面對時代潮流,迎頭直上,在繼承傳統的同時,大力采用西方現代小說技法,別開一番全新氣象。1994年,梁羽生在悉尼演講時也承認:“我頂多只能算是個開風氣的人,真正對武俠小說有很大貢獻的,應是金庸先生。……他是中國武俠小說作者中,最善于吸收西方文化,包括寫作技巧在內,把中國武俠小說推到一個新高度的作家。”[7]梁羽生對新派武俠小說有首開風氣之功,但其武俠小說仍然未能脫離古典小說的窠臼。而金庸則使武俠小說真正實現了現代轉型。而這或許正是八十年代后,二人武俠小說命運不同的原因。
(本論文成果系華中師范大學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資助。)
注釋:
[1]佟碩之(梁羽生):《金庸、梁羽生合論》,《金庸評說五十年》,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年版,第208頁。
[2]金庸:《書劍恩仇錄》,廣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669頁。
[3]李小龍:《中國古典小說回目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05頁。
[4]佟碩之(梁羽生):《金庸、梁羽生合論》,《金庸評說五十年》,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年版,第203頁。
[5]孔慶東:《金庸評傳》,鄭州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頁。
[6]嚴家炎:《金庸小說論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頁。
[7][澳]劉維群:《梁羽生傳》,長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355頁。
(辜學超 ?湖北武漢 ?華中師范大學 ?43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