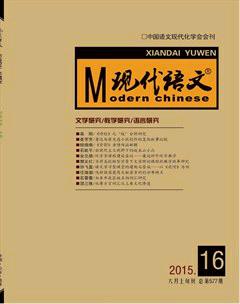女性主體意識的探尋
摘 ?要:王安憶的中篇小說《弟兄們》講述了三個互稱為“弟兄”的女性之間的愛情故事。本論文描述了她們三人之間姐妹情誼的建構及瓦解,并分析了她們的精神戀愛最終失敗的原因,從而探討了女性追尋自我解放的道路,并彰顯出作者女性意識的覺醒。
關鍵詞:《弟兄們》 ?姐妹情誼 ?建構及瓦解 ?追尋自我
王安憶在《弟兄們》這篇小說中寫的是三個普通人物的生活——從相識相知到分道揚鑣的過程,小說從女性視角出發,描寫三人之間建立起來的姐妹情誼的高尚可貴,但在與傳統男女戀愛模式的對抗中卻變得不堪一擊,促使我們去關注女性在自我解放的過程中,她們所經歷的心理變化和情感變化,以及女性建構自身主體性的努力。
一、姐妹情誼的建構及瓦解
(一)姐妹情誼的建立
這里所講的“姐妹情誼”,也就是指女子之間的精神之戀,具體是指女子之間相互了解、體恤,為了保有女性自我而互相鼓勵幫助,進行心靈上的溝通與探討,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一種不是姐妹卻勝似姐妹,特別是在心理上能互為“知已”的一種親密關系,是女人作為個人的相互交往。[1]她們班里只有她們三個女生,同住一個寢室,在這樣的生活學習空間里她們緊緊相連。她們在短暫的校園生活中,互相鼓勵、互相關愛,喚醒“在過去很久的日子里,她們都不了解自己是誰”[2]等這些被無意埋沒的意識,共同為自我的獨立和完整而奮斗,不斷地解放自我,還原各自真實的自我。她們把她們的姐妹情誼,看作是“一個自我滅亡與新生的奮博的過程”,是在“你拉著我,我拉著你中,才沒有沉沒”[3]。總之,“她們因能擺脫男人而感到生存的滿足,并且在同性相處之中獲得了自我認識和肯定的體驗,這種具有團結、平等、自由和發展特質的感情關系,是女性主義者極為重視的姐妹情誼”[4]。可以說,她們是幸運的,在這段時間,她們運用自己的“話語”進行精神上的交流和探索,建立了深厚的姐妹情誼。
(二)姐妹情誼的瓦解
小說中,她們三人的姐妹情誼是建立在假定存在“真實的自我”之上的。她們自認為可以擺脫女性身上的包袱,可以消除現實生活中的顧慮,解放自我,建構女性主體性。但是,在男人占統治地位的傳統社會秩序中,女性的自我是不可能實現的,這也就意味著建立在“自我”基礎上的姐妹情誼失去了其理想烏托邦的基礎。首先,《弟兄們》這個標題一方面反映了她們渴望像男人一樣擁有屬于她們的深厚情誼及強烈的自我存在意識;另一方面,我們應該看到在當今這個父權社會里,女性在言說自我時不得不借助男性話語,只有這樣,她們才能參與到歷史的敘述中來。這是女性意識覺醒的一個表現,但是對于她們的這種覺醒而言,其可能性只存在于三人的校園時光里,她們暫時脫離了家庭,脫離了社會。一旦她們回歸到自己的家庭和社會角色,這種美好的姐妹情誼將會被打破,她們身上的自我主體意識也將逐漸被消磨。
其次,我們來分析她們之間姐妹情誼瓦解的過程。她們的姐妹情誼最先遭受到老三妻性的破壞。老三認為,“無論自己怎么叫自己‘兄弟叫‘別人家的,弄到底,女還是女男還是男,這是根本無法改變的。完全徹底地‘自我是不可能實現的,說說開心而已。其實,重要的是,男人與女人之間有沒有愛情。如有愛情,誰被誰吞沒也都是快樂和有價值的。”[5]在學校的時候,每次她的丈夫來看她,她就偏離了三人原本堅持的自我世界,喪失了自己的話語權。畢業時老三為了自己以后的家庭和睦,放棄了留校任教發展自我的機會,而選擇了丈夫替她安排好的工作,在一個小縣城里過著平淡的生活。沒有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喪失了實現理想的機遇,剩下的只是生活的平淡忙碌,對于老三,自我的建構已不復存在。接著瓦解這份姐妹情誼的是帶著母性的老大。她們三個曾在鳳凰山下對著長江立下過這輩子決不要孩子的誓言。然而老大回來就叛變了。她雖然懂得自我的意義,但在日復一日地擠公共車,討價還價買菜做飯的平庸瑣屑生活中,自我于她已成了一樁過于奢侈的娛樂,她消受不起。她想念小孩,以此來緩解自己內心的落寞。當身體中另一個生命在成長時,她感到一個完整的自我回到了她的身上。孩子降生后,母愛使老大自覺地把她的生命全系在這個脆弱的小生命上,其實作為老大的“自我”已不再是在自己身上,而附在孩子身上了。[6]老大的那一句“別碰我的孩子”徹底斬斷了她和老二的姐妹情誼。留給我們的畫面是:老大的臉色鐵青,牙關緊咬,眉毛豎了起來,面目竟有些猙獰。淋漓盡致地展現出女性喪失自我的悲涼感。和老大、老三相比,老二可以說是一個相對純粹的女性。在她身上妻性和母性的因素都被淡化了,更多的是表現她對于女性獨立自我的追求。在這個過程中,她既清醒地堅守著女性獨立的精神,又對現實生活做出妥協讓步,這樣的矛盾性深刻描繪出女性在解放自我道路上的真實心態。一方面,老三敢于沖破男性中心文化的包圍,掌握自己的話語權。老大的孩子受傷之后,她與老大的丈夫發生了沖突,她堅決反抗老大的丈夫將孩子受傷的責任歸罪于她,面對他的指責以及驅趕,她沒有退縮,只是顫抖著聲音說:“我不走,這不是你一個人的家。”[7]即使老大在此刻沒有站出來幫她說話,她的話語是那么的孤獨,但她身上的堅韌性格以及較為清醒的女性自我意識,仍值得我們探究。另一方面,孤獨的堅守有時會使她甘于生活的平庸,將自我淹沒。她的思想好像變得懶惰了,便用打毛線來消磨平庸的日子,釋放過剩的精力;可打毛線又使她感到苦悶、空虛;為了打破這枯寂的生活,她學習化妝,打扮自己,她甚至產生了要孩子的念頭。老二最后陷入到無目的的生活中,不停調動的工作使她都意識不到自己想要什么。在小說中作者從女性自身出發進行探索,并以此來關注女性自身的命運,即女性的話語權以及主體性被男性所剝奪,以至于她們真實的存在也被男性所遮蔽。
二、姐妹情誼瓦解的原因
當她們三人的姐妹情誼脫離校園這個環境面向社會時,便一步一步走向瓦解。我們可以從外在的壓力以及內在的矛盾兩方面來分析其瓦解的原因。外在的壓力主要是由父權制意識形態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環境所造成的。男權社會里,女性服從于男性,促使男性對她們的妻性和母性形成依賴。一旦她們開始淡化自身的這種角色,追尋自我,男性為了維護他的權力和地位,便會對女性進行壓制。在小說中老二的覺醒以及她們的姐妹情誼,已使男性感受到了一種存在的威脅。然而,“老二的丈夫并不擔心這洪水有朝一日會沖垮堤壩,這并不是因為他對她的理智抱任何幻想,而是因為他深知這一道堤壩不僅由她的理智組成,而是由其他許多人的理智組成,其中也包括他的。當然,這也并不是說他因此就放松了警戒,相反,他密切注意著動向,一有情況他就采取相應的措施。”[7]還有老大的丈夫以孩子受傷這件事為契機,點燃她們姐妹內部的矛盾,從而消解女性的群體性力量,破壞女性的姐妹情誼。除此之外,她們的姐妹情誼本身就存在著矛盾性。她們的姐妹情誼是建筑在假定有“真實的自我”之上的,而現實中女性真正的自我是不存在的。就小說而言,老大的“自我”必須附在一個實體上,才能在這個嘈雜擁擠的世界上占有一席位置。她把“自我”藏匿在一顆容量極大的心里。她的孩子便是她理想的寄托。而老三則更絕情地斷言,“完全徹底的‘自我是不可能實現的,說說開心而已”[8]。老二的瀕臨沉沒,在某種程度上也和她自身的弱點和惰性有關。她對于追尋自我的時而清醒時而徘徊,也讓我們看到她內心的矛盾性。總之,她們“自我”的存在本身就是個問題,也就不可能一直保持這種女性之間的精神戀愛。事實上,在父權制意識形態依然占統治地位的商品社會中,那種相依相守、互為精神支柱的姐妹情誼不過是一種女性成長風景中的烏托邦。而姐妹情誼在女性成長敘事中蘊含了豐富的女性文化和社會文化癥候,則象喻性地表明了在商品消費主義與父權文化合謀的轉型社會,女性試圖通過解構異性戀霸權來拒斥男性價值中心,并試圖通過尋求同性聲援而去建構女性主體性的堅強努力。[9]小說的最后寫道:“船走在峽谷里,兩邊是筆直的峭壁,很高的懸崖上,露出一條藍天。”[10]這一條藍天隱喻女性獨立自我的新天地,它盡管受兩邊壓迫,在夾縫中,遙遠而難以到達,但終歸還是看得到,表現出作者對于女性真正解放這一理想的寄托。
三個普通女人,一段復雜人生,她們為姐妹情誼憂愁傷心,一心想追尋女性真實完整的自我,卻以失敗而告終。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弟兄們》探討的主要是一種純粹精神的關系,如果沒有婚姻、家庭、性愛來做幫助和支援,可否維持。小說以女性獨特的經驗,來刻畫女性之間精神戀愛的可貴及脆弱。一方面表達了在男性中心話語的圍困下女性話語“浮出歷史地表”的意愿,另一方面深刻地揭示了在男性中心文化的圍困下女性話語“浮出歷史地表”的艱難。最終姐妹情誼的破裂和女性自我的沉沒,使我們深刻感受到喪失主體性的女性的悲哀,顯示出女性“較為明顯的依附性人格”[11]的形式過程。同時也要看到小說最后作者所寄托的理想,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進步,我國女性的社會處境及家庭處境都在不斷地改善,她們正在一步步掌握自己的話語權,最終將實現自我的解放。
注釋:
[1]竇芳霞:《懷念:王安憶關于兩性精神戀愛的一種理想——從<神圣祭壇><弟兄們>到<烏托邦詩篇>》,濟寧師范專科學校學報,2005年,第5期。
[2][3][5][7][10]王安憶:《弟兄們》,上海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
[4]陳順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敘事與性別》,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6]任一鳴:《質疑女性主體的一則寓言——解讀王安憶<弟兄們>》,昌吉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
[8]張京媛:《解構神話——評王安憶的<弟兄們>》,當代作家評論,1992年,第2期。
[9]高小弘:《親和與悖離——論20世紀90年代女性成長小說中的姐妹情誼》,河北師范大學學報,2009年,第6期。
[11]張文娟:《五四文學中的女子問題敘事研究——以同期女性思潮和史實為參照》,山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趙軍榮 ?河南開封 ?河南大學文學院 ?47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