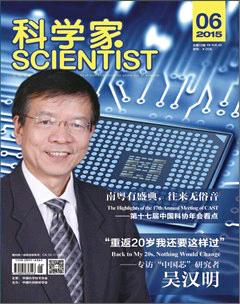科技進步的韁繩與倫理階梯
李俠
這個月最熱門的科技話題當屬中國科學家于2015年4月18日在生物學雜志《蛋白質與細胞》(Protein & Cell)在線發表了人類生殖細胞基因修復技術的文章,據介紹,這是世界上第一次發表編輯人類胚胎基因組的研究。隨后,引發了國內外學界對該項研究的廣泛爭議,歸納起來,主要有三種聲音:其一,支持該項研究,以國內聲音為主;其二,反對聲音,以西方學者為主;其三,提倡中立性的謹慎研究,持此觀點的人國內外都有。到底該如何看待這種現象,恰恰是科技倫理在高科技時代所面臨的主要任務。作為一名哲學工作者,借著這個契機恰好可以做一點哲學普及工作,基于此,本文主要關注如下兩個問題:首先,文化與責任;其次,學術榮譽最大化與倫理危機。
一、文化與責任
筆者注意到本次報道中的一些細節很有趣,該研究的科研人員曾聲明:此次修改人類胚胎的基因,所選用的胚胎均無法發育成嬰兒,不能正常出生,這些胚胎均來自當地醫療機構。這則信息透露出的內涵很豐富:其一,研究者清醒地意識到此次研究未來所要面臨的嚴重倫理問題,因而聲明所選胚胎是“廢品”,而且來自合法機構,以此為研究結果可能出現的倫理爭議預先設置倫理規避措施與退路;其二,此次研究的切入點是修改人類胚胎中可能導致β型地中海貧血的基因,這是本研究能高度獲得社會認同與合法性的共識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本研究能夠獲得預期的轟動、贊譽與爭議早在意料之中,這一切得益于研究者對選題的精準把握以及對中國文化主旨的精確定位;第三,基因編輯技術的安全性與不確定性在國人實用主義的期盼中被有效懸置。然而,研究結果顯示,51.9%的存活胚胎被CRISPR技術成功實現基因修改,但脫靶問題明顯,一些正常基因也被無法預料地修改了。由此,該研究團隊表示:“實驗結果說明,從基因編輯到基因療法技術,中間有明顯的障礙,在達成任何臨床應用之前,仍有很多問題要研究清楚。”至此,一項石破天驚的研究記錄無可更改地陳列在科學競爭的展臺上,然后鄭重宣布,該項研究走向實踐的征途需要慎重。問題是潘多拉的盒子打開了,還能關得上嗎?拋開這些字面含義不談,筆者比較感興趣的是在此事件中反映出的一些深層問題很有趣,如文化與責任問題。借此契機,值得深入挖掘中國科研文化中的規范結構問題。
在文化與責任的大標題下,第一件值得關注的事情是,文化與行為的關系問題。據作者透露,該研究最初是投向著名的Nature(《自然》)和Science(《科學》)雜志,如此熱點、吸引眼球的題目被拒,作者推測可能是出于倫理原因,而且隨后引發西方學者比較普遍的倫理質疑可以佐證這個猜測。作為對比,該研究以最快的評審速度在國內的學術期刊上發表,并且快速贏得國內眾多的贊譽與支持。這里值得插入一句:學術期刊在當下的國內考評機制下日子也不好過,發表如此倫理敏感的文章,自然是要承擔連帶風險的,好在風險總是與回報同行,這可以看作是作者與期刊的一次雙贏的學術營銷戰略。
同一件事在兩種文化境遇下的遭遇簡直是天壤之別,原因何在?這才是熱鬧過后值得思考的事情。總體來說,原因有三:其一,西方長久的基督教文化,以及由此而生發出的理性主義傳統,強調生命的神圣性,因而任何改變生命本質的行為都是與宗教教義相違背的,這種文化背景成為公眾判斷事件意義的起始點,再加上自16世紀以來,西方實行的宗教改革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觀念,規范社會行為的倫理范式也由神圣性轉為世俗性,這種轉變正好伴隨著近代科學興起的400年,不難看出,近代科學的精神氣質中就暗含了清教倫理的精神氣質,關于這一點,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論述《清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已有很好的論述,后來美國科學社會學家默頓更是對清教倫理助推近代科學發展的機制作了深入的闡釋。歸結起來,西方文化在從神圣社會到世俗社會的轉變中,同時存在著兩種主流倫理觀念,即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前者從信念與動機入手規范人們的行為,而后者則是世俗社會中支配個體實踐的主導倫理觀念,強調個人要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那么,由此可以看出,西方文化的變遷反映在主導倫理觀念的變革上,由此造就了一種混合倫理模式,即個體同時擁有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區別只在于哪一個倫理成分所占的權重更大一些而已。
相反,中國傳統文化骨子里就是一種以修齊治平為表征的入世的功利主義與實用主義的混合體,它側重的是計算性的工具理性,所謂的“經世致用”就是這種理念在實踐中的經典表達。一切行為只要能致用并帶來利益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建國后推行的宏大烏托邦意識形態在近30年的實踐后被證明失敗,改革開放后整體轉向徹底的技術決定論,這期間技術的效率標準開始成為評價行為倫理性的唯一標準,所謂不管黑貓白貓能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實用主義哲學更是助長了這種功利主義倫理觀,它是以犧牲人性中的形而上美德為代價的,由此觀念型塑而成的公眾,大多具有技術樂觀主義的認知偏好,甚至有些人在此基礎上走得更遠,成為奇跡主義的忠實擁躉。這種文化孕育功利主義的同時,也荒蕪了信念倫理的存在空間。客觀地說,這30年間我們從來沒有如此地糾結于“目的與手段”的倫理質問:目的美好可以掩蓋手段的殘酷嗎?或者干脆把手段當成行為的目的?在爭議不決之時,我們慣常采用存而不議的鴕鳥戰略,用發展來掩蓋深層次的良心拷問,畢竟解決痛苦的最便捷的方式就是用更痛苦來代替以往的痛苦。因而,在當下的中國科技已經成為替代宗教的一種廣譜性信仰。再加上,基因修復技術所展現的技術前沿性、廣泛的應用前景以及巨大的潛在商業價值,恰恰暗合了從個體、公眾到機構的所有主體的心理偏好與績效期盼,這種利益展現方式與中國文化的內在精神結構形成了高度的契合,由此,不難理解為何同樣一篇文章會在中西兩種文化背景下呈現出迥然有別的命運。再做一個推論,如果該作者在美國從事這方面研究,可能面臨著既發表不了研究成果,也無法獲得聯邦基金資助的局面,還要遭到無數人的質疑,那么誰還會來做這個事呢?
其二,如此熱門的話題相信在全世界感興趣者甚多,但西方具有相對比較完善的法制體系,以及嚴格的執行機制,因而一旦立法,即便有熱衷于此者,也不敢貿然以身試法,否則代價太大(克隆人計劃的夭折與此有關);反之,中國則由于法制不健全,尤其是有關科技倫理的立法嚴重滯后,再加上執行監管的部門的普遍缺席與走過場,以及公眾對于科技進步的片面熱情,導致公眾對科技后果危害性的認知相當陌生,甚至完全不了解(傳統科普的片面性的正向傳播就是典型案例,中國人對于科技負效應的認識大多來自于美國科幻大片),加上有些研究成果之后果的完全展現需要漫長時間,這些隱而不顯的危機在短期利益面前會被短視的公眾迅速忽略掉,導致這類越界研究成為科學共同體內很劃算的一種行為選擇模式。當權利與責任不對等時,超越規范尋求利益最大化就是個體的理性表現。
第三,基因修復技術原本起于西方,為何人家不允許進行此類研究,眼睜睜地放棄即將到手的學術第一的榮譽?畢竟現代意義上的科學是源于西方的產品,他們在近代科學興起的幾百年間對于科技的后果與群體行為選擇具有更清醒與深刻的體認,畢竟那些成功的經驗與失敗的教訓會讓他們在遭遇到如此重大問題上審慎前行,而我們缺少這方面的經驗,我們的觀念里只有效率與利益,而無法真切意識到這些選擇的后果,即便意識到了也可以視而不見,而且無需對后果承擔責任。在這種思維惰性背后,我們就會不可避免地遭遇到進步帶來的尷尬局面:解決的問題遠遠沒有制造出來的問題多。當困難問題出現了,我們再用新的風險來處理舊的風險,至于能否解決無人真正知道,這樣就會出現風險的累積效應,到最后積重難返。筆者多個場合講道:人類社會的發展要遵循相同的規律,沒有任何個人或者國家可以自負地越過那些客觀存在的發展障礙。在發展這條路上沒有捷徑可走,更沒有任何特色可言,規律是不可逾越的。以前我們曾嘲笑西方發達國家的環境污染,相信今天我們遭遇到的環境問題已然能夠證明這個規律,科技的發展同樣如此。
第二件值得關注的問題是:責任與倫理的關系。沒有倫理的約束,責任就是一個虛擬的結構,關于這點需要簡單解釋一下:責任是對行為結果而言的,對于過去的事件,結果已經發生并且無法更改,我們負不起責任;對于當下的行為,結果尚未呈現,我們無需負責;對于未來的事件,由于結果沒有到來,我們無責可負。責任就是把當下的行為與遙遠的結果用獎懲機制聯系起來,如果時間足夠遙遠,責任的約束功能迅速降低。明白責任的這個運行結構,很讓人震驚,如何約束人類的行為,這就需要倫理的永續保證,對于當下的行為我們需要責任倫理,對于過去與未來的事件,我們需要信念倫理的支撐。而功利主義倫理只注重當下的利益考量,過去與未來被制度性懸置,其后果自然不容樂觀。試想原子彈爆炸后,包括愛因斯坦在內的一些科學家感覺自己對此負有責任,這種拷問就來源于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的共同作用;反之,我國的科學家則很少對此有這種責任感與內疚感,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就在于我們的文化中所設定的倫理僅僅是單維的倫理,這種倫理結構在科技領域所蘊含的危機已然是不爭的事實。
基于上述分析,筆者一直好奇這樣的一個問題:假如基因修復中出現了“廢品”該如何處理呢?據報道這項研究中科研人員所利用的CRISPR/Cas9技術本身就存在嚴重的不確定性,由此,可以肯定地說基因修復中出現廢品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一旦這些基因修復失敗而制造出的生命該怎樣對待呢?誰來為他們的遭遇負責?這還僅僅是表層問題,由此引發的深層問題更難以處理,這些經過修復(編輯)的基因是可以遺傳的,由此,一些新的種類開始出現,我們和那些制造出來“超人”或意外“廢品”如何相處?不難想象,科技界中總會出現一些狂人利用這些技術進行拓展研究,而社會中則存在另一些人擁有某些特殊的心理偏好需要(如美貌、智慧、健壯、返老還童等),由此,可以做一個設想:那些被證明是人類的卓越品質甚至邪惡品質都會有潛在的需求者,潛在的供需關系得以確立,那么,人類社會將進入一個“人造超人”泛濫的時代,那么千百年來所形成的社會秩序終將被這些超人完全摧毀,這不是科幻而是潛在的技術未來。筆者無意去批評那位年輕的科學家,因為這項工作,即便不是他,也會有別人去做出來,畢竟這里的誘惑太多。哲學家萊布尼茨早就說過:每種可能性都要求存在,以便成為現實。只要可能性一旦展現在人們的視野中,就再也無人能真正阻止它的到來。我們今天強調科技倫理的規訓作用,無非是想通過一種規范倫理的約束延緩這種危險的推進速度,為人類的安全與秩序留出足夠多的準備與調試時間而已。
二、學術榮譽最大化與倫理危機
筆者一直固執地認為,在知識經濟時代社會的深層風險來自于精英的選擇與行為。換言之,知識的門檻決定了個體參與社會變遷的能力。科技共同體歷來是人群中最具抱負與野心的群體,他們的行為與選擇對未來社會的影響巨大。要想理解科學共同體的行為選擇模式,首先要搞清楚科技共同體的行為驅動機制,毋庸諱言,科技共同體與其他社會群體一樣,有著屬于自己領域的特有偏好,如經濟領域商人偏好追求利潤最大化;政治領域政治家偏好追求權力最大化,同理,科技領域科研人員偏好追求榮譽的最大化。這些偏好都是基于理性的選擇,通過名、權、利在最后達到殊途同歸的效果,即個人通過追求自己領域的主導偏好,實現自我滿足與超越,這些原本無可厚非,但是如果沒有相應的倫理規范約束,那么在各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就會出現違規現象。拋開前兩者不談,僅就科技共同體而言,科技人員之所以追求榮譽最大化,是因為它標志著在科學界獲得承認與贏得收益,而承認是科學界的硬通貨,只有獲得同行承認,才能體驗到源于智慧的優越感,那些前期投入才不會變成沉沒成本。從這個意義上講,科技界面臨著巨大的競爭壓力,要想勝出其實是很難的,在這種氛圍下,越界不失為一條捷徑,尤其是在沒有明確的懲罰機制下,這種選擇是收益最大化的選擇。對于這個案例我們可以盡情猜測與預見到它的潛在結果:該研究讓研究者迅速成為本領域的學界翹楚,然后,各種榮譽稱號與稀缺資助會紛至沓來,從而有助于個人的自我實現與收益最大化,否則,按照常規套路,為了獲得如此聲譽還不知道要艱苦拼搏多少年?
那么如何約束科研人員的倫理行為呢?這要從科研行業的職業特質說起,只有了解了其內在的含義,才能找到合理的約束方式。職業這個詞在西方基督教語境下,它內涵的演變大體經歷了如下三個階段:召喚、使命與謀生的職業,換言之,職業內涵里先天地具有了奉召與使命的意思,這是需要信念倫理來維系的,而隨著近代科學的建制化,職業更多地意指一種謀生手段,此時通過責任倫理來提供約束。但不論怎樣演變,任何職業內涵中都不能少了召喚與使命的含義,否則單純以此謀生是讓人無法忍受的。這也是哲學家阿倫特所謂的積極生活的要義所在。對于科技人員而言,通過彰顯職業的召喚與使命感,恰恰是捍衛個體尊嚴的一種方式。如果職業所針對的對象是人,此時僅有責任倫理是不夠的,還需擁有信念倫理的輔助,畢竟人不是機器。按照哲學家康德的經典表述:人永遠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那就意味著,人和工程、機器是不一樣的,當工程技術人員建造工程或機器時,即便失誤了還可以重來,這個過程可以看做是可逆的,而當研究人員把人類的生殖細胞當做像工程一樣的東西來操作的時候,有關人類的尊嚴與意義的所有價值建構都將消解。按照德國哲學家約納斯的說法:人們不能利用未出生的人做實驗,就是說,使他們成為自己獲得知識的手段。現在生物技術在其控制中卻可以用自由的虛構取代選擇,并因此獲得為任意目標服務的計劃選擇。這些知識在實踐領域一旦擴散就會成為一種無法控制的危險平臺,這應該被看作是此類研究的倫理底線。
人類文明史的進程一再表明:每當人類社會的倫理邊界發生移動的時候都會帶來社會的震蕩,但是,如果這一過程是自生自發秩序的結果,而不是人為設計的結果,那么社會震蕩會以非常小的幅度發生作用,并不會帶來劇烈的社會沖突,原因在于漫長的進化時間把那些潛在沖突的風險分攤了,通常這個適應期一過人類文明就會隨之提高;但是這個過程如果是人為強行推動的,那就必然導致社會準備不足,沖突短期內集中釋放,社會的消化期過短必然導致調試期變長,并帶來長久的社會秩序混亂與倒退局面,反而有可能使社會的文明程度不升反降,文明的實現從來都是有代價的。前些年有些學者提議設立技術研究禁區,立意很好,但缺乏可操作性,從而就淪落為紙上觀念,實際的運行仍是各種危險的研究風起云涌。在一個民主與法制不健全、以及文化存在先天缺陷的國家,權力的任性更是有可能助長這種冒險性研究,因為沒有人會為后果負責,普通公眾對于遙遠未來的習慣性漠視,不可避免地被短期的利益許諾所蒙蔽,最后造成群體尊嚴的喪失而不自知。筆者曾戲言:任由基因編輯技術的發展,輸在起跑線上就有可能真的變成不可逆轉的現實。到時所有人的福祉與公平都將蒙受損失,社會秩序得以維系的公平與正義的產生基礎將會被某些與人有關的科技力量徹底顛覆,我們有多少人對此做好了準備?基于上述考慮,筆者一直在建議:應該給某些科技領域套上韁繩,設置必要的倫理階梯。有些邊界是不能肆意僭越的,在條件不具備的時候,貿然跨越進步的階梯是一場冒險的賭博。行文至此,突然看到最新消息:2015年5月18日,美國國家科學院(NAS)和國家醫學院(NAM)宣布,將發起一項倡議,提議為編輯人類基因組制定指導性規范。
突然想到哲學家阿多諾的一句話:哲學繼續存在是因為實現它的那一刻已經錯過了。在我看來,當下拯救意義與尊嚴的使命對于科技倫理來說正是恰逢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