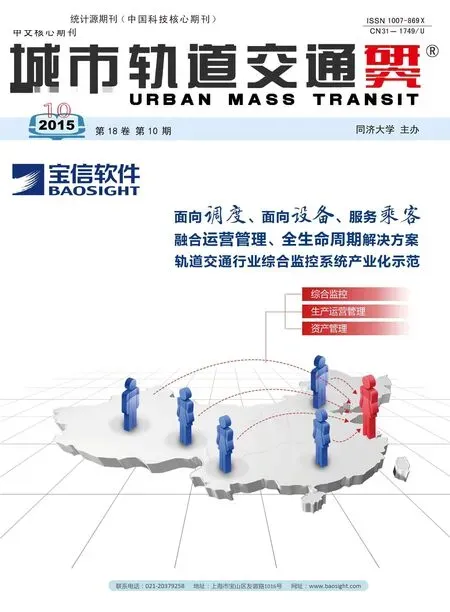大斷面黃土地鐵隧道CRD法施工誘發的地表沉降規律
任建喜 萬永濤 張揚洋 于松波 許世恒 劉 華
(西安科技大學建筑與土木工程學院,710054,西安∥第一作者,教授)
隧道開挖施工引起地表沉降的規律一直是地鐵隧道安全施工中的關鍵技術問題之一[1-3]。施工方法的差異,將導致隧道開挖施工誘發不同程度的地表沉降。文獻[4]運用有限元法分析了淺埋暗挖隧道CRD(交叉中隔壁)工法不同的開挖順序對地表沉降的影響。一旦開挖施工引起的地表沉降超過允許值時,極易引起大面積的地表塌陷,進而引發一系列的工程安全事故,嚴重影響施工進度。因此,為確保施工和周圍建筑物的安全,對地鐵隧道開挖施工引起的地表沉降進行監測與控制是極為必要的[5]。本文以西安地鐵3號線胡家廟—石家街區間工程為例,采用FLAC 數值模擬軟件和現場監測相結合的手段對CRD 法施工引起的地表沉降規律進行研究。
1 工程概況
西安地鐵3號線胡家廟—石家街區間線路沿東二環自南向北行進,下穿金花北路,區間全長1 250 m。本文選擇隧道左線ZDK33 +116—ZDK33 +141區間進行地表沉降規律的研究。該區間隧道采用CRD 法施工,并采用φ42 mm 的超前小導管注漿,對拱頂的土體進行預加固,以改良地層的力學特性;在鋼拱架架立后及時噴射混凝土,盡早使支護結構封閉成環,改善整體結構受力體系。布設范圍在拱頂150°,環向間距300 mm。對于超挖中出現的地層與拱頂間的空隙,及時注漿加固填充,以控制拱頂圍巖及支護結構的變形。具體的隧道支護結構見圖1。由于隧道開挖斷面大,埋深較淺,并穿越f3 地裂縫,因此對開挖施工引起的地表沉降有嚴格的控制。
該區間地鐵隧道穿越的主要地層是人工填土、第四系上更新統新黃土、飽和軟黃土、統古土壤、第四系中更新統老黃土、第四系中更新統粉質粘土。
該區間地下水高程介于 392.24~397.33 m 之間,勘察期間接近平水位期,水位變幅按2 m 考慮,流向主要為由北向西。擬建場地的地下水主要來自大氣降水、側向地下水徑流補給,潛水排泄方式主要為側向徑流排泄。對該區間地鐵隧道施工有直接影響的是地下潛水。為了減少地下水對隧道施工的影響,切實達到“無水作業”,隧道開挖前應對施工區域先進行降水,使得水位降至隧道底板以下3 m 方可進行開挖施工。

圖1 隧道支護結構圖
2 地表沉降規律預測
2.1 建立計算模型
西安地鐵3號線隧道淺埋暗挖CRD 法施工段(ZDK33 +116—ZDK33 +141)開挖斷面為9.00 m×9.035 m,隧道拱頂埋深10.6 m。根據施工經驗及理論計算可知,隧道開挖施工的影響范圍一般是洞徑的3 倍左右。預測沉降槽的影響寬度約為30 m。為減少隧道模型邊界條件對數值計算結果的影響,對左、右邊界水平方向及底邊界豎直方向進行約束,頂部自由。隧道模型的計算范圍為:隧道中軸線左右二側各取30 m,沿隧道開挖方向為25 m,地表面以下取40 m,故模擬區域為60 m×40 m×25 m(長×高 × 寬)。該模型的坐標原點位于隧道的中線處。數值模擬監測中的地表沉降點布置見圖2。
隧道開挖斷面處的網格按0.5 m 為一個單元,其他均按照1 m 為一個單元進行劃分。由于隧道左線地表面處車流量較大,故在模擬計算中對地表施加附加荷載,附加荷載按15 kPa 計算。根據上述條件建立如圖3所示的隧道計算模型。

圖2 地表監測點示意圖

圖3 隧道計算模型
2.2 數值模擬計算
在數值模擬計算中,土層采用摩爾—庫倫模型計算,支護結構應用線彈性模型計算。根據地質勘察報告,可知土層的基本物理力學指標(見表1)。
CRD 法施工計算工況:為了較為真實地模擬CRD 法施工過程,模擬計算中嚴格按照現場施工方案進行開挖,以此來預測CRD 法施工誘發的地表沉降。具體的導洞開挖順序見圖3。由于該區間采用了完善的降水設施,故模擬中不考慮地下水的影響。

表1 土層的物理參數指標
2.3 FLAC 數值模擬軟件計算結果分析
2.3.1 隧道分步導洞開挖造成的地表沉降分析
礦山法施工對地層變形的影響主要集中在豎直方向,現采用FLAC 數值模擬軟件對CRD 法施工不同開挖步序對地表沉降的影響進行研究,僅考慮導洞引起的累計地表沉降量,并選取1—1 斷面進行研究分析。
在隧道施工開挖過程中,由于CRD 法開挖施工的時序性,造成地表沉降的中心會偏向首先開挖的局部斷面,但隨著施工工序的不斷跟上,地表沉降的中心逐漸向中心偏移。每一步開挖工序施工完成后引起的地表累計沉降量如圖4所示。
隧道開挖工序的不同,將導致地表沉降變形的程度也不一樣,所以對CRD 法施工中不同導洞開挖順序造成的地表沉降進行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1)導洞1 的開挖施工引起的地表變形較明顯,最大地表沉降量為4.62 mm,沉降變形的范圍在隧道中心走向左右10 m 范圍內,沉降形成的沉降漏斗較平緩。
(2)導洞2 的開挖施工造成的地層變形相對導洞1 的較大,地表沉降的范圍擴大到隧道中心線左右20 m 范圍內。
(3)導洞3 的開挖施工完成后,隧道開挖斷面中隔墻以上完全形成空洞,這對地層變形的影響極大。所以導洞3 開挖完成后的地表沉降量突然大幅度增加,其中最大沉降量為9.23 mm,且隧道開挖施工形成的地表沉降漏斗相對較陡。這主要是由于中隔墻以上斷面形成空洞后對地層的豎向影響較明顯,而對橫向影響相對較弱。
(4)導洞4 開挖完成后,對地表沉降的影響加速,但比導洞3 的增速要小,最大地表沉降量為11.39 mm。導洞開挖完成后,隧道開挖斷面形成完整的空洞,地表沉降變形的影響范圍在25 m 左右。
對最終沉降變化曲線研究分析知:隧道開挖施工及支護過程中誘發的累計地表沉降最大值為15.76 mm,隧道導洞開挖造成的地表沉降量占最終沉降量的72.34%,由此分析可知,影響地表沉降變形的因素主要來自隧道的開挖施工。地表沉降變形形成的沉降漏斗明顯,影響范圍擴大至隧道中心線左右倆側30 m 左右。地表沉降最大值位于隧道的中心軸線處,且引起的最終地表沉降能夠滿足地表沉降控制標準的要求。
2.3.2 隧道縱向地表沉降變形分析
隧道開挖斷面距地表監測斷面的距離與縱向地表沉降量的變化密切相關,沉降量的大小會隨著隧道開挖施工工序的推進實時動態變化。現選取典型監測點X3、A4、X6 的地表沉降量進行分析研究。以隧道開挖斷面距離典型地表監測點的距離為橫坐標,開挖斷面到達監測點之前的距離為負值,穿過監測點時距離值為正;以地表的最終累計沉降量為縱坐標,由此可得典型地表監測點距離隧道開挖斷面距離與地表沉降量的變化曲線。數值模擬結果見圖5(縱向地表沉降變化圖)。由頭5 可見,在隧道開挖斷面未到達監測點時,地表沉降的幅度較小,即所謂的先行位移;一旦開挖斷面推進到地表沉降監測點時,隧道開挖施工引起的地表沉降大幅度增大,且沉降速率較大。沉降監測點X3、A4、X6 處的累計沉降量分別達到5.29 mm、4.54 mm、5.09 mm,該階段的累計地表沉降量占整個開挖影響階段的20%~40%左右。該階段地表沉降較快的范圍基本處在開挖斷面越過地表監測點一倍左右的洞徑。之后由于隧道開挖施工引起的地表沉降逐漸變弱,即隧道初襯發揮作用,隧道圍巖變形逐步達到穩定。
2.3.3 隧道開挖斷面橫向地表沉降變形分析
根據FLAC 數值模擬結果,針對隧道開挖中圍巖特性及模擬監測點的地表沉降結果,結合1—1 剖面的橫向地表沉降變形結果,綜合預測地鐵隧道CRD 法施工引起的最終橫向地表沉降量。

圖5 縱向地表沉降變化圖
圖6 為橫向地表沉降變化曲線圖。經研究分析可知,CRD 法施工引起地表沉降曲線圖呈現Peck 公式的變化分布趨勢,沉降槽明顯,沉降槽的影響范圍大約在隧道中心軸線左右兩側30 m。結合現場施工開挖進度,可知當隧道開挖斷面初襯封閉成環,支護體系承載能力提高,隧道圍巖變形逐步穩定,即地表沉降變形也趨于穩定。根據橫向地表沉降監測結果,獲得該區間監測斷面處地表沉降變形的最大值為15.76 mm,滿足地表沉降控制標準。

圖6 橫向地表沉降變化曲線圖
3 實測結果與FLAC數值模擬結果對比
3.1 監測方案
地表沉降量的大小能最直接地反映隧道開挖施工支護措施是否得當,為判斷隧道整體穩定性提供準確的信息。本施工段隧道下穿東二環道路,道路周邊建筑物較多,地表的沉降將影響到建筑物的安全及車輛的安全行駛。現選取該區段研究CRD 法施工對地表沉降的影響。
(1)地表沉降監測點布置。根據施工監測要求,在區間ZDK33 +116~ZDK33 +141 進行地表沉降監測點的布置。現場監測地表沉降點布置圖見圖7。所布置的沉降監測點分為縱向地表沉降監測點和橫向地表沉降監測點。使用精密監測儀器Trimble 數字水準儀對地表沉降監測點進行及時測量,每次將所測數據與上次數據進行比較分析,獲取本次測量的地表沉降量,并將監測數據與地鐵隧道未開挖前的高程數據進行比較,由此可知隧道開挖施工引起的地表沉降量累計值。在大量監測數據的基礎上,可得到CRD 法施工引起的地表沉降分布曲線及趨勢圖。
(2)監測點埋設。地表沉降監測點的埋設方法:公路上沉降點埋設,用沖擊鉆在地表鉆孔,然后放入圓頭螺紋鋼筋(長200~300 mm,直徑18~22 mm),四周用錨固劑或水泥漿填實;豎井周邊硬化場地測點布設采取套筒埋設的方式,如圖8所示。
(3)地表沉降控制標準。根據相關規范及施工經驗制定地表沉降控制標準值,一般地表沉降控制標準是30 mm。
3.2 對比分析

圖7 現場監測地表沉降點布置圖

圖8 地表沉降監測點埋設圖
在地鐵隧道施工過程中,由于附近建筑物及地下管線眾多,施工期間的安全至關重要。針對CRD法施工中的地表沉降,設計完善的施工方案及監測方案,并運用FLAC 數值模擬軟件對施工方法及工序的可行性進行模擬分析;同時,運用監測儀器對地表監測點進行實時監測,并將實測數據與模擬數據進行對比研究,進一步分析驗證施工及監測方案的合理性。數據對比分析圖見圖9。
關于隧道開挖施工引起的縱向地表沉降,由圖9 可知,FLAC 數值模擬結果與現場實測數據的變化趨勢基本保持一致,縱向地表沉降受隧道開挖施工的影響范圍大概在2 倍左右的洞徑;現場實測數據相對于數值模擬結果較大,這主要是由于在數值模擬中對地層進行了簡化設置,另外現場施工條件復雜,無法完全模擬現場開挖施工情況。FLAC 模擬的縱向地表沉降最大值為18.23 mm,而實測地表沉降最大值為19.47 mm,二者相差1.24 mm。根據地鐵隧道施工引起的地表沉降控制標準可知,FLAC模擬結果與實測地表沉降量均能滿足地表沉降的控制標準。

圖9 實測數據與模擬數據對比分析圖
關于隧道開挖施工引起的橫向地表沉降,由圖9 可知,FLAC 數值模擬結果與現場實測數據的變化趨勢基本保持一致,隧道開挖施工引起的最大地表沉降在隧道中心線左右處,這與經驗法Peck 的變化曲線保持了較好的一致性。FLAC 模擬的橫向地表沉降量最大值為15.76 mm,而實測地表沉降最大值為17.01 mm,實測數據比數值模擬大8%左右。這主要是由于施工現場條件較為復雜,在數值模擬分析過程中,對附加荷載的作用范圍進行了簡化,未考慮土層中的孔隙水影響等因素。地表沉降實測值及數值模擬結果均滿足地表沉降控制標準。
上述監測數據與FLAC 數值模擬結果的對比分析,進一步說明了在該區間采用CRD 法施工的科學性、合理性和安全性。
4 結論
(1)CRD 法施工引起的縱向地表沉降基本遵循“緩慢變化—急劇變化—緩慢變化—基本穩定”的規律,最大地表沉降值為19.47 mm。橫向地表沉降的變化基本遵循經驗法Peck 公式的變化規律,在隧道中心線上方的地表沉降監測點變形突出,隧道中心線左右兩側的測點沉降變形較小,地表變化總體上呈現漏斗狀,沉降槽較明顯;橫向地表沉降影響范圍由隧道中心線向左右兩側達到3 倍左右的洞徑,最大地表沉降值為17.01 mm。
(2)淺埋大斷面隧道由于距離地表近、開挖跨度大,再加之CRD 法施工工序復雜,使得施工工序對地表沉降的影響很大。通過采用超前小導管注漿、及時架立鋼拱架及初支盡快封閉成環等控制措施,使得CRD 法施工誘發的地表沉降能滿足控制標準。
(3)FLAC 數值模擬預測值與實測值相吻合,均處在地表沉降變形的允許范圍之內。這說明淺埋大斷面隧道采用CRD 法施工能夠較好地控制地表沉降。
[1]李濤,韓雪峰,黃華,等.深圳富水復合地層地鐵隧道暗挖施工引起地表沉降規律的研究[J].現代隧道技術,2014,51(2):76.
[2]宋建,樊赟赟,霍延鵬.復雜條件下淺埋暗挖地鐵車站施工地表沉降規律分析[J].現代隧道技術,2012,49(6):88.
[3]王霆,劉維寧,張成滿,等.地鐵車站淺埋暗挖法施工引起地表沉降規律研究[J].巖石力學與工程學報,2007,26(9):1855.
[4]張銀屏,雷震宇,周順華.淺埋暗挖隧道對地表變形影響的三維數值分析[J].華東交通大學學報,2005,22(5):52.
[5]趙旭偉,談晶,于清浩.砂卵石地層盾構推進對地表沉降影響數值分析[J].城市軌道交通研究,2012(4):33.
[6]谷拴成,王兵強.西安地鐵區間隧道交叉中隔墻(CRD)工法施工變形監測與分析[J].城市軌道交通研究,2014(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