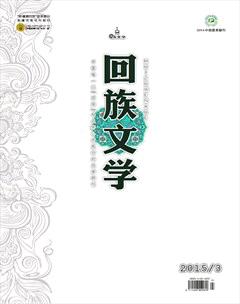功崇惟志 業廣惟勤
劉陽鶴
2014年6月6日,午后的北京正飄著細雨,我只身一人來到三里屯使館區,因置身于某種獨特的情境而無心避雨。我應約邀前往伊朗駐華大使館參加伊朗開國領袖霍梅尼逝世二十五周年紀念活動,這便成了我和我所期待已久之人——阿里·雷公的首次會面。
活動在伊朗駐華大使館會議廳舉行,當誦經師莊重而悠揚地誦讀完《古蘭經》開場經文后,大使館文化參贊向與會者致歡迎辭,介紹應邀到會的中國伊斯蘭教協會領導,以及各位專家、學者、貴賓。介紹到中國著名穆斯林藝術家阿里·雷公時,我看見一位頭戴黑色禮拜帽、留有花白胡須,精神抖擻、中等身材的中年人,從頭排站起身向中外嘉賓和后排的眾人揮手,并點頭示意。
作為一種文化身份,阿里·雷公既是當代中國穆斯林畫家,也是中國與伊朗、土耳其、馬來西亞等國進行文化交流的“文化使者”。因他為中國和伊斯蘭世界的文化交流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所以被吳思科、華黎明、王世杰等中國駐外大使和中東問題特使稱贊為“中國和伊朗及伊斯蘭世界進行文化交流的橋梁和使者”。另外,阿里·雷公還被伊斯蘭世界和國內外藝術權威人士公認為“中國伊斯蘭細密畫派創始人”,并于2011年獲得了由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伊朗中國友好協會授予的“杰出穆斯林藝術家”稱號。
阿里·雷公,原名雷孝書,字恭天,號雍陽漁者,原籍天津武清,1954年10月出生在北京一個普通的回族工人家庭。年少時雖家境貧寒,但作為一名鐵路工人的父親仍對他寄予厚望。或許從一件童年逸事中,我們可以尋到這一厚望的“短暫影像”——1961年的除夕夜,剛上小學的雷公去鄰居家玩耍時,看到了一幅精致的《文姬歸漢圖》,這帶給他的不單單是心靈上的震顫,更使他對繪畫產生了興趣,從而把自己滿腔的熱情化作筆觸來表露對美的追求。
自此以后,雷公開始在課后啃讀《西游記》《水滸傳》,這為他幼小的大腦在成長中增添了無限的藝術想象空間。同時,《岳飛傳》《楊家將》等連環畫不但成了他繪畫的范本,更為他那少年心靈注入了精忠報國、行俠仗義之正氣。一切美的事物,都成了他汲
阿里·雷公
取養分的藝術源泉。然而不幸的是,“美”所遭遇到的歷史境況使其幻滅得太快。1966年,文革的爆發給這個家庭帶來了沉重的苦難,其父因蒙受政治冤屈而遭到不公正的待遇,雷公則因故一度顛沛流離,甚至飽嘗乞討之苦。但是,那段艱難的生活所帶來的巨大磨礪,并沒有泯滅他自幼萌發的藝術熱情,待其輟學數年而境況有所好轉后,雷公以優異的成績讀完了初中,但最終還是因為貧困導致高中肄業。從那以后,雷公先后從事過自行車修理工、電工、琺瑯美工、工會干事、櫥窗美工等職業。
1971年金秋,緣于北京畫院專業畫家馬泉、吳休、周思聰和范曾等國內諸多藝術名家到昌平文化館講學,雷公在這些藝術活動的切身體會中大受啟發,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地踏上了艱辛而漫長的從藝之路。就這樣,他利用所有業余時間拜師學藝,堅持騎車到昌平、海淀區文化館和勞動人民文化宮,學習素描色彩的繪畫技巧。在學藝的過程中他雖歷經坎坷,但恰恰是這樣一種真切的生活經驗,為其日后的藝術創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72年,雷公到北京畫院正式拜師學藝,受到了很多藝術名家的悉心指導,繪畫技藝有了極大的提升,他身上所透露出來的朝氣和執著于繪畫的精神,深深地打動了幾位藝術前輩。1974年,著名畫家范曾先生還為雷公創作了一幅個人肖像畫,以勉勵其在藝術探索中繼續學習。為此,他曾在一次節目訪談中這樣說道:“……我很幸運,那個時候就已經邁上這個門檻了。”無疑這段佳話,可以被視為雷公青年時期所獲得過的最大鼓舞。更為幸運的是,雷公于1978年成為了著名美術史論家、工筆畫大師潘絜茲先生的入室弟子,開始更為專注地研習美術理論和工筆畫藝術,并陸續得到了任率英、黃均、俞致貞、劉力上、文懷沙和劉炳森等藝術前輩的關懷和教誨。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短短幾年的繪畫創作中,雷公的作品便從1976年開始參加國內外的諸多畫展,其中較為重要的作品有《采蓮圖》(1980年)、《荷仙》(1985年)、《三打祝家莊》(1987年)等。有評論者認為,這些早期的佳作成為他躋身畫壇的資本。1981年,雷公加入了中國美術家協會北京分會。即便在這種可以稱得上是“旗開得勝”的情形下,雷公也沒有絲毫松懈,反而趁熱打鐵,他不斷努力廣拓畫路,終于在1988年獲得了中級美術師職稱,又于次年參與創辦了隸屬于中國少年報社的《中國初中生報》,并擔任該報的美術編輯一職。然而就在他事業順風順水之時,不知是受影響于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文化界的風起云涌,還是更多地歸因于個人的身體狀況和藝術追求,雷公在1991年毅然辭去了報社的這一公職,成為了一名澎湃在改革開放大潮中的自由職業畫家。
與此同時,雷公為自己身份的轉變也做出了相應的“正名”,他先后改本名“雷孝書”為雷公、阿里·雷公,這當然可以理解為某種社會身份的命名,實際上其身份所標示的文化意義更值得我們重視。首先,作為來源于中國神話的“雷公”這一人物稱謂,似乎從本質上就為其藝術創作植根于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提供了某種象征性預言。其次,同樣作為人物稱謂的“阿里”則明顯具有伊斯蘭信仰的身份認同,而這一貫穿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和新世紀初之間,近二十年左右的身份表達,也為雷公的創作帶來了迥異于當代畫壇其他畫家的美學特質和藝術魅力。
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文化尋根”熱潮的影響,回族文化在經歷了六七十年代的斷裂期后逐漸恢復了元氣,而這必然離不開當時活躍在文藝界,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詩人、作家,以及各個領域的學者和藝術家。毫無疑問,雷公就是其中一個用繪畫語言為本民族發聲的藝術家。他曾在1991年的一次北京穆斯林畫展上對記者說:“作為
少數民族藝術家,我們有責任為提高本民族的素養竭盡心力,更有必要要求自己準確把握伊斯蘭的精神。”在這次畫展中,雷公以中西合璧的創作技巧,將印象派、純工筆與中國畫的潑墨大寫意手法交融在一起,并融入自己對伊斯蘭精神的文化理解和藝術創造,為現場的觀賞者提供了一幅清新冷峻、神秘雅致的畫作《皎潔光明?一塵不染》。其創作中所表現出來的崇高舉意博得了眾多伊斯蘭國家駐華使節的高度贊揚。當時這幅畫也被視為雷公二十年繪畫生涯的巔峰之作。
值得慶幸的是,他在該畫展中所獲得的巨大成功為其藝術創作打開了更為獨特,且極具視野的新局面。此后雷公又在潛心研究伊斯蘭文化的基礎上,借鑒阿拉伯和波斯的藝術風格,試圖尋找中國繪畫與伊斯蘭繪畫之間相通的人文精神。為了讓傳統煥發出新的生機,他不斷探索并陸續創作出了《溝通》(1993年)、《無盡甘泉》(1994年)、《波斯織女》(1997年)、《銅匠》(1998年)、《樂園》(1999年)、《張騫出使西域》(2002年)、《和平使者——鄭和》(2004年)、《阿舒拉之光》(2010年)等一系列浸染了中國傳統文化色彩的伊斯蘭細密畫,其中以表現伊斯蘭文化中的鏨銅工藝、贊美勞動創造人類文明為主旨的作品《銅匠》,成了雷公所獨創的中國伊斯蘭細密畫派藝術成熟的標志。對此,其同鄉恩師劉炳森先生曾在《功崇惟志??惟勤業廣》一文中給予雷公以中肯的評價:“……為光大中華大民族傳統藝術,為其穆斯林民族藝術而拼搏創新……(他)定位于中國傳統,吸取中東藝術精華,開創了中國伊斯蘭細密畫之先河。”曾被譽為“畫壇伯樂”的著名美術教育家、回族著名畫家丁井文先生生前也曾有過這樣一段題詞:“雷公先生是我國享譽國內外的穆斯林畫家,他開創的中國細密畫為中國藝林的創舉。”凡此種種,關于雷公在藝術創作中所獲成就的諸多肯定,都促成了他被伊斯蘭世界和國內外藝術權威人士公認為中國伊斯蘭細密畫派的創始人。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因雷公不斷致力于探索中國伊斯蘭細密畫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其聲名鵲起于國內外的伊斯蘭文化界。1995年和1999年,他先后兩次應邀遠赴伊朗舉辦個人畫展,其中1995年在德黑蘭所舉辦的活動,是中國—伊朗文化交流史上第一個中國穆斯林畫家的書畫展。當時,這一展覽不但受到了伊朗觀眾的喜愛,而且得到了中國駐伊朗大使館的重視,伊朗電視臺、電臺、報刊等新聞媒體也紛紛報道了此次活動,可以說,在伊朗國內掀起了不小的“中國畫旋風”。此后,雷公又陸續到美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國采風訪問、辦展講學,并在溫州、蘭州、平涼、大同、泰安和北京等地舉辦個人畫展,而且許多作品也曾被國內外紀念館、博物館、駐華大使館、商務機構,以及沙特阿拉伯、西班牙、文萊等國的王室所收藏。
或許在某種意義上,對于二十世紀末漸趨成熟,且創作頗豐的雷公來說,擁有一個穩固而牢靠的藝術陣地,會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鑒于1997年自美國訪問回來后的
阿里·雷公作品《銅匠》
所觀所感,雷公在1998年創建了阿里·雷公藝術工作室,這為他提供了創作環境上的保障,同樣隨著新世紀網絡時代對文化領域的刺激與影響,雷公也因此得益于自己所處的文化環境帶給他的良好業績。
有一次,受某出版社的邀請,雷公創作了六幅名為“世紀騰龍”的組畫,并制作成掛歷被海潮出版社和遼寧美術出版社公開發行,這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其踏上另一條文化主題的探索之路。為此,他在接受采訪時曾談道:“……把中國文化中的龍文化發揮到當代一定的高度……作為一個中國畫家,我覺得這應該是我的使命。”自此雷公便在全新的主題探索,及其與伊斯蘭細密畫的并舉創作中,顯現出了他充沛而精湛的藝術創造力。
2001年,中國少數民族美術促進會和北京市朝陽文化館聯合舉辦了“送龍年·迎新春·雷公畫龍作品展”。在畫展中,很多前輩,如潘絜茲、文懷沙、黃均、丁井文、吳休、劉炳森、雷正民、李力生等數十位書畫家和數位伊朗使館官員前往祝賀,并紛紛題詞賦詩、撰文給予雷公高度的評價,稱其工筆重彩繪龍、寫意水墨暈染、造景抒情的立意和手法,是繼承優良傳統,不同古人的成功藝術實踐。值得一提的是,其恩師潘絜茲先生還在當天早上為他題寫了一四尺《苦學百日成》,并在畫展上高聲誦讀道:“愿阿里·雷公永遠走在中國伊斯蘭畫派的前列,再造殊榮、再創新功。不要老盯過去,只要不務浮華,更下十倍苦功,才有望成為民族的脊梁,中國的希望……”就這樣,雷公帶著其恩師的殷切祝福,于2003年應邀為“天下第一城”創作了兩幅二點二米高、九米長的“唐式”敦煌人物巨型壁畫《萬方來儀圖》,使許多藝術界的知名人士都嘆為觀止,并被文懷沙、黃均、劉力上、劉炳森等工筆畫大師稱為“當今天下第一工筆人物壁畫”。另外,雷公還于2004年應馬來西亞之約,歷時三個月創作了丈余長的巨型細密畫《和平使者——鄭和》,并在吉隆坡參加了“紀念偉大航海家——鄭和七下西洋600年國際展”,這次參展大獲成功而且引起了轟動的效果。2005年4月,雷公遠赴沙特阿拉伯參加了由中國駐沙特大使館舉辦的“中國文化周”活動。2006年2月,他在北京民族文化宮參加了“首都部分(十八位)回族書畫家作品聯展”,同年8月又參加了在西安舉辦的“海峽兩岸民族情大型畫展”等活動。
原北京畫院院長、著名書畫家吳休先生在《勇攀藝術高峰》一文中,也曾談到了雷公的藝術探索與建設之路,他說:“三十多年來,雷公始終堅持了一條正確的藝術道路。他在不懈地打造深厚的藝術功底,吸收廣博的文化素養,積累豐富的生活閱歷和構建崇高的精神境界……他是一個虔誠的穆斯林,對藝術也具有信徒一樣的真誠,他愿以真、善、美的藝術貢獻給全人類。”
說到這里,我不禁想起了曾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費德里科·馬約爾稱贊為“一位屬于全人類的畫家”馬哈茂德·法爾希奇揚,他是目前享譽全球的伊朗細密畫藝術的杰出代表。相對來說,雷公憑借其在中國伊斯蘭細密畫藝術探索中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及獲得的顯著成就,而被理所當然、名副其實地贊譽為“中國的法爾希奇揚”。當然,這可以稱得上是對阿里·雷公在中國伊斯蘭細密畫藝術創作上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
整體來看,以雷公在繪畫藝術中最為搶眼的“中國伊斯蘭細密畫”作為考察點,毋庸置疑在藝術成就上與此有著同樣分量的當屬“雷公畫龍”。事實上,這兩個熠熠生輝的藝術標簽也在很大程度上獲得了當代中國畫壇的贊許和認可。著名研究員西沐在《雷公畫龍》一文中說道:“中華民族具有燦爛的歷史文化,而且是一個奮發圖強、勇于奮斗的民族……隨著國運的興盛,人們越來越重視精神生活。雷公畫龍,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的重要現象,這與其說是一種個性化文化心
理的選擇,不如說是一種時代文化精神的趨勢。”在這種趨勢下,雷公以自身獨到的創作理念,為龍的傳統象征意義賦予了新的時代精神,在富麗堂皇、凜然大氣的藝術形象中刻畫出了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吉祥符號。結合雷公的身世及其成長經歷,西沐還在此文中說道:“在他的筆下,龍是一種正義、一種君臨天下而又不可戰勝的精神力量,這既是他對命運的抗爭,也是其內心深處的無以言表的寄托,更是對正義力量的一種向往。同時,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在當代人們心理上的一種心性的解讀,一種新的體悟所沉積下來的痕跡。”
現在看來,我們有必要就其具體作品再作一次文化意義上的考察,同樣是具有穆斯林身份的丁井文先生對“雷公畫龍”也曾作出過高度的評價和認可:“……他畫的龍別具風范,超越前人,不同今人,尤其是那剛健嚴謹的線條和金紅豐富的墨色塑造出的威嚴崇高的“九五之尊”,充分反映出中華民族沉厚的歷史文化積淀和神圣不可欺的神威。我認為這幅作品是近現代不可多得的畫龍佳作。”當然,他也著重強調了這一界定與其他幾位藝術家的一致性,著名國學大師文懷沙曾為雷公題贈:“龍亢彼無悔,雷公畫筆知。”著名畫家黃均先生也曾在題詩《贊雷公畫龍》中寫道:“雷公畫龍稱第一。”可以說,正是基于這些評價,才使得“雷公畫龍”成為了當代畫壇一個重要的文化品牌。
縱觀雷公近半個世紀以來的繪畫歷程,其藝術創作涉獵廣泛,且成果豐碩,在山水、花鳥、人物等眾多題材上都有很高的造詣。無疑這都歸功于他將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與自身的伊斯蘭信仰相結合,并以此為根基把“和諧觀”視為重要的創作理念,在藝術創作中表現出了兼具古典情懷和時代氣息的美學特征。
本文收筆之時,正值阿里·雷公、雷傳翼父子畫展“經典與傳承”開幕,該展覽似乎是阿里·雷公一個甲子的藝術人生和育兒教子的小結,同時也是其愛子雷傳翼于北大畢業、清華工作四年后,遠赴土耳其留學,邁向更廣闊的知識海洋和藝術世界的新起點。
最后,值得一提的還有,去年秋天,阿里·雷公首次踏上了新疆這塊神奇的土地,并帶著美好的舉意,于今年開始創作一幅頗具民族特色和地域風情的細密畫《火焰山的秋天》,該幅畫是其繪畫生涯中獻給新疆的首次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