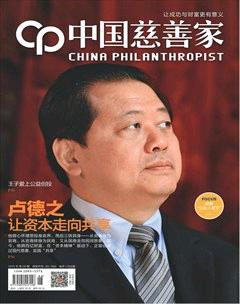徐健:中國自然攝影師市場化的“帶頭大哥”
徐會壇

“可能99.99%的人還是業余愛好,全職的非常少。”
影像生物調查所(IBE)所長徐健告訴《中國慈善家》。比起十三年前他加入“野性中國”時,現在中國自然攝影師的數量多了起來,但是,談及現狀,他不自覺地皺起了粗黑的眉頭。 “野性中國”由因拍攝和保護滇金絲猴和藏羚羊而聞名中外的中國自然攝影師奚志農創辦,是一家致力于用影像傳播和推廣自然保護理念的公益機構。當年,它幾乎聚集了全中國最好的自然攝影師。
在“野性中國”,徐健負責中國自然影像庫的籌建工作。他早年便立志成為一名職業自然攝影師和自然保護工作者,最不缺的就是埋頭苦干的工作熱情。但是慢慢地,公益機構等捐贈、靠資助的狀態讓他感到窘迫的同時,中國自然攝影師生存不易的問題也困擾著他。
“經濟上很難,因為拍野生動物需要花很長的時間,需要高昂的野外費用,用很貴的設備,但是愿意花那么多錢和時間讓自然攝影師去野外拍攝的人很少。”他發現,與英、美等媒體完全市場化的國家相比,在中國,靠賣攝影作品給媒體或圖片庫“很難維持職業攝影師的生存”。
同時,徐健還看到了另外一個問題。他曾在很多公開場合做過一個“辨認野生動物”的小測試,結果發現,公眾了解外國的動物遠遠超過中國本土的動物。
“這是一種很不正常、又挺可悲的現象,因為中國實際上是全世界生物多樣化最豐富的國家之一。”他說,“連我們中國的動物的名字都不知道,我們怎么指望大家去關心它們、保護它們?”
怎樣才能夠彌補中國自然影像的缺失,增加公眾對中國生物多樣性的了解?能不能有一種更加可持續的方式,讓中國的職業自然攝影師生存下去?
徐健開始了中國自然攝影師市場化道路的探索。2008年,他離開“野性中國”,聯合同樣熱衷于自然攝影、畢業于北京大學生物系的郭亮以及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工程師秦大公,一起創立了IBE。
IBE是Imaging Biodiversity Expedition(影像生物多樣性調查)的英文縮寫,是一種把專業自然攝影和生物調查結合起來的生態調查法。“我們希望用這種方法快速記錄一個區域比較完整、豐富的生態系統和生物類群,最后把成果匯集起來,形成一個中國自然影像志,讓更多中國公眾認識中國的生物和自然。”徐健說。
與普通的自然攝影師不同,IBE的每一位自然攝影師都同時具備一定程度的專業生物學背景,例如專攻鳥類的攝影師董磊,他從鳥的外形、叫聲、飛翔的姿態就能判斷鳥的類別,是中國鮮有的拍到三種虹雉(綠尾虹雉、棕尾虹雉和白尾梢虹雉)的攝影師之一。
因此,與普通的自然攝影作品不同,IBE的每一張照片不僅畫面生動鮮活,而且包含了詳細的數據,例如GPS坐標記錄、生物種群數量等。拍攝的同時,IBE的自然攝影師還會進行物種鑒別、動物行為分析等。
多年來,IBE收獲了大量珍貴的野生動植物影像資料。2008 年,他們在貴州務川仡佬族苗族自治縣發現極危物種務川臭蛙的新分布區;2009年,他們在云南梅里雪山記錄了麗紋攀蜥的新亞種;2010 年,他們在云南老君山發現了中國特有物種白點鹛的新棲息地;2011年,他們在西藏雅魯藏布大峽谷首次拍攝到被稱為“昆蟲活化石”的墨脫缺翅蟲,并在河谷里發現了黃腰響蜜 ,此前,專家認為這種鳥只生活在喜馬拉雅山南坡……
IBE的客戶主要包括各地林業部門、自然保護區、環保公益機構、商業生態旅游公司等。截至目前,IBE已經在中國的52個地區開展了65次野外拍攝和調查。就在接受《中國慈善家》專訪的前一天,徐健剛剛從遼寧醫巫閭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回來。應該保護區管理局的邀請,IBE在那里進行了一個生物多樣性調查項目。
和以往一樣,在簽訂了項目合同后,徐健召集了一支覆蓋鳥類、獸類、兩棲爬行動物、昆蟲、植物等門類的七人自然攝影師隊伍,計劃分春夏秋冬四次前往保護區進行拍攝和調查。在項目結束后,他們將向保護區提交調查報告、畫冊、紀錄片等,幫助保護區完整、系統地了解和呈現其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價值。
徐健介紹說,如何深入挖掘、尋找亮點,是這次調查項目的一個挑戰,因為不同于以前去的一些“深山老林”和大保護區,醫巫閭山自然保護區在遼寧中部人口相對密集的區域內,“面積沒有那么大,物種沒有那么多”。
但是,他依然不愿意放棄這次機會,“我們更希望不管這個地方是深山老林也好,是一個城市也好,都能把它與自然的關系用最恰當的影像展現出來。”
IBE已經運營了將近七年,基本摸索出了一條中國自然攝影師的市場化生存路徑,可以維持日常的運營和項目的運作,給每個參與的攝影師發工資,包括差旅費用。
但是,對IBE的發展徐健卻“不是特別滿意”,因為中國全職自然攝影師的規模依然很小,還是以業余為主。他告訴《中國慈善家》,IBE現在有三十多個自然攝影師,除了四個全職的—中國目前全職自然攝影師僅十個左右—其余都有自己的本職工作,分布在全國各地。
2015年5月25日,結束醫巫閭山自然保護區第一期拍攝回京后,IBE全職自然攝影師、傳播及媒體總監左凌仁在朋友圈發了一條消息,“野外結束,作鳥獸狀散。”
徐健和IBE其他幾位全職自然攝影師認為,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應該有更多社會資源的投入,以創造一個更大的空間,讓更多有能力的自然攝影師進入,才有可能獲得真正的、具體的成效。
在拍攝和調查過程中,徐健見證過很多生態被破壞的場景。“生物消失的速度非常快,比我們的想象要快。”他舉了一個例子:2009年春天,他們在梅里雪山曾經拍到1500只美麗的大紫胸鸚鵡從頭頂飛過,壯觀無比。但是,秋天他們再去時,卻找不到這種鸚鵡了,因為它們賴以生存的那片森林被附近的村民砍伐掉,用于蓋房子、當柴火了。
人類到底應該怎樣跟自然相處?徐健一直在思考。他認為,“最終還是價值觀的問題”,所以,他給IBE的定位,除了搶救性地記錄中國的生物多樣性,還希望把兼具美和科學價值的記錄傳達給公眾。
“目前這個事情是我們力所能及的,我們把它做好了,也許可以潛移默化地改變我們的下一代。這也是我們對自己工作的價值的一種期望。總的來說,做一定比不做要好。”
高峰的時候,徐健一年需要在野外拍攝和調查六七個月。他的愛人也是做自然保護工作的,給了他極大的理解和支持。他們的女兒今年還不滿兩歲。
2015年5月,他第一次帶她們去看了他工作的地方。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之上,眺望底下的云杉林和遠處的雪山,女兒高興極了。
“以后只要有機會,我希望多帶女兒去,她會耳濡目染,會受影響,至少會對自然有感覺,不會隔離。”徐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