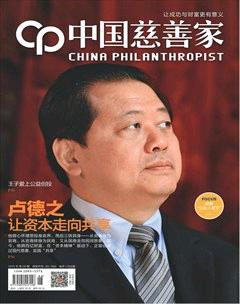明旭:學者,儒商研究專家
儒商的社會變革力量
很多草根出身的企業家,在經濟上有所成就的同時,也開始有了進一步提升管理水平、增強社會影響力、追尋人生意義與社會認同、消費傳統文化產品等多方面的需求
基于儒家理念開展商業活動的行為源遠流長。公元前五世紀,孔子的弟子端木賜(子貢)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不過,當時的人并不稱他為“儒商”。同樣,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司馬遷也列舉了很多“富而好禮”、注重社群共同繁榮、又能合理牟利的商人,這些商人注重長期的可持續利益,區別于某些貪婪攫取短期利益的“貪賈”,而被稱為“廉賈”。其中也沒有提到“儒商”。那么,“儒商”是否只是一種浪漫的歷史回憶呢? 明代儒商的兩個傳統 ——文辭與道德
香港中文大學金耀基、張德勝兩位教授認為,“儒商”在明代后期已經成為一個顯著的社會階層。這個社會階層的出現,與明代商業發展過程中讀書人增加、但科舉名額有限所引發的“棄儒就賈”大潮有關,類似于現在人說的“讀書人經商”。不過,“儒商”何時才成為一個被廣泛接受的詞匯的呢?浙江大學儒商與東亞文明中心周生春教授研究發現,“儒賈”最早相連成詞于明代嘉靖、萬歷年間,而“儒商”則最早出現于清代康熙年間。“儒賈”與“儒商”的涵義基本相同,“賈”與“商”的差異,并不是“坐賈”與“行商”的差異。
“儒賈”一詞,主要出現于士大夫創作的商人墓志銘、傳記中。這些文本往往因為文人“諛墓”的問題,遭到學者的輕視。因此,出現了一類簡單化的解釋——“儒商”只是一種歷史虛構,一種對富裕商人的贊譽之詞。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儒商”是不是對商人的某種贊譽,而在于該詞語的創造者與使用者要傳達一種什么樣的訊息與期待?因為詞語是人們想象、思考世界的工具,其中蘊藏著改變社會的力量。新詞語的出現,表明了新的社會動員力量正在生成。
明代儒商主要受兩個傳統的影響。第一個傳統是文辭的傳統,延續了前七子李夢陽等人的文學復古思潮。第二個傳統是道德的傳統,延續了王陽明的心學思潮。
目前發現的史料中,最早使用“儒賈”一詞的是官至兵部侍郎的汪道昆。萬歷三年(1575年)左右,汪道昆批判了官場士人“輕商重儒”與徽州社會“重商輕儒”兩種風氣,隨后提出了一個尖銳的認同選擇:到底是做像商人一樣的儒家(即“賈儒”),還是做像儒家一樣的商人(“儒賈”)呢?他描述的徽商叫程鎖,年幼時接受詩教,為人很孝順;父親客死淮海后,扶柩歸葬,家道稍損,受母命棄儒就賈,與宗族十人在吳興艱苦創業;中年時,程鎖客居溧水(今南京南)經商,低息放貸給貧民,又于豐年低價囤積糧食,饑年平價賣出,在貧民中很有聲譽。除了商業活動外,他跟隨呂楠、湛若水兩位學者學習儒家性命之學。當倭寇入侵徽州時,又召集里中少年練軍御倭,多次捐款筑城;晚年則“釋賈歸隱”,暇時“召賓客,稱詩書”;其母死時,他以年邁之身嚴守喪禮而病亡。其人格形態明顯是儒家式的。
這類儒商參與了文學復古的運動,期望借此突破理學與市場的雙重桎梏,解放性情,重新獲取一種具有啟蒙意義的新主體身份。很多徽商向他們學習,到了崇禎年間,甚至出現徽商因為大規模進入詩壇而引起士人反感的現象——“禿兵與徽賈,闌入詞人壇。律之鑿石門,奪牛而蹊田。我欲肆毒手,一浣此醒膻。”
無獨有偶,湖北黃安人耿定向(1524-1597年)以《儒賈傳》為篇名,為曾客居黃安縣的徽商程豪、程表兩兄弟合寫了一篇廣為流傳的商人傳記。該文引導人們思考:到底是叫賣智術、釣取奇貨的職業讀書人可以稱得上儒者,還是扶義樂善、仁心為質的商人可稱得上儒者?傳主程豪早年是個小商人,他的整個商業發跡過程,是從湖北舉水河上游的麻城岐亭小市開始的,在那里他從鄉人郭今處,學習陽明心學,因為出色的領導力團結了一批人而經商致富。在當地的一次嚴重饑荒中,他傾力救濟而被縣令賜匾褒獎,得到當地士紳民眾的交口稱贊,也有了“儒賈”的好名聲。他的生意越來越大,做到舉水河下游、靠近長江入口的黃岡團風鎮。隨著他在新的陌生地不斷構建信任社群,他的財力也越來越雄厚。到年老時,他派遣仆人到江蘇真州去販賣食鹽,偶爾也回到徽州整飭宗族,宴飲舊友。程豪總結自己的商業成功的關鍵就在于學習儒學。
經過眾多文士與商人的共同努力,“儒賈”終于成為萬歷以后的一個流行用語,并對商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與此同時,儒家倫理與智慧也隨著商業書、商人書的出版與流行,在實際生活中被擴散開來,成為塑造明清以來商業文化氛圍的重要因素。 當代的“儒商”話語
迭至民國時期,“儒商”仍時不時出現于報刊文章及社會用語中,并沒有消亡。上世紀三十年代,哲學家賀麟就曾提出過儒商、儒工等說法。即便經過五十年代的私有化改造以及后來的文化革命,這個詞仍然留存于少數中國人的觀念中。但是,總體而言,儒商觀念已經成為一條隱線。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儒商”又開始成為中國大陸的一個社會熱詞。不過,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文字研究所將“儒商”當作1992年出現的新詞語選登出來,并認為“儒商”是當代人所造就的新詞匯,就是指“書生經商”。這個“儒商”詞匯,最初既不與儒商傳統的歷史記憶關聯,也不與儒家思想在大陸的復興聯系,反而更像是某種失去歷史記憶、卻又有著心靈積習的集體無意識的呈現。“儒商”一詞,幾乎作為某種贊譽性的世俗詞匯在報刊雜志間流傳。
這個社會熱詞的出現,主要是兩種政治經濟的因素促成的。1)早在1980年代末,國家就通過火炬計劃,鼓勵知識分子經商,將科技轉化為商品;直至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體制內的大批現代知識分子下海經商,媒體人開始稱呼他們為“儒商”。有趣的是,1993年,一部名為《儒商》的電視連續劇熱播,所描述的就是一群下海經商的老、中、青三代科技工作者。2)中國沿海各地大規模吸引香港、臺灣及東南亞的華商家族回國創業,這些保留著明清至民國商業傳統的家族商人,也經常被人稱為“儒商”。1994年暨南大學的潘亞暾教授舉辦的儒商大會,就是與東南亞華商的招商會合二為一的。
2000年以后,部分被媒體熱捧為儒商的企業家陷入法律與道德的危機,儒商一詞的熱度略有降溫,“讀書人經商”意義上的“儒商”逐漸消退。歷史學家、哲學家加入討論中,通過鉤沉史實、闡發意義,一方面幫助人們恢復對于儒商傳統的歷史記憶,一方面又注入新的哲學精神,期以實現儒商傳統的現代轉化。再者,很多草根出身的企業家,在經濟上有所成就的同時,也開始有了進一步提升管理水平、增強社會影響力、追尋人生意義與社會認同、消費傳統文化產品等多方面的需求。社會上也陸續出現了形形色色、以“儒商”命名的協會、俱樂部或研究中心。有的成為企業家接受繼續教育、參與教育事業的平臺,有的成為經營文化產品的企業性機構,有的則單純地成為政治、商業、學術、媒體、文藝、慈善各界人士構建關系網絡的平臺。
近兩年來,在政治上,出現了一個新的動向,就是政府大規模反腐敗、反對官商勾結、并提出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這些舉措正在震蕩中國商人的心靈,追求可持續、和諧、同情、責任等價值的儒商理念也日漸得到更多的認同。在經濟上,產業轉型與新常態的出現,要求更加具有治理彈性與容納空間的社會關系,來化解經濟放緩帶來的各種不可預測的矛盾。因此在慈善、倫理及文化等領域的社會投資,終將成為資本追逐的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