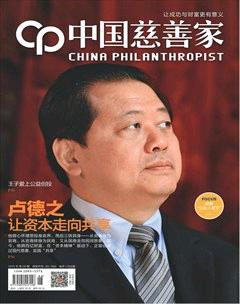王潮歌:我總是感到哀傷
白筱


王潮歌跟現實世界一直有些難以消解的隔閡。她一頭栽進藝術創作中,如癲似狂,而外界從未曾真正認識她的憂郁與哀傷
黃昏時分,一家人鉆進廚房,洗菜、燒飯,填飽肚子。家家人間煙火,王潮歌快哭了。她情緒低落、憂郁,她感到重重的哀傷。
“太無聊了,”她將“太”字拖得老長,長到無以復加。“真的太無聊了,一幫人在廚房里做東西吃,世界怎么這么平庸啊!” “這女的太狠了” 王潮歌拿過一本雜志翻了翻,雜志上有自己一張整版照片,拍攝于2014年9月。“誒呀!”她感嘆,“這女的太狠了。”好像照片里的是別人。
她當時身在五臺山風鈴宮,正操持《又見·五臺山》情景體驗劇。照片上,她坐在劇場觀眾席,側對鏡頭,隨意地穿著條粗布工褲,黑皮靴,絨衣袖口被攢上肘關節處,像剛剛進行過舞美裝修。
“現在很少有女人是這個樣子的,都在那賣萌呢。嗯,這樣的。”她對《中國慈善家》記者賣了個萌,“誰會把女人弄成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是王潮歌的常態。每一次創作她都有如跌入一個深不見底的坑,要向上爬,姿勢相當難看,有血有淚。她一次次在舞臺上為演員做示范,聲情并茂,張牙舞爪,跪倒,爬起,再跪倒,神魔附體一般,如癲似狂。
她與張藝謀和著名舞美設計師樊躍曾多次合作,被稱為“鐵三角”,開創了國內實景劇先河,并參與導演奧運會開幕式。她將原創歌劇《秦始皇》搬去紐約大都會歌劇院,那是大都會建院150多年首次邀請華人執導的劇目。從《印象·劉三姐》至今,她參與創作的“印象”系列實景劇和獨立創作的“又見”系列室內情景體驗劇已達九部,每天在全國各地上演。
她把“小命”和大部分時間都搭在了藝術創作上,每一部劇,她都要創新。
創作《印象·劉三姐》時,她癡人說夢般地要用燈光把十二座山打亮。大家的意見是,“這不瞎耽誤錢么!”她卻辦到了。無數個燈將山圍起,夜來,燈亮,山成了舞美元素。一百多個姑娘,走成一串,一下亮了,一下又滅了,如夢似幻。“我是在她們身上做了亮泡處理,后來把這招用在了奧運會開幕式上。這是我們的發明。”
技術之外,《印象·劉三姐》一劇,“最大的突破,是我自己包括樊躍在觀念上的突破。我們試圖讓觀眾的觀念也改一改,別用老一套再去看那樣的戲。”
她不肯破壞當地自然風貌,使得劇場一年被水淹沒四次。山洪來了,把燈搬到高處,觀眾席都在水下,水退了,“所有人上去扒泥巴”。創作《印象·西湖》時,劇場是隱形的,觀眾席都可拆卸,白天看不到。太陽落山,燈光乍現。“每一個燈都由一艘小船載出來,為了防止污染,船不能用油,要用電。“關于環保,我們都是系統設計過的,在這方面沒有任何紕瑕,甚至我覺得我是環保標兵。”
《又見·平遙》中,觀眾參與演出,成了劇情的一部分,不僅如此,80%的演職人員是當地人。她的這些劇目常年演出,成為眾多當地人養家糊口的飯碗。“我養的孩子多了。”王潮歌說。
2008年汶川地震后,她請來一群災區兒童參與演出,將其他演員召集起來,“不許問你是哪來的?你爸呢?你媽呢?大家完全一樣。”
這些未經任何訓練的演職人員“不能唱,不會跳,都得一點點來。”王潮歌強行幫他們將自己“打碎”,然后讓他們成就自己。“給他們什么呢?你可以給人一份工作,很難附帶給人一份生活的信心和尊嚴。”
起初去一些地方演出,有觀眾“光著大膀子就來了”。如今這種現象逐漸消失,“這是藝術的力量,”王潮歌覺得,“挺積德的”。
《又見·平遙》是王潮歌首次獨立于“鐵三角”創作的大型室內情景體驗劇,講述的是一個關于血脈傳承生生不息的故事。“底沒了,全部要重新建立。其他的劇,可以好點、壞點,但這一部是‘有和‘沒有,要么成,要么零。”創作過程中,王潮歌一次又一次被壓力推向絕望,以至于精神崩潰,免疫力喪失。“一陣風來,你就感冒。”兩個月內,她四次重病,“最多只休一天。”
她曾為了給樊躍幫忙,剖腹產生完女兒12天便爬上舞臺。頭上包個毛巾,躺在床上吃點補品,這樣的日子她忍不了。
她受不了那些婆婆媽媽的事,人間煙火會讓她感到不快,甚至是哀傷。 “您能想點別的事兒么?”
王潮歌跟現實世界一直有些難以消解的隔閡。她一頭栽進藝術創作中,如癲似狂地追求著,而外界從不曾真正地認識過她。
工作中,她跋扈、飛揚;面對大眾,她智慧、灑脫。媒體將其塑造成事業型的“女強人”,但她卻一直對這三個字感到強烈不適。
她熱愛事業,是因為她熱愛這事業的內容,以及與那些內容相處的過程。身處其中,她的靈魂可以終日游走于“一念天堂、一念地獄”之間。她的目的單純直接,想離平庸遠一點,再遠一點,盡可能地更遠一點。寧可談天上的星星月亮,不愿聊家長里短。
“我很少跟婦女們在一塊,你家孩子怎么著,我家老公怎么著。我不是清高不是不愛跟你聊,我會覺得,你怎么又跟我說物質世界?你怎么又跟我說人間的事?你怎么又跟我說活著這點事?”
“活著這事兒不大么?”《中國慈善家》記者問她。“不大,一點都不大。”她不假思索,答得輕描淡寫。“吃飽了睡,睡飽了操,操完了再吃,吃完了再睡,上面一嘴,下面一嘴,照料好了,完了!一輩子就這么完了。牲口、畜生都這么活著。精神呢?不該被照料么?”
她覺得人們只朝著那些低級欲望奔命不叫活著,只能算是“沒死”。她有精神潔癖,不愿這樣茍且。
“您能想點別的事兒么?您吃飽了,甚至還沒吃太飽的時候,您看到了《少年維特的煩惱》,您想象另外一個遙遠國度,一個少年,偷偷喜歡一個姑娘。您能否進入那種情境?”她費解,活出人應該活的精神怎么就那么難?
王潮歌是北京人,生長在教育大院,父母都是大學生,高級知識分子,收入不錯。在她兒時,父母每人每月五十幾塊錢的工資,可以滿足她和姐姐吃糖果、點心、餅干,吃穿無虞,生活算得上優渥。
這優渥不只是物質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王潮歌的父親做過雜志和報紙的總編,母親在《縱橫》雜志做了十年總編,后又到文史出版社做了社長。家里除了父母的恩愛,剩下的全是墨香。在這樣的家庭長大的王潮歌,或許有些精神上的優越感,她稱之為“清高”。
“在我們家,不會討論用什么方法掙點錢這種問題。”王潮歌說。
在象牙塔里長大,還沒出校門便因導演作品出色而小有名氣,藝術成就豐厚,早早收獲愛情且甜蜜至今,一雙女兒被她視為自己“最出色的作品”—王潮歌或許沒有太多機會體驗人間疾苦。也因此,她說她對物質沒有那么高的欲望。 “當我老了”
王潮歌是北京觀印象藝術發展有限公司聯合創始人兼CEO。她說,成立這個公司的目的并非賺錢。“它的目的就一個,就是大家看到的,每年拍一部戲,現在給中國提供了九部都非常優秀的作品。”
《印象·國樂》是2013國家藝術院團演出季的演出劇目之一,作為導演,王潮歌接受中央民族樂團的邀約,編寫并執導該劇,但她要求象征性地只拿1元稿酬。民族樂團的人慌了,問她是何用意,是哪里照顧不周,還是想推掉這活兒。
“這是個商品社會,突然你只拿1塊錢,人家馬上就覺得,不對,你肯定有背后的內容。其實特別簡單,我是想做一次敬禮,向中國傳統文化敬禮。”王潮歌說。
藝術與商業結合,她覺得“百分之百應該”,但她補充,每個人行走在商業社會都應該有一個底線,或者說“有點理想”。
她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人們用金錢衡量一切,她憤怒,因為她看到愛情都被貼上了價簽。她無法出離這種情緒,因而愈發哀傷。
“幸虧我老了。”她僥幸自己的青春時代已經結束。她無法設想將自己的青春活成如今天年輕人一般的模樣:為心愛的人過生日首先想到買件新衣服,結婚一定要有那塊石頭,為了奮斗一個車轱轆拋棄自我遠離家人,為了一個加薪500塊的職位與同事打得頭破血流……她慶幸自己不用每天想方設法向自己的另一半證明,“操!我還有能力!”
“現在的年輕人天天生活在恐懼之中,不知道明天怎么樣。永遠有比你有錢的,永遠有比你年輕漂亮的。你還有其他追求么?”王潮歌說,“我真的替現在的年輕人感到哀傷。”
王潮歌年輕的時候,青春是用來享受和揮霍的。她深深知道,青春貴重,“此一去,永不復返”。
王潮歌對人生有很深的領悟,活得干脆爽利。她那過人的悟性大多體現在她的藝術創作中,其中有天賦異稟,也離不開她的日常積累。
她一直保持著大量閱讀的習慣,只要有字的紙,哪怕一個紙片,她也要看看。有時候出差忘了帶書,晚上翻來覆去睡不著,拿酒店“入住須知”過癮。她書架上的書雜而廣,甚至可以找到梵文佛經。
王潮歌13歲時在《人民文學》發表了一首名為《海,月亮和我》的小詩,大意是,少女在海邊見到明月,心神向往,想到月亮中去,但又畏懼海水太深,她向海懇求,能否用潮汐和浪花將月亮推給自己。
她原本想報考中央戲劇學院新聞系,但新聞系隔年招生,她選擇了導演系。觀印象公司出品的九部大劇都是她執筆。她為《印象·西湖》寫了主題曲—雨還在下,落滿一湖煙/斷橋絹傘,黑白了思念/誰在船上,寫我的從前/一筆誓言,滿紙離散。
王潮歌的細膩與憂傷更多地藏在她零星的文字中,被她工作中的堅硬與大氣所掩蓋。她曾在微博里寫,“以一片海的激情,波瀾一葉舟般的人生。”海與一葉扁舟的意向,是澎湃磅礴,也是深沉憂郁。
“哎呦真是,你太準了!我憂郁得不行。”被猜透心思,王潮歌臉上難掩一抹嬌羞,“我現在也想當作家,我現在也想寫詩,我甚至想,當我老了,干不動了,我回去是不是還能當一個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