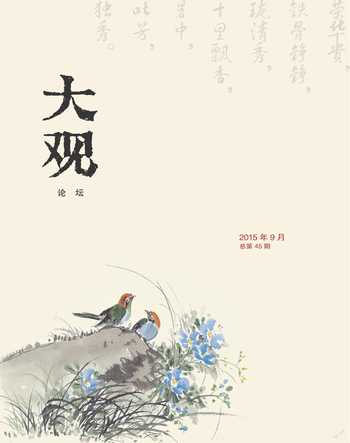論老子“大音希聲”的音樂美學涵義
摘要:老子對審美和藝術采取了一種完全否定和排斥的態度,但并不是一般地反對美和藝術之類,而是厭惡那種過分的、奢侈的、令人混亂的、令人迷狂的縱欲式審美享樂,反對把聲色之娛作為純粹的感官享受的工具。“大音希聲”,無為的自然的音樂為道的音樂,符合道的特征,是一切人為音樂之本,無所不在,無所不容。它是最美的,又是無聲的,是音樂的最高境界。
關鍵詞:老子;大音希聲;音樂美學涵義
我國的先秦時期是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的過度時期,著一時期,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都發生著質的變化。人們已經逐步的舊思想解放出來。在戰國時期就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現象,其中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對后世的思想音響是最為深遠,音樂美學亦是如此。
一、提出及釋義
“大音希聲,大象無形”被認為是老子最重要的美學思想之一。老子的原話是這樣的:“大白若辱,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老子》第四十一章)
(一)對“大”的理解
這段話在文辭上一般是好懂的。正確理解“大”的本義最為關鍵。王振復先生認為,此處的“大”決非“大小”的“大”,而是指原樸、原始之意,可作本原意義理解。(王振復《中國文化的文脈歷程》)此說有深刻的見地,可信。就是說,上面一段話中的“大白”“大方”“大器”“大音”與“大象”,乃“原白”“原方”“原器”“原音”與“原象”之謂。根本而原樸的白,好像是黑的一樣,因為既是原樸之道,則無所謂白還是黑。同理,原樸之道無所謂方圓。原樸之器,因為是根本意義上的“器”,當然總是有待于完成(晚成)的器。原樸之“聲”,當然是無聲的。有聲之音,還能使原樸之“音”嗎?原樸之象,同樣是一種“無形”狀態。總之,“道”是“隱”的存在,無以名之。(名可名,非常名)
所謂“大音”“大象”,就是原樸之音、原樸之象,指自然、生命之初始的混沌狀態,即“惟恍惟惚”“昏昏默默”的原樸狀態,這是原始先民對“道”的一種體悟,是老子對“道”所做的一種勉為其難的描述。可見,這段話本與美學思想無關,因為,老子在這里要說的并非藝術(造型藝術與音樂),而只是他對心中所悟之“道”的一種形象的描述。但是,“音”“象”往往與美、審美相聯系,所以,“大音”“大象”也便可能與美、審美悠關,特別是經過后世的哲學家、文論家發揮和闡釋,“大音希聲,大象無形”便被賦予了深厚的美學思想,對中國古典美學和文學藝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大音希聲”中的“希”
《老子》中“聽之不聞曰希”的解釋。意思是說“希聲”并不表示聲音少或者沒有,而是我們感覺不到,或者可以理解為好的聲音不以形式美為美,而是重寄情,輕發聲。我們能夠聽到的聲音奏出的音樂再美好也難免有缺陷和遺憾,不如音樂本身那么完美,這種音樂思想與歐洲古典主義的音樂思想是完全背離的。
二、“大音希聲”對音樂審美產生的影響
(一)欣賞音樂要有審美的心胸
沒有審美的心胸就無法進行審美,因為“至樂不笑,至音不叫”。(《淮南子說林訓》)優秀的音樂是要讓人慢慢的去品味的,這“品”的過程,就是欣賞的過程、審美的過程。正如有的論者支出:“在中國美學史上,審美心胸理論是一個影響很大的理論”。這種審美心胸的理想雖然是有莊子建立的,但是它的最早年的源頭卻是老子。
(二)啟迪了音樂創作和實踐中的靈動精神
啟迪了音樂創作和實踐中一種不同于“雅樂”也不同于“鄭衛之音”的靈動精神,這種靈動精神的價值指向就是自由與自然。因此,它就有可能是傳統音樂的顛覆者,也可能是新音樂的創造者。如蕭統在《陶淵明傳》中說:“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弦琴一張。每適酒,輒撫弄以寄其意。”琴無弦,彈不出樂曲。但是表達了一種士人的精神境界。音樂從魏晉開始,就是士人體驗玄理,鑄造人格的手段。士人之樂,不是朝廷的宗廟儀式的音樂,也不是宮廷歡宴、民間節慶的艷麗熱鬧音樂,而是表達士人性情和形而上境界的音樂,即所謂“游心太玄”,士人們在“游心”的過程中,把握“道”,進而達到“與天和”的目的。
三、“大音希聲”音樂美學思想對中國音樂的影響
雖然說在中國封建制度社會統治的歷史時期,老子的音樂思想通常被視為是消極的,但實際上他的音樂美學思想卻對中國的音樂審美趨向產生了重要的、基礎性的影響,現階段對世界的音樂美學思潮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如果我們的藝術家評論家不對當前的一些音樂作品進行適當的批評和引導,忽視和偏離社會主導文化審美傾向,其結果就會使我們的精神世界、精神產品,特別是一些年輕人和社會表層民眾的審美傾向出現偏差,這將是我們的音樂審美教育所不愿意看到的,應當引起全社會的總夠重視。現在看來,傳統美學中老子的一些思想,至今仍散發著理想的光輝。因此我們必須要重新審視傳統音樂美學中的一些理性審美,這對于當今處于價值觀轉型期的社會音樂文化發展是很有必要
四、結語
“大音希聲”是一種藝術和美的最高境界。它揭示出,最完美的文藝作品都必須進入道的境界,進入自然樸素而沒有任何人為痕跡的本真境界。懂得“道”的奧秘的人所追求的“美”是那種不把人犧牲于聲色貸利、仁義禮教等外物,不使人為那些外物所奴役的美,即自然真樸的美。只有這才是絕對的,唯一的、真正的美。
【參考文獻】
[1]孫常德.談《老子》中的“柔弱”思想[J].中國道教,1994,(02).
[2]蔣孔陽.先秦音樂美學思想論稿[J].福建師范大學報,1994,(02).
[3]葉明春.《老子》音樂美學觀新探[J].玉溪師范學院學報,1994,(06).
[4]田銀龍.“ 大音希聲”辨析[J].星海音樂學院學報,1998,(01)
作者簡介:馮柱新(1978.2),男,漢族,講師,研究生,廣西藝術學院音樂教育學院,研究方向:音樂鑒賞與評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