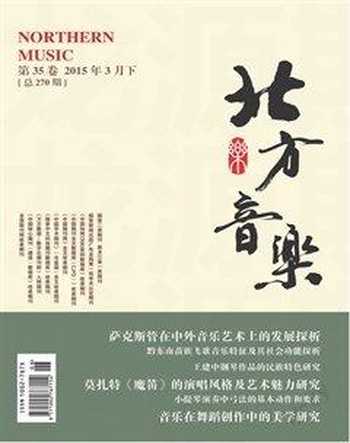博引諸家著述成果 真實再現歷史原貌
【摘要】劉再生教授新著《中國近代音樂史簡述》有三大特點:一、增添新內容,力求全面展示中國近代音樂史全貌;二、評判公允,客觀、辯證地看待歷史現象;三、求史以信,真實再現歷史原貌。同時書中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問題。
【關鍵詞】劉再生;《中國近代音樂史簡述》;中國近代音樂史;治史觀
山東師范大學劉再生教授是中國音樂史學界一位享有盛譽的學者。多年來,他筆耕不輟,潛心學術研究,成果頗多,曾在《音樂研究》《人民音樂》《中國音樂學》等國家級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百余篇,特別是他的代表著作《中國古代音樂史簡述》自原版至修訂版2010年1月第四次印刷以來,已印刷14次,印數達五萬余冊,在中國音樂史學界乃至整個音樂學界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現已年屆七旬的他,仍保持著一種積極向上的研究心態,新著《中國近代音樂史簡述》(以下以“新著”代之)就是繼他《中國古代音樂史簡述》之后的又一部力作,是《中國古代音樂史簡述》的姊妹篇。
“新著”于2009年7月正式由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該書除了在裝幀設計上給人以樸素大方的視覺享受外,還插入了179幅與內容相關的珍貴歷史圖片,以及附贈一張含有135首(部)作品音響資料的MP3教學光盤。圖片和音響的“交相輝映”,增強了歷史的真實感與直觀性,更令讀者讀來有聲有色,愛不釋手。
“新著”保留了《中國古代音樂史簡述》一書在撰寫體例上的特色,即仍以一個個專題的形式梳理中國近代音樂史的發展脈絡。劉教授以“音樂文化不同時代特色為分期依據”,將全書分為清末民初、20年代、30年代、40年代四個歷史時期,共分為四編,編下共設90個專題來“梳理我國近代音樂產生與發展之脈絡。突出音樂家及其作品為史學本體,結合音樂教育、音樂理論、音樂表演、音樂思想等各個方面闡述中國近代音樂文化之來龍去脈。”[1]每個專題都用一個小標題來概括,“或概括歷史事件”,如專題1的標題“封建皇朝的沒落”告訴我們“鴉片戰爭拉開了中國近代歷史的帷幕”;專題2的標題“自西徂東” 提供給我們“西方傳教士踏上中國國土”的信息;“或評價歷史人物”,如專題25的標題“提倡美育、以西衡中”是在評價音樂家柯政和及其發起的北京愛美樂社;“或引述音樂家核心話語”(這種標題居多),如專題7的標題“吾國樂界開幕第一人”就是引用李叔同的話來評價學堂樂歌的先驅者沈心工的”;……這些都“立足于以歷史事實證實歷史本來面貌。”[2]筆者拜讀后對該著作的特點進行了總結,擇其要點略發數端,望專家、學者們指正!
一、增添新內容,力求全面展示中國近代音樂史全貌
“新著”增加了很多曾在中國近代音樂史上有過突出貢獻卻被很多音樂史專著忽略了的學者、教育家、音樂家。正如黃旭東教授所講:“就研究、編寫中國近代音樂文化史來說,……不應當割斷歷史。而是應當根據音樂史實,從蔡元培、蕭友梅到冼星海、聶耳,凡是為我國近代音樂文化事業做出貢獻、做過有益事情的教育家、音樂家(不僅是作曲家,也不僅僅是中國音樂家,還包括當年在華工作的外籍音樂家),不管其是共產黨員,還是國民黨人,……都不應忘記,尤其是做出過重要貢獻而又有代表性的教育家、音樂家的思想理論及其活動都應當給予科學總結,給予應有的恰如其分的歷史地位。”[3]與以往的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專著相比,劉教授這樣的史學思維尤為突出,這些新內容具體可以分為如下幾類:
(一)我國近代早期思想界、教育界、學術界代表人
例如,專題12“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史學大師王國維的音樂論著”,作者單設一個專題來評價在常人看來似乎和音樂沒有多少關系的史學家、思想家——王國維、梁啟超、康有為。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是“我國第一部戲曲史論著……為現代以科學觀念方法研究我國戲曲史的開山之作,在音樂學界同樣具有廣泛影響。”[4]康有為、梁啟超這兩位維新派的領袖,曾是近代音樂教育的大力倡導者。其中,“康有為的《請開學校折》(1898)…‘令鄉皆立小學…教以文史、算術…歌樂中所提‘歌樂,為康有為對音樂教育早期之力薦,有首倡之功。”[5]總之,他們“對推動近代教育的發軔和學堂樂歌的發展都產生了一定影響”[6],對他們進行評價和論述是十分必要的。
(二)近代有一定業績和貢獻而被遺忘或埋沒的音樂家
例如:專題23“搜集傳統曲牌 改良記譜方法——李華萱搜集、整理傳統音樂業績”一節,作者詳細的論述了20年代李華萱在音樂理論與教材編寫出版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貢獻,“尤其在采集、整理傳統音樂方面,李華萱和劉天華一樣做了拓荒性工作,成績斐然……”[7]。
(三)在華做出重要貢獻的外籍音樂家
“就音樂文化領域而言,有相當一批外籍在華音樂家,尤其是在人材的培養上,做出了貢獻,中國人民是不應該把他們遺忘的……”[8]。在 “新著”中,作者也用了一定的篇幅來評價他們,如:專題30“西洋管弦樂隊的一顆東方明珠——梅百器與‘上海工部局管弦樂隊”一節,作者詳述了梅百器對于近代中國管弦樂事業建設和對中國音樂人才培養方面的突出貢獻;專題40評論了中國近代鋼琴教學的奠基人——查哈羅夫;專題53評論了一位以中國音樂為素材、中國文化為題材創作多種西方音樂形式的唯一外籍作曲家——阿甫夏洛穆夫……,這些“外籍音樂家對于中國音樂文化所做出的貢獻,已經成為我國近代音樂史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9]
另外,作者在新著中還增加了不少“歷史細節”式的內容,這些內容使得原本枯燥乏味的歷史變得有滋有味,使人讀來更具親切感,拉近了歷史距離。試舉幾例:
1.“上海國立音樂院”是如何成為“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的?
當代學過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的人,當初在學到“上海國立專科學校”一節時,或許腦海中曾經產生過這樣一個疑問:“在建校初期(1927年11月27日)就以‘國立音樂院冠名的近代第一所獨立的高等音樂學府怎么就很快(1929年8月20日)又變成‘國立音樂專科學校了?”就筆者所知,以往的近現代音樂史書均少(或未)涉及其中的緣由,而在劉教授的“新著”中(專題35),作者回答了這個問題:“1929年暑假期間,由于留校學生須交納雜費、音樂院面臨降格為專科學校、有的教師幕后操縱等原因,引發了一場‘學潮…參加學潮的…十余名學生在按教育部訓令暫行停辦國立音樂院后離開學校……1929年8月20日,國立音樂院改組為國立音樂專科學校。”[10]
2.聶耳是如何溺水身亡的?
聶耳是一位罕見的音樂天才,可惜他英年早逝,一生只活了23歲。關于他的死,以往的近現代音樂史專著只寫“溺水身亡”,但對于他具體在日本身亡的經過,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猜想,劉教授在“新著”中則給出了答案:“1935年7月17日,下午聶耳與朝鮮朋友李相南、房東濱田實泓的姐姐丸山小姐及九歲的外甥厚,他們共四人一起到鵠沼海濱去游泳。那天,風浪很大……聶耳在水深齊胸的地方獨自游。一個多小時后,另三個人都上了岸,卻不見聶耳……他們連忙通知監視聽。房東濱田實泓得到消息,趕到海岸,那已是傍晚六時左右。第二天……在游泳地點西南約30米處的海底,打撈起了聶耳的遺體。……看到聶耳口里流著少些血,頭上也出了少許血,經醫生檢驗為溺水窒息而死。藤澤町町長簽發了死亡認許書。”[11]……類似的問題,有翔實的史料依據,令人信服。
二、評判公允,客觀、辯證地看待歷史現象
正如劉教授“新著”后記所言:“一部中國近代音樂史……其中或多或少涉及與主流意識形態之分歧。究竟按照歷史本來面目反映歷史真實,還是屈從與權利話語而惟命是從……歷史研究的目的,能否保持科學獨立品格,還是成為依附于某種政治意志的附屬品,涉及寫作宗旨的功利性與客觀性問題……是著者在寫作過程中常常思考的問題,也是希望能夠達到的一種境域。”[14]以下試舉幾例:
(一)科學看待西方傳教士來華傳教之正負面影響
正如作者書中所言:“我們既不應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由于政治與意識形態原因,將他們統統斥值之為‘披著宗教外衣進行文化侵略的帝國主義分子,也不排除其中少數傳教士懷著‘奴化中國人目的或者抱著‘擴張主義心態從事宗教活動”。[15]傳教士狄考文夫婦來華,使中國產生了近代第一所教會大學——登州文會館,近代第一部具影響力的介紹西方基本樂理的著作—《樂法啟蒙》……。
(二)實事求是評價王洛賓
1994年4月——1995年6月,就王洛賓民歌創作的“著作權”問題,音樂界引起了一場論辯。劉再生教授也寫文章[16]發表了自己的觀點,他指出:“在批評‘王洛賓熱現象的某種不正常狀況時避免抹煞王洛賓在采集、改編和傳播西北地區民歌中曾經做出的歷史貢獻,真正按照實事求是的準則來評價一個人的是非功過。”[17]王洛賓在搜集、整理、改編、創作“西部歌曲”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因此在作者“新著”中,專設一節(專題56)“在那遙遠的地方——王洛賓搜集、改編‘西部歌曲”來紀念那位為傳統音樂做出貢獻的人,作者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客觀地評價了王洛賓先生的功與過。
(三)公正評判陳洪
陳洪先生是20世紀中國高等教育開基創業者之一,也是三四十年代所謂“學院派”音樂思想的代表者之一,尤其是他“對于‘國樂概念的界定,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部分學院群音樂家的主張……他的‘新國樂,成為現代中國音樂創作的重要形式之一。”[18]歷史上,他卻因自己曾經發表的《戰時音樂》一文,長期蒙受過不白之冤。[19]劉教授在“新著”中,獨設一節(專題66),公正評判這一現象。指出:“在一些音樂史著作中,陳洪這篇文章長期被歪曲為‘音樂與抗戰無關的錯誤觀點加以評判……學術論辯如果被不正常地演化為宗派對立情緒乃至政治性質批判,使學術問題引入政治化、階級斗爭化‘誤區,在中國音樂文化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實際上已經顯露出一種不良后果。”[20],從中足以看出作者直言不諱,探求真理的學術品格。
總之,作者客觀、辯證地看待歷史現象,對于重新解讀中國近代音樂史有著特殊意義。
三、求史以信,真實再現歷史原貌
“一部歷史著作,要能夠成為‘信史,首先必須具有‘史料和‘史實的可信性。”[21]作者也云:“史料是構建歷史科學的重要基礎科學。去偽存真、去粗存精之‘史實更是史料之精華部分。”[22] “新著”寫作過程中,作者本著“信史”的原則,或直接取材于國內外學者(當然也包括作者本人)的最新研究成果,或攜“舊史料”于仍在世的近代音樂家或其后人、友人進行核對、訂正……總之,盡可能使論述真實可信,力求有根有據、原原本本再現歷史原貌。
(一)“新史料”的發掘,真正改寫了音樂史
1.中國近代最早的學堂樂歌——山東登州《文會館志》中的“唱歌選抄”
以往我們都認為,學堂樂歌是產生于20世紀初期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采用日本或歐美曲調填寫歌詞而形成的一種歌唱形式。然而,山東登州《文會館志》中的“唱歌選抄”史料的發現[23],使我們對中國近代學堂樂歌產生與發展的歷史有了重新梳理的必要。因此作者在孫繼南先生“重要發現”的基礎上,又發表專文《我國近代早期的“學堂”與“樂歌”——登州<文會館志>和“文會館唱歌選抄”之史料初探》[24],得出:“西方傳教士在中國開辦的教會學堂是我國早期‘學堂樂歌的策源地;……‘文會館唱歌選抄中的10首歌曲則是我國目前所見最早的一批‘樂歌”[25]之新的歷史結論。為了真實再現歷史之本來面目,作者將此文重新編輯加工后,積極納入“新著”(即專題3“我決心將生命獻給中國——傳教士狄考文夫婦對中國近代音樂教育的貢獻”和專題4“中國近代早期的‘學堂樂歌——山東登州《文會館志》中的‘唱歌選抄”)之中,改寫了學堂樂歌的歷史,填補了以往近現代音樂史書的空白。
2.我國最早的救亡歌曲——“五三慘案”后國立音專師生譜寫的8首歌曲
在專題34“勿忘國恥 警鐘長鳴——抗日救亡初期的歌曲創作”一節,作者引用《革命與國恥》特刊“編者志”[26]中“我們剛要編成本院院刊付印發行的時候,革命的氣勢發展甚速,到了濟南忽發生日兵武力戕害我軍民的一大波折,時為‘五三……我們全院同人,義憤幽憂,只有盡其在我,發表幾首歌曲,增印特刊……”一段史料綜合其他史料,得出《革命與國恥》特刊中所載的8首歌曲創作完成時間在1928年5月30日之前,“這是目前所知我國第一批救亡歌曲作品,說明音樂界最早譜寫救亡歌曲的是國立音樂院代院長蕭友梅率領下的一批愛國師生。”[27] “8首歌曲”使得我們對早期的救亡歌曲有了重新審視的必要。作者在文末進一步指出:“歷史評價如果忽略了這樣的事實,將有悖于歷史的客觀性與公正性”[28],足以看出作者公允待史的治學態度。
(二)有根有據地對一些史料進行訂正與質疑
1.對音樂家生卒年的訂正
書中每一位音樂家,只要從相關的史料中能找出根據,作者都盡可能的將其生卒年詳細到年月日,并對一些“以訛傳訛”的錯誤記錄予以訂正。例如:專題23填李華萱的出生日期時,作者“經由山東藝術學院人事處檔案資料中查閱,李華萱于1958年‘干部登記表中親筆填寫出生日期為1895年11月24日”[29];專題28,作者對鄭覲文(1872-1935.2.24)的去逝日期進行了訂正,作者認為:“以往有關傳記寫1935年1月20日乃是陰歷,按陽歷應為1935年2月24日。”[30];……這些“看似簡單,卻不僅需要查閱許多參考資料,進行辨析考證,還要盡可能與這些音樂家的后人或友人取得聯系,力求準確,體現對音樂家生命的尊重。”[31]
2.對某些音樂常識重新進行訂正
(1)關于“常州第五中學”校名的訂正
“常州第五中學”培養出不少名人,近代著名音樂家像劉天華、儲師竹、劉北茂等均就讀于該校。作者認為:“近代史料中俗稱‘常州第五中學,或簡稱‘常州五中,均非正式校名。其前身為‘常州府中學堂,始建于1907年11月15日,創建人為屠寬。1913年7月改名為‘江蘇省立第五中學,任童斐為校長。……1929年9月改稱‘江蘇省立常州中學。現名‘江蘇省常州高級中學,與目前‘常州市第五中學非同一學校。”[32]
(2)關于“李叔同在日本留學學校及歸國時間”的訂正
以往對于李叔同在日本留學學校及歸國時間的說法多有訛誤。“如學校名稱有‘上野美術專科學校、‘上野高等美術學校、‘東京美術學院等18種異說;歸國時間多寫為‘1910年畢業回國。”[33]劉教授在“新著”中引用劉曉路《李叔同在東京美術學校——兼談李叔同研究中的幾個誤區》[34]的研究成果,積極更正了以往的誤說,得出:“正確校名應為‘東京美術學校;畢業時間應為1911年3月29日。”[35]
四、值得商榷之處
世無十全十美之物,何況一部剛剛出版的新著。筆者試舉幾例,在這里提出一些個人看法,與專家們商榷:
(一)一些“重要信息”的遺漏
例如在書中第130頁,注釋二第8行“……1924年5月學校升格為國立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學制年。”具體學制是多少年(后經筆者查閱資料,具體學制為五年)?是作者遺漏了,還是編輯的問題?再如書中第226頁第5行“…剛到國立音專時,黃自、應尚能、韋瀚章三人住在一起。由于都是單身漢,一起開伙食,韋瀚章燒菜,應尚能煮飯,黃自說他不會燒菜、煮飯,不好意思吃現成的,由他負責洗碗。
(二)出現了相互矛盾的內容
例如在專題5“洋洋之聲觸耳皆是——近代西式軍樂隊的傳入”一節,作者引用著名音樂家韓國鐄先生的觀點指出赫德樂隊“……是中國近代第一個由國人組成的管弦樂團……”[39];而在書中第44頁第12行,卻說“‘上海貧兒院管弦樂隊是我國近代第一支由國人組成的西式管弦樂隊”,這兩種觀點明顯是相互矛盾的,赫德樂隊肇始與1885年,即使到該樂隊重組,也是1902年,而我們從“‘上海貧兒院管弦樂隊…比1923年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創建樂隊要早十四年……”[40]可以推測出“上海貧兒院管弦樂隊”成立于1909年;因此,“‘上海貧兒院管弦樂隊是我國近代第一支由國人組成的西式管弦樂隊”的說法是不妥的,而應是“我國近代最早一支全部由少年兒童組成之樂隊。”[41]
(三)少數民族音樂史的遺漏
一部中國近代音樂史,是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所有愛國音樂家共同創造的歷史,它有漢族的,也應該有其他少數民族的。正如杜亞雄先生所言:“……中國史領域中,注意力集中于漢族音樂史的研究,對少數民族音樂史關注不夠,其結果是漢族音樂史取代了中國音樂史。”[42]少數民族是中華民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少數民族同胞在中國音樂史上做出過杰出的貢獻,可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為漢族音樂的發展做出的貢獻,二是為其本民族音樂發展做出的貢獻”[43]。一部中國近代音樂史,如果缺了少數民族這一塊是不完整的,我們需要至少用一個專題對他們進行一個輪廓性的描述,我想這是十分必要的。
當然,以上只是本人的一些愚昧的想法和建議,不足之處還請廣大專家、學者指正!
參考文獻
[1][2][4][5][6][7][9][10][11][12][13][14][15][18][20][21][22][27][28][29][30][32][33][37][39][40][41]劉再生.中國近代音樂史簡述[M].人民音樂出版社,2009(7).
[3][8]黃旭東.應還近代音樂史以本來面目 要給前輩音樂家以科學評價——評汪毓和先生<中國近現代音樂史>[J].天津音樂學院學報,1998(3).
[16][17]劉再生.批評者,批也,評也——對“王洛賓熱”現象的思考[J].人民音樂,1994(10).
[19]戴鵬海.還歷史以本來面目——20世紀中國音樂史上的“個案”系列之一:陳洪和他的<戰時音樂>[J].音樂藝術,2002(3).
[23]孫繼南.我國近代早期“樂歌”的重要發現——山東登州<文會館志>“文會館唱歌選抄”的發現經過[J].音樂研究,2006(2).
[24]音樂研究,2006(9).
[26]國樂改進社編[M].音樂雜志,1928(4).
[34]劉曉路.李叔同在東京美術學校——兼談李叔同研究中的幾個誤區[J].杭州師范學院學報,1998(1).
[36]孫海.蕭友梅留德史料新探[J].音樂研究,2007(1).
[38]汪毓和.中國近現代音樂史(近代部分)[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6).
[42][43]杜亞雄.少數民族音樂史是中國音樂史的重要組成部分[J].中國音樂,2005(2).
作者簡介:董鄭峰(1984—),男,山西陽城人,碩士,講師,現供職于長治學院音樂舞蹈系,主要從事中國傳統音樂理論、中國音樂史及音樂作品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