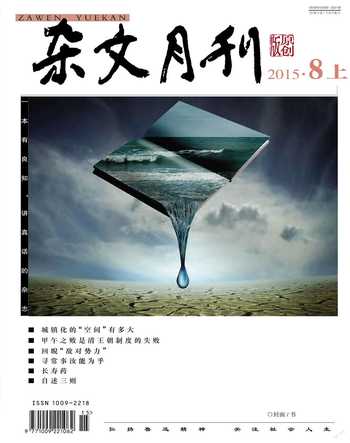我的吃公簡史
夫林
1973年夏,我被縣水產公司“要”去當筆桿子兼“水產養殖技術員”。很快就有了平生第一次公款吃喝,是“吃空餉”。一場洪水把我所在的黑龍江穆棱縣的穆棱河堤沖垮,各單位都分配到了加固河堤的任務。公司經理親自帶領30名壯勞力去義務勞動。中飯就在工地吃,后勤送來了豬肉燉粉條、魚罐頭、火腿腸、榨菜、饅頭,管夠吃,還有白酒、啤酒。錢從哪來?后來得知,修河堤算出差,出勤30人卻按公司全員138人報銷的伙食補貼。吃公的感覺真好!自己不花一分錢而能大快朵頤,不僅沒有絲毫奢費的自責,還油然生發出一點身份上的得意,我不是原來的我了。
從此一路吃下去,方式五花八門。
靠水吃水。公司下屬的漁場在郊區,為防偷魚,晚上安排4個人值班。我和漁場葉場長輪流帶班(實際上我倆每晚都一起去)。半夜腹饑,就撒網打上來十幾斤肥魚,燉一大鍋當飯吃,白酒是“勞保用品”(下水驅寒用),隨便喝。
吃床腿。那時動不動就召開水產工作會議(兼有技術培訓內容)。我是水產技術員,逢會必參加。會議伙食,中餐和晚餐都是宴會標準,一桌8人10大盤菜1盆湯,非常豐盛。晚餐有酒。第一頓因為肚子空基本把菜吃光,吃到后來,胃里積攢了油水,一桌菜要剩一多半。后來上面要求實行四菜一湯,但對策多得是,一般是四菜隨吃隨添。錢從哪出?床腿。組織會議的單位統一與旅館結算住宿費,再給與會人員開住宿發票,比如原本30元就開60元,多出來的錢用于吃喝綽綽有余。我們管這叫“吃床腿”。
吃包伙。1978年我被局里調去當秘書科長。局里經常安排干部下基層調研或蹲點,下基層干部把出差補助全數交給基層單位,由他們安排伙食。我們管這叫“吃包伙”。基層怕“灶王爺”的嘴“上天言壞事”,比賽著提高伙食標準,豈止雞鴨魚肉,山珍海味也上。基層領導也樂得陪吃。錢從哪出,沒問過,查問起來反倒尷尬。
吃交流。局與局之間會時不時地相互參觀學習,交流經驗。好吃好喝之余,還招待看戲看電影。不知對方是怎樣核銷費用的,我這個秘書科長走的是“辦公經費”或“維修費”科目。后來我們局自己辦了帶飯店的招待所,吃喝費就從利潤指標中沖減。
吃商品損耗。1986年我被下派到有190多名職工的果品公司任總經理。總經理其實是個“小媳婦”,上面有十幾個管我的“婆婆”,工商、稅務、銀行、物價、審計、公安(防火防盜)、計生、工會、電業、給水、環保、鐵路運輸等,都會不定期地來公司“檢查指導工作”或“征求意見”。都得罪不起,都得“看人下菜碟兒”,按不同規格好好“接待”,否則就會有這樣或那樣的“麻煩”。生意上的客戶是“上帝”,更得招待好籠絡好。那時財務費用科目里沒有“招待費”子目,我一般是用“商品損耗”來“核銷”招待費,就是銷售收入不入賬,出現的商品窟窿用商品損耗抹平。
吃百分比。后來有了明文規定,“企業招待費可按總銷額的3‰核銷”,這樣,我一年可以合法地花銷三四萬元的招待費。如果超支,虛做一筆總銷額在財務上不是難事。
吃回請。我做經理10年,每年都回訪有業務往來的客商,除新疆、西藏、內蒙古外,其他省市我都去過。對方的招待令我汗顏,我那兒的招待連他們的小吃都不如。八大菜系的菜都吃過,還在江蘇揚中縣冒死吃過河豚,在廣州吃過蛇,在湖南津市吃過團魚(一種河龜)席,在重慶吃過火鍋。
我一生最高只做到正科級,屬于官之末,吃公卻幫我享受到了“超級”的口福。
1995年我55歲,辭職自己開公司,也就結束了長達22年的吃公史。這之后,據說吃公有了新發展,詳情不得而知,未便亂下雌黃。幫我打理公司的大兒子與我一同陪吃。陪了沒幾頓,兒子就不準我參加了,說我表情“僵硬”。吃公就像吃唐僧肉,自然笑逐顏開,吃私卻像剜心頭肉,內里痛,表情上一不留神就“原形畢露”了。
這種精神負擔終于被卸載,從整治“四風”以來,我們就算用八抬大轎去請,“婆婆”也是不會來端我們的飯碗的。我市凡靠公款吃喝賺大錢的豪華大酒店都已關門歇業。
吃公史很值得寫,從一個側面,它能畫出一段向好的歷史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