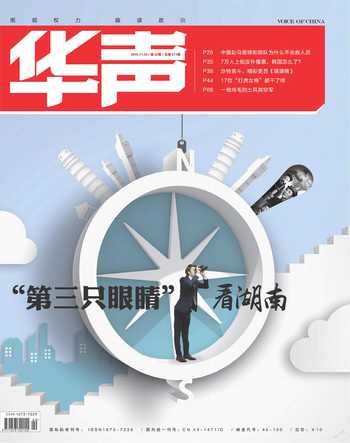裴士鋒筆下的譚嗣同
冷眉
郭嵩燾晚年在長沙期間,有位也屬于行動派學者的知己,但此人的目標和動機卻與郭嵩燾背道而馳,此人名叫周漢。周漢雖支持者甚多,但并非所有年輕一輩的湖南人都傾向于支持周漢。
來自長沙東邊瀏陽的年輕學者譚嗣同,痛惡周漢一如洋人。譚嗣同知道郭嵩燾欲重整湖南人心風俗之事,且支持郭的志業,他甚至把郭嵩燾與曾紀澤譽為有可能喚醒他們特別落后省民的僅有的兩位湖南人。譚嗣同對郭嵩燾的敬佩,在他早年受教育時就植下,他的三個主要老師碰巧都是郭嵩燾重振船山學的擁護者。
譚嗣同的三位恩師歐陽中鵠、劉人熙、涂啟先讓他大略了解了王夫之學問的重要,他則將這些教誨融合為博雜的學問,其中既反映了他本人游歷各地的閱歷,也反映了十九世紀晚期中國通商口岸匯集的多樣的外來影響。青春時期,譚嗣同隨升官的父親足跡遍及中國各地,他涉獵佛家、道家、詩歌、今文經學和西方科學著作,但對他影響最深者,還是王夫之。
在省外生活多年,譚嗣同已如同自英返鄉后的郭嵩燾,和湖南鄉親有了隔閡。兩人都敞開心胸接受在湖南罕有人聽聞的外國思想,但他們并不是同一代人,因而譚嗣同對湖南敵視洋人心態的厭惡,使他推斷(這是郭嵩燾所極力避免的)湖南的排外完全得歸咎于湘軍和其諸位領袖。譚嗣同表示,湘軍不該只為湖南人的仇洋心態負責,還該為全中國的仇洋心態負責,“獨湘軍既興,天地始從而痛之(洋人)”。譚嗣同不只和郭嵩燾一樣認為湖南人是中國境內最粗魯、最壞、最頑固之人,還把整個中國的排外現象全歸咎于他們。
據譚嗣同的說法,湖南人排外心態的反轉點出現于一八九四到一八九五年,那場以中國慘敗收場的中日甲午戰爭。甲午戰敗,嚴重打擊了中國各地文人,但譚嗣同在此中找到了對湖南前途的可能沖擊,其他地方的文人皆暢談清朝這場慘敗給予中國的教訓,對譚嗣同來說,這慘敗是預料之中的必然結果。在譚嗣同看來,這也是中國挫敗中的一線曙光,中國敗于甲午之戰,預示了守舊自大心態的終結,長久以來,這始終是湖南改革的最大阻力。
甲午戰爭之后,譚嗣同把王夫之“征諸實事”的做學問精神和在“萬無可為之時”承擔責任的精神視為在湖南師徒相承的一個傳統,譚嗣同認為,身為湖南人,他和他的恩師都肩負延續王夫之生命與著作的使命。
譚嗣同回瀏陽時,湖南已在大變之中。這個時候官紳在湖南展開迅速的制度變革和工業發展,但把文教方面的變革交給較年輕的本省學者掌舵。這些學者以譚嗣同和其同鄉好友唐才常為首。譚游歷多省期間,唐才常是唯一帶給他慰藉的人士,兩人結為至交。
一八九五年譚嗣同搬回瀏陽,唐、譚兩人重聚,并合力創辦瀏陽算學社。兩人以此為起點,在新學政江標的鼓勵下,促成以學習西方思想為宗旨的學會在省內各地與日俱增。那些經營有成的較大型學會,在較偏遠地區設立分會,整個維新運動紅紅火火,引起了上海報紙的注意,稱湖南這些學會如雨后春筍般興起。在這股突然想把西方思想、科學、西式改革弄明白的氛圍中,江標從上海引進湖南第一家鉛字印刷廠,在校經書院的校園里創立了湖南第一份報紙。他請唐才常和何來保擔任首批主筆,不久譚嗣同也加入主筆群。他們推出兩份刊物,先是旬刊《湘學報》,繼而是日報《湘報》。
王先謙于一八九七年奏請陳寶箴巡撫開設結合中西學科的全新學校。唐才常、譚嗣同、陳三立與他一同規劃新課程,大體上剔除傳統書院科考取向的經籍課程,并取名為時務學堂。
時務學堂諸創辦人聘請了一位非湘籍人士擔任此校的中文總教習,即廣東政論家梁啟超。時務學堂匯聚各路英才,由梁啟超介紹來自沿海地區最新改革派思潮,譚嗣同和唐才常則投注于湖南本地思潮。
湖南維新運動期間流通的理念,借《湘報》的“問答”專欄得到充分體現。不到十年前湖南省還是保守心態當道,而這一專欄所談的主題格外令人吃驚,而主筆的回復則大部分出自譚嗣同之手。身為主筆,譚嗣同和唐才常深知大眾傳播媒體在打造共同體團結意識上的潛力。譚嗣同在為《湘報》寫的序中強調湖南維新運動在中國絕無僅有,從而表示湖南人有獨一無二的能力帶領中國邁入現代國家之林。在湖南維新運動的論述中,“中國”之未來與“湖南”之未來兩者的區別是不分明的,譚嗣同在這篇序的末尾寫道:吾見《湘報》之出,敢以為湘民慶,曰諸君復何憂乎?國有口矣。這間接表示湖南人的心聲就是中國的心聲。
湖南維新運動作為具自我意識的省復興運動,其巔峰隨著一八九八年初期譚嗣同和受敬重的學者皮錫瑞創立南學會而到來。湖南不久前還被視為守舊排外心態的大本營,這時已改頭換面,致使梁啟超覺得那是唯一能讓來自中國其他地方的改革者盡情一展所長的地方。一如湖南的工業改革乃是為了使該省經濟得以自給自足,維新運動的知識層面改革最終也聚焦于湖南如何才能在政治領域也取得自主的問題上。誠如梁啟超在長沙與譚嗣同一起奮斗時所解釋的。“專以……完成地方自治政體為主義。”這一計劃并非只有學者或士紳知情,因為譚嗣同和梁啟超把此計劃當作翔實的政策建議呈給巡撫陳寶箴。
譚嗣同將王夫之譽為湖南改革的先驅,而當湖南維新運動的政治發展軌跡偏向本土自治時,他也在王夫之的著作里找到支持民主的理論依據。唐才常把譚嗣同對王夫之民主思想的詮釋帶進了時務學堂的教室里。拜譚嗣同之賜,學生們首度讀到了王夫之原就希望讓人一讀的論滿人之著作。譚嗣同和梁啟超把王夫之的著作當小冊子在學校里散發,學生們則熱切地拜讀。因此,老一輩湘軍和新一代湖南學生把他們大相徑庭的意識形態都溯自同一湖南先賢,即王夫之。
一八九五年五月,王先謙的一名門生無意中拿到時務學堂學生的部分札記,送給王先謙看。王先謙大為震驚,他立即呈請巡撫陳寶箴解散該校,辭退該校老師。但對長沙時務學堂的強烈抗議聲,不久就被北京情勢的重大轉折淹沒。年輕的光緒帝首度抗拒其姨母慈禧太后的懿旨,下令變法革新。一八九八年六月,他把幾位改革派大將召來京師,包括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并安插譚嗣同入軍機處任職。
但這場后來人稱“百日維新”的運動不到兩個星期就戛然而止。譚嗣同于九月二十四日在北京被捕,四天后,他遭到斬首。
譚嗣同遭處決僅三個月,梁啟超在日本出版譚的《仁學》,并在序中寫道譚嗣同是“中國為國流血第一烈士”。這一歷史定位將永遠跟著他,他將以中國民族主義第一位烈士之名永遠銘記于后人心中。
譚嗣同深信只有讓人民可以參與的國家,才值得為其死節。譚嗣同通過他在《湘報》的主筆工作,試圖實現建立參與型民主國家的理想。譚嗣同的死代表了湖南改革的一個轉折點,此后,那些自認為“湖南精神”之化身者,大部分將揚棄郭嵩燾和譚嗣同開啟的本土草根改革策略,轉而采用更為激烈的變革之道。于是,譚嗣同捐軀后不到兩年,唐才常返鄉——不是為了創立學會,而是創立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