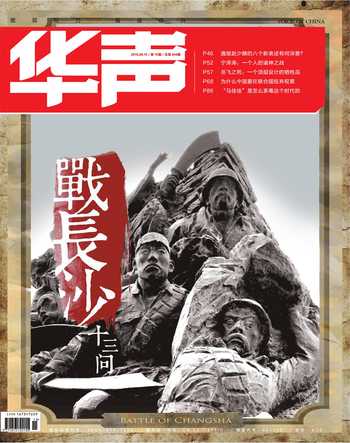“馬佳佳”是怎么荼毒這個時代的
呂崢
何勇是我小時候最崇拜的音樂人,如果有喜歡搖滾的可能會知道這個人,“魔巖三杰”之一。為什么要提他呢?因為我感覺在我的有生之年,可能再也聽不到像他的《垃圾場》,還有《姑娘漂亮》這么純粹的吶喊以及這么清澈的眼睛,因為我們這個時代已經變了,因為我們這個時代崇拜的是另外一類人,譬如馬佳佳。
我們這個時代像馬佳佳這樣的布道者還有很多,他們的商業模式基本上就是靠一張嘴,很多人還自以為在啟蒙這個時代,但我覺得所謂的啟蒙,應該是讓人擺脫現實的奴役,而不是讓人去適應現實。
而反觀馬佳佳,我們可以看到她不斷強調自己同50后和60后之間的一些區別,但是在我看來,她強調的那些所謂資源置換的一些理論,就是怎么去跟這些有資源的人去做交換,其實只是傳統政商關系的另外一種表述方式。
話題又說回來,其實逐利是沒有什么錯誤的,我今天要講的“知行合一”,它的提出者王陽明,是在傳統的重農抑商的古代中國,第一個給商人題寫墓志銘的大儒。但是我想說的是,對這個世界的態度只有索取的那一類人,請尊重一下另外一種立場和態度,那就是我對這個世界的態度:只是體驗,只是經歷。我對這個世界不做任何改變,既不把它變得壞,也不把它變得我自認為好的。
關于現代人的痛苦,有一句箴言:人的痛苦本質上是源于欲望大于能力,讀書太少而想得太多。而在古希臘,人們的生活目標是追求人的完美,但是到了今天,現代人則一味“追求物的完美”,甚至把自己變成了物,把生命別變成了財物的附屬,于是“存在”就被“占有”所支配。說到底,你占有了物,失去的卻是自己,故存在主義說,“擁有就是被擁有”。
去年有一本書叫《信息簡史》,這本書我認為最有價值的部分就是定義了所謂信息疲勞。什么叫信息疲勞呢?作者給出的解釋是“因為暴露在過量的信息當中,而導致的漠然、冷淡或心力交瘁,尤其指由于試圖從媒體、互聯網或工作中吸收過量信息而引致的壓力”。
信息其實不是智慧。在互聯網時代,我認為能夠看到事物的不同,其實就是很重要的能力,譬如喬布斯,我們知道蘋果打敗了一個最大的手機廠商是諾基亞,其實我們不要小看諾基亞,諾基亞是在蘋果出來之前,所有的手機廠商里面對用戶體驗研究最深的一家。
但是蘋果出來以后,喬布斯就說:我就一個iphone。惟精惟一,它把一件東西做到極致,做到簡約,做到極限,所以打敗了一個做了那么多手機的諾基亞。
這個就像一個人的目光。人的目光總是朝著外界的,對自身的了解反而很少,囿于三千世界的假象之中。有鑒于此,王陽明提出的最重要的觀點就是讓人跳出意識的層面,站在心體的層面來俯察意識。
我們今天經歷的從互聯網到移動互聯網的變遷,本質上是人的目光從關注外界到關注自身,關注內心這樣的一個轉變。電腦和你的距離在一尺開外,手機和你的距離是貼身攜帶。
這種物理距離的縮小,其實也是一種人的心理狀態的改變。那么在此背景下,所謂的互聯網思維,絕不是所謂用戶,簡約、極致、迭代思維,而是反身而誠,真實無妄不自欺。這真實無妄不自欺正是《中庸》的核心思想。
如果說互聯網推崇的是分享和免費,那移動互聯網的價值就在于內容和體驗。越是了然于心,越是了然于人,因為天人合一,人同此心,構成你我以及構成這些桌椅板凳的微觀粒子都是原子,那你把它分到無限細的時候,所有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佛把人的心境分為大我、真我、名我和身我四個層面,也就是告訴大家,只有站在更高的層面,才能看清較低層面的事,然后理解,知心然后用心。由此可見,在心力上用功越多,外在事功的增長空間也就越大,最后不是你跟著用戶跑,而是用戶跟著你跑。
產品經理是這個時代最熱門的職位,產品經理往往最了解用戶需求,需求的背后其實是人性。我再講一個關于亞馬遜創始人貝索斯的故事。
貝索斯小時候經常在寒暑假去爺爺奶奶家玩,爺爺奶奶在加州參加了一個房車俱樂部,經常很多人組成車隊到處旅行。有一次貝索斯隨隊旅行,爺爺開車,奶奶在副駕駛上吸煙。貝索斯看著吸煙的奶奶,突然想到一個戒煙的公益廣告,內容是說如果你每多長時間抽一口煙,人生將被縮短多少年。貝索斯窮極無聊,開始計算奶奶的抽煙頻率和折壽年數。他花了一些時間計算,算完之后很興奮,脫口而出:奶奶我算出來一個數字,如果你繼續再這樣抽煙的話,你會少活9年。
爺爺聽完貝索斯的“高見”后,把車停了下來,讓貝索斯下車。爺爺很嚴肅地對他說了一句話:杰夫(貝索斯的昵稱)慢慢你就會明白,其實善良比聰明更重要。
善良比聰明更重要,也更直抵快樂的本質。這種由人格完善帶來的快樂其實是由內而外,自然生發的。它本自具足,基本不需要外界條件的支持,被王陽明稱作“真樂”。就像斯賓諾莎所言:“快樂不是對美德的獎賞,而是美德本身。”光明也并不直接懲罰不接受它的人。但是拒絕光明,停留在黑暗之中,這本身就是一種懲罰。
社會學家馬斯洛,把人的需求像金字塔一樣分為幾個層次,他通過研究發現,那些自我實現的成功人士身上都有一個共同而顯著的特點,即打破了二元對立和“非此即彼”的慣性思維,能夠把游離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事物整合進一個統一體。而這個,其實就是王陽明口中的“萬物一體”。
回到我們今天演講的主題:知行合一是檢驗互聯網思維的唯一標準。不知道為什么,每次我一想到馬佳佳,腦海中就浮現出梁武帝蕭衍的故事:蕭衍這個人當時非常崇拜佛學的皇帝,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這四百八十寺很多就是在梁武帝手中修建的。梁武帝他精研佛理,甚至親自登壇講經,還動不動就跑到寺廟剃度出家,自以為功德無量。
有一次,達摩祖師經過他的領土,他自以為功德無量,就夸示于達摩。孰知只換來達摩一句:“并無功德。”蕭衍很震驚,問怎樣才算功德?達摩說既凈化自我,又凈化他人。這種度己度人的功德,不是靠世俗的有為來求得的。
回到互聯網,互聯網不是工具,也不是思維,而是溶于你行走坐臥、待人接物的行事準則和價值信仰,它是對自由的向往、平等的熱望,是對人類苦難不可遏制的同情。一切真理都在你心中,不假外求,所有的學問和學說,如果沒有經過和它同樣的體驗,沒有自得于心的話,對你來說就毫無價值。
不用去傾聽外界的那些所謂的專家、學者,更不用去傾聽馬佳佳說了什么,一切都在你心中,天理就在你心中。因此一切學問與人生哲理,都要自得于心,否則一文不值。
(本文系作者在新浪網“知行”欄目的演講,作者系《互聯網周刊》主筆,硅谷動力首席企業文化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