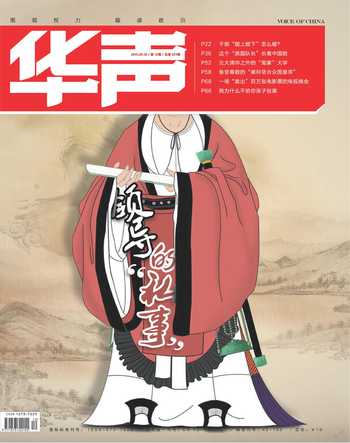沖動釀就的漢武西征
蓮悅
西漢武帝太初二年(前103年),一支數萬人的遠征軍艱難地跋涉在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的北緣。他們饑腸轆轆、缺水缺糧,忍受著天空的烈日和腳下的大漠流沙。與此同時,他們還需時刻提防匈奴鐵騎的騷擾襲擊。
這支部隊的目的地是遠在西域之西的大宛國。大宛國的地理位置在今天中亞地區烏茲別克斯坦費爾干納盆地,距離當時西漢王朝的首都長安足有萬里之遙。中間還隔著羅布泊、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和帕米爾高原。在兩千多年前的交通條件下,數萬人西征,注定是極其艱難的過程。西漢王朝之所以做出西征的決定,卻是源于漢武帝的一個夢。
話說漢武帝曾夢見“天馬”西來,于是,派人四處尋找夢中的“天馬”。西漢王朝自公元前121年由驃騎將軍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之后,便與西域諸國聯系頻繁,外交使團和商隊不斷深入西域和更西邊的國家。知道皇帝渴望良馬,從大宛國歸來的使節告訴皇帝,大宛國盛產一種特別優秀的馬匹,汗出如血,每日能奔行千里。
漢武帝聞言,自然心動。于是,派遣以車令為首的外交使團,帶著黃金二十萬兩以及一匹用黃金鑄成的金馬,前往大宛,以期換取汗血寶馬。
漢武帝此舉,無疑極具戰略眼光。
西漢王朝自建國之初,便時刻面臨著北方強大匈奴汗國的威脅。對于以農耕為主的漢王朝而言,要戰勝北方以游牧為主的草原民族,僅僅有更為先進的武器裝備和高素質的兵卒還不夠,馬匹才是決定勝負的關鍵。步卒即便數十萬之多,也往往難敵數萬騎兵的沖殺。
建國甫畢的西漢王朝軍馬曾極度匱乏。漢高祖劉邦在白登被匈奴騎兵圍困,差點因之喪命時,全國的戰馬僅數千匹。
為應對匈奴,文帝、景帝時代極為重視馬政,在西北邊郡大興馬苑,招募烏孫人、羌人等擅長養馬者為漢軍蓄養軍馬。文帝時頒行《馬復令》,民間飼養一匹軍馬可免三人徭役,以此鼓勵民間養馬。景帝時西北邊郡的馬苑共有三十六所,養馬三十萬匹。到漢武帝時代,漢王朝一度擁有甲兵四十五萬,軍馬六十萬匹。
公元前119年,漢匈兩國決戰漠北,西漢王朝僅此一役便損失了十余萬匹戰馬,很難再組織起大規模的北伐匈奴的戰役。所以,漢武帝對好馬、“天馬”的追求,無疑對西漢軍隊的長遠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
然而,車令帶到大宛國的黃金和金馬并未打動大宛國王和貴族。他們雖然畏懼漢王朝的強大,卻仗著兩國之間萬里之遙,更兼路途艱險,認定西漢王朝拿自己沒折,所以,拒絕交換自己視若珍寶的汗血馬。
這原本完全可以通過進一步的外交斡旋、利益疏通來解決問題。然而,漢使車令卻在大宛國的朝堂上做出了令人瞠目結舌的極不理智的行為。他竟然對大宛王破口大罵,并用鐵錘擊碎了帶去的金馬,然后揚長而去。
車令為何會如此失態?史書中找不到明確的答案。車令的言行,完全不像一個大國使節,倒更像“憤青”。
“憤青”雖然是現代網絡詞匯,但在歷史中,這樣的人如恒河沙數,活躍在每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這大抵是一群嚴重缺乏理性思維能力的人,言行不計后果,只受控于個體私利,或者簡單地為自身喜惡所驅動。這樣的人表現出來的往往是壯懷激烈,卻空有一腔雞血,成事不足,敗事倒有余。
根據司馬遷的記載,自西漢王朝聯通西域之后,漢武帝向西域諸國派遣了許許多多的使團,使節的素質卻是參差不齊。漢武帝自身偏好于任用那些巧言令色的浮夸之輩。再加上當時前往西域,路途艱險,往往需要冒著生命危險。所以,愿意出使之人,大多是些家境貧寒的亡命之徒。他們鋌而走險,無非是希望能效法博望侯張騫晉爵封侯,甚至單純地只是將政府交托給他們的國禮偷入私囊,從中漁利而已。
而在西域那些少則幾千,大則幾萬人的國家,不少漢使仗著西漢王朝的雄厚國力和龐大體量,行為乖張、飛揚跋扈,制造了無數的摩擦和矛盾。為此,西域諸國對西漢使節采取了諸多抵制行動,拒絕為他們提供飲食,甚至對使團進行劫掠。為保護使團,西漢王朝還專門派騎兵掃蕩西域,炫耀軍威,震懾各國。
因為車令不理智的行為,受到侮辱的大宛王下令截殺漢使,不僅將二十萬兩黃金和使團所攜帶的財物全部奪取,更誅殺了使團的所有成員。西漢使團被全部誅殺,這是漢武帝外交史上的第一次。漢武帝自然將其視為無法忍受的奇恥大辱。他選擇了用武力解決問題。
汗血寶馬,這原本應該只是一單互惠互利的國際貿易,充其量演化成一場外交斡旋,與戰爭根本風馬牛不相及。可是現在,西漢王朝和整個西域都將為之血流成河。于是,有了我們開篇那支龐大部隊的遠征。
誰也想不到,這支遠征軍的命運會如此悲慘。
西域諸國原本都是些大漠戈壁中依靠綠洲湖泊而繁榮的小國。這些綠洲和湖泊的承載能力極為有限,所以,這些國家的生存環境都很脆弱。現在數萬人的大軍過境,提出龐大的水和糧的要求,很多國家根本無力滿足。
于是,數萬人的軍隊一路渴死、餓死、病死、戰死不計其數,抵達大宛國時僅剩幾千個衣衫襤褸、饑腸轆轆的殘兵。這樣的軍隊自然無法攻城克敵,于是返回漢邊,一路又是死傷無數,只有幾百人活著抵達敦煌郡。
漢武帝卻不甘心,第二年組織起更為龐大的部隊再度西征。經過一年的艱難跋涉和征戰,到公元前101年,西征大軍攻陷大宛國,誅殺大宛王返回長安時,僅剩下一萬余人,為皇帝帶回了一千余匹汗血寶馬。
“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感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這就是漢武帝見到四蹄生風、日行千里的汗血寶馬后龍顏大悅,所作的《西極天馬歌》。經過兩次西征,大漢軍威威震整個西域。大軍主帥、貳師將軍李廣利也一戰成名,受封海西侯,更成為漢武帝晚年討伐匈奴最為倚重的將領。
只是,可憐兩次西征,歷時四年,十萬漢家兒郎,萬里黃沙、千里鹽澤、流沙無數、草木不生,連把枯骨都帶不回故園。
用十萬人的性命換一千匹馬,合不合算?我相信,很多人會認為,汗血寶馬可以改良中原王朝的馬種,讓中原王朝在往后和北方草原民族的交鋒中更有優勢,這是個利國利民,造福千秋萬代的好事。所以,犧牲再多的人都是值得的。
不過,這一千匹汗血寶馬果真改良了中原王朝的馬種了嗎?我不是動物學家,沒看過相關的研究報告,而史書在這方面也沒有明確的記載。但從以后中國兩千年的歷史不難看出,歷朝歷代,在面對北方草原民族的威脅時,因為戰馬質量、數量上的劣勢而導致騎兵部隊的弱勢一直是中原王朝沒能解決的問題。
事實上,漢武帝發動的汗血馬戰爭,是用整個王朝在為一個外交使節不理智的荒唐行為買單,為自己的顏面買單。那些帶著皇帝賞賜給各國君主厚禮的漢使們出使的目的只是取悅皇帝和為自己謀取私利,并未意識到外交的目的是和平而非戰爭。
當這些漢使們依仗著王朝的強大國力,蔑視周邊小國,甚至心存“漢匈之間不妨一戰,奪取汗血馬不排除戰爭手段”諸如此類的思維時,必然將國家導向戰爭,讓人民生靈涂炭。
十萬漢軍將士的性命便是西漢王朝為這種思維付出的代價。當然,在人命如草芥的集權社會里,為博龍顏一悅,十萬人、百萬人、千萬人枯骨又算得了什么呢?
摘編自共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