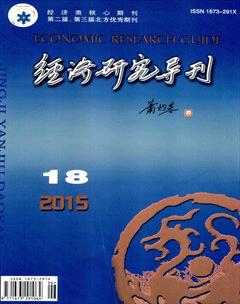論國際海上核污染責任體系的構建
李樸原
(上海大學法學院,上海 200444)
福島核災難才剛過四周年,美國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近日發出的消息指出,在加拿大溫哥華海預測到來自日本福島的輻射,海水樣本中含有微量的銫-134和銫-137,這不禁讓人們再次回想到2011年福島核電站核泄漏所造成的嚴重核污染問題。從國際法的角度上說,福島核電站污染事故涉及國際環境法中的危險物質和活動所造成的污染和損害問題。
作為三大類危險物質之一的核能,若利用和管理得好,可為人類帶來巨大福利;若利用和管理不當,就會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災難。因此,如何對核能妥善加以利用和管理是各國政府面臨的共同問題。
一、國際民用核能法律制度存在缺陷
當今有關核污染的國際法律制度主要關注的是海洋環境污染的民事責任,二者都不涉及對公海污染的賠償問題。所以,迄今世界上還沒有一部專門針對海洋核污染問題的國際公約,更不會專門考慮自然災害等誘發因素。雖然國際原子能機構曾主持簽訂過有關核事故的相關條約,但在日本核危機過程中,國際原子能機構在阻止事態的惡化方面并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而且現有的有關核能的國際法律制度也存在種種缺陷:其一,強制性不足。目前世界上并沒有真正為確保核安全建立一個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國際制度。其二,不夠具體。例如1986年核事故及《早通報公約》規定由各國來解釋什么是“重大影響”,并無統一規定。其三,監督力度不夠。現有的體制下,對公約成員履行義務執行情況的監督主要是依靠自我監督有關國家的國家報告書。
上述缺陷集中體現了民用核能領域里的國際法律制度與國家主權之間的一種緊張關系,這種緊張關系在福島核電站事故中尤其凸顯。
二、國際海上核污染法律責任體系存在缺陷
國際海上核污染的環境責任分為國家責任和國家賠償責任。
國家責任是指國際法主體對其國際不當行為或損害行為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國際不當行為必須具備兩個要件:一是一國的某一行為可歸因于國家而構成該國的國家行為;二是該行為違背了國際義務,包括兩類行為:其一是違反核裁軍和核不擴散義務的不法行為,其二是違反核能和平利用義務的不法行為。
國家賠償責任,是指國際法主體對其從事國際法不加禁止的活動所產生的損害后果所應承擔的國際責任,損害責任并非由違反國際義務的非法行為所引起,不是一種過錯責任,它是伴隨著國家在民用核能、石油運輸、航天航空等現代科技條件下的經濟活動而出現的。
理論上,只要這些活動對地球表面的人員、財產和環境造成損害,無論行為國是否存在過失,都應承擔賠償責任。實踐中,國際法上不加禁止活動的國際責任尚無一套成熟的制度,充其量只引起補償義務,不導致國家責任。由于對國家責任沒有一個國際性的體制,國際社會對核損害所產生的責任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民事責任。
國家責任的要件一般包括行為、損害、行為和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某一造成環境污染的行為,可能同時引發國家責任、民事責任。由于環境損害是個新問題,各國關于損害賠償的法律規則并不相同,這將造成受害者的差別待遇。為了協調責任規則,便利受害者追償,國際社會在一些領域發展出民事責任規則,體現在締結的一系列國際條約中,如1960年《核能領域第三方責任公約》(《巴黎公約》)等,這些條約對核事故的民事賠償責任都作了明確規定,通常由核設施或核動力船舶的經營人承擔賠償責任,但是戰爭、自然災害和受害方過失可以作為經營人免責的理由。
三、完善國際海上核污染法律制度的政策構想
鑒于現有的國際環境法律制度無力對海上核污染問題進行專門規制,制定一部專門的國際海洋核污染公約不僅非常重要,而且十分迫切。日本海上核泄漏事故對國際環境法里的傳統國家主權理論構成了沖擊和挑戰,主權內涵需要重新界定的時候到了。
完善國際海上核污染法律制度需要考慮的因素很多,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解決:
1.通過制定一系列國際安全強制標準和具體規定,約束各國主權,以及明確和強化締約方責任來增加公約的可操作性,從而構建一個強有力的國際法體制。
2.在公約中尤其應對成員國防止核污染的預防義務加以嚴格要求,因為污染后的補救總是無法徹底復原。不僅如此,履行預防義務更有必要性,因為人們對危險活動的運行、所用的材料以及管理這些活動及其所產生的風險的知識在不斷增長。關于成員國的預防義務的公約要求,筆者認為應有以下幾個方面:
(1)事先核準。在公約范圍內,成員國不應未經允許即在其領土內從事含有核泄漏風險的活動。因此,事先核準是預防原則的重要部分,只有經過成員國集體同意的活動,才能被允許進行,這從源頭上減少了風險的發生。
(2)風險評估。在事先核準階段是否核準某項活動,應根據該項活動可能造成的跨界損害的評估,包括任何環境影響評估。聯合國的一項研究指出,環境影響評估已經顯示出執行和加強可持續發展的價值,因為它結合了風險預防原則和防止環境損害原則,也考慮到了公眾參與。
(3)通知、信息交流與磋商。如果上述風險評估的結果表明該活動有造成重大跨界損害的危險,進行該活動的國家應及時將該危險和評估通知可能受影響的國家,并應向其遞交評估工作所依據的現有技術和所有其他有關資料。
(4)貫徹不歧視原則。在事故發生之后的補救階段,事故發生國和其他受影響國都可以平等的地位參與其中,這特別適用于領土毗連的國家之間。
3.在建立一個統一的國際法律文件的同時,更是要成立區域性的核能組織,切實有效地對成員國運用核能進行監督和管理,并且對責任國核污染的處理進行督促,以免福島核泄漏事故后受影響國無法得到賠償的情況再次發生。目前區域性的核組織只有歐洲原子能機構和美洲核能委員會,在亞洲還缺少這樣一個區域性合作機構,如果能效仿歐洲建立“東亞原子能共同體”,不僅能促進東亞各國的核技術交流與合作,預防核污染的發生,還能在污染后及時劃清各國責任并督促賠償責任的落實。
在成立“東亞原子能共同體”后,應在組織內建立海上核污染的區域統一評估和強制合作制度。要求共同體內所有民用核能的使用國必須提供核安全中長期評估所需的一切技術資料和信息,而且在發生海上核污染事故時不得拒絕區域合作。
4.雙邊條約的建立對于完善國際海上核污染條約體系也有著重要的意義。例如,中法、中英的民用核電合作有著廣泛的前景,雙方在核電方面的合作程度日益加深,與之配套的雙邊條約對于雙方各自的責任劃分和利益保護有著關鍵的意義。所以,筆者認為凡是涉及到核能共同開發的項目,核能風險責任承擔的雙邊條約應該及時跟進,防止事故發生后產生互相推諉的局面。
5.在各國對賠償事宜難以達成一致時,可以奉行“專事專辦”的宗旨,搭建一個由各關系國共同組建的賠償委員會,由各國派代表參加,專門解決賠償問題。賠償委員會的設立,有利于各國之間的交流與協助,為爭議的解決提供便捷。
賠償委員會可以邀請國際知名的核能專家、法官、法學家和各國政府官員參加,綜合各方力量促成爭議的解決。
6.鑒于國際原子能機構的軟弱性,世貿組織在防止海上核污染方面賦予其更大的權力。畢竟國際原子能機構是下設的一個組織,雖然不是專門機構,但卻是國際性的平臺,相對于其他平臺而言,優勢是顯而易見的,讓其充分履行職能,協助各國發展核能、處理核事故,不失為一條可選之路。
四、結論
福島核泄漏事故不僅是災難,也是警鐘,在現有的國際法律制度框架下,國際環境法中所存在的問題充分暴露,這需要人們重新審視國際法律背景的缺陷,也更讓大家看到了建立一個公正、高效的責任體系的必要性。建立責任體系的核心莫過于各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只有各國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實現核能的安全利用和責任的合理劃分。
[1]王紫零.日本核污染事故的國際環境法思考[J].法治論叢,2011,(5).
[2]段小松.論國際海上核污染法律制度的完善——以日本海上核污染為例[J].經濟與法制,2011,(10).
[3]嚴旭銘,李錦崇.日本電視臺“復原”事故全程——解析福島厄運原因[N].中國青年報,2012-03-10.
[4]沈姝華.日本政府報告稱福島核事故處理過程充滿錯誤[EB/OL].中國新聞網,2011-12-27.
[5]日本福島核事故處理承包商被曝偽造低輻射量[EB/OL].中國新聞網:北京,2012-07-21.
[6]唐釗.國外污染轉移的法律規制及其啟示[J].湘潭大學學報,2011,(9).
[7]張相君.區域合作保護海洋環境法律制度研究[J].中國海洋大學學報,2011,(4).
[8]李建勛.區域海洋環境保護法律制度的特點及啟示[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1,(2).
[9]屈彩云.宏觀與微觀視角下的日本環境ODA研究及對中國的啟示[J].東北亞論壇,2013,(3).
[10]闞占文.跨界環境損害責任導論[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