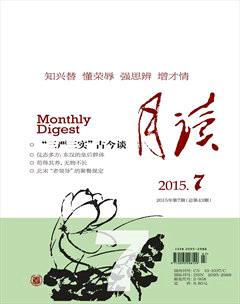儒學的意義和價值
編者按:莊士敦(1874—1938),英國蘇格蘭人,畢業于愛丁堡大學和牛津大學,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的外籍老師,是一位地道的“中國通”。本文選自莊士敦于1933年在布里斯托爾大學所作的題為《儒學與未來的中國》的演講。雖然時隔八十余年,其觀點和思想對當今人們認識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仍有借鑒和啟發意義。左為莊士敦著清朝服飾照片。
儒家思想一向樂于從其他思想體系中,比如佛教和道教中汲取營養。有時,人們在談到道教、佛教的一些思想融入儒家思想這件事的時候,似乎感覺很不光彩,好像儒學有剽竊的嫌疑。但事實卻是,道家學說與儒家正統學說具有很強的協調性,它能夠進入儒家思想并被后者吸收,本身就表明儒家思想具有高度同化和吸收其他思想的特質。就如同基督教有資格、有能力把新柏拉圖哲學納入自己的體系一樣,儒學也具有吸收其他思想體系中的優秀成分的資格和能力。可以確信的是,儒家思想如果想要在當今中國生存壯大,這種特權就必須保持和延續下去。
如果那些忠誠的儒學家們希望孔子繼續保有他坐了兩千多年的至圣先師寶座的話,那么他們就應該按照另一個完全不同的導師——卡爾·馬克思——教導其追隨者的話去做:“他們必須對儒學加以梳理,分清哪些內容已經僵死,不再適應今日的形勢;哪些內容仍然具有活力,仍然具有成長和適應現實的能力——而這是真正有生命力的事物才具有的特性。”
我堅持認為儒家思想就是這樣一種富有生命力的事物。對于儒學中是否真的存在已僵死的內容,我深表懷疑。但如果其中確實存在這樣的內容,就應當毫不猶豫地將其拋棄。
儒家思想完全有資格被稱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傳統”。這個詞是W.R.英奇博士在談到歐洲的基督教—亞里士多德—新柏拉圖傳統時所用的。
儒學是使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并使中國成為當今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國度之一的最主要因素,想否認這一點無疑是徒勞的。在上個世紀里,中國也曾沉淪落后,但是,僅僅把視野局限在中國那些災難時期,而無視漢、唐、宋時期的中國是何等輝煌,難道這樣是公平的嗎?為什么單單拿今天(編者按:指國民黨統治時期,下同)混亂、屈辱的中國作為標準來評判儒家思想,而不是以在17世紀得到文明但欠發達的歐洲國家熱情贊揚的安寧繁榮的中國為評價標準呢?誰敢迷信中國除非拋棄儒家思想,否則將永遠不會再恢復其往日卓立于世界的輝煌?
如果說儒家思想是邪惡的,不利于一個充滿活力的民族健康成長,那么為什么在很久以前,歐洲的現代國家尚未形成的時候,中國沒有被其毀滅掉呢?如果說儒家思想是一劑致命的毒藥,那我們又如何解釋當這劑毒藥用在中國身上時,其效果卻簡直像是一味益壽延年的靈丹妙
藥呢?
在那些戰栗著思考當今歐洲國家的悲慘境地,并對今天西方文明面臨的巨大威脅有所察覺的人當中,有許多人宣稱“基督教已經失敗了”。對于這樣的言論,人們自始至終回之以義憤的反駁:“基督教沒有失敗:它從來沒有接受過驗證。”但是,同樣是這些為基督教作辯護的人們,卻過于急切地斷言說“儒學已經失敗了”,還說今天中國的境況就是證明。那么這些人是不是準備說,儒學在中國受“驗證”的程度,要遠遠高于基督教在歐洲受“驗證”的程度呢?毫無疑問,如果每一個基督教徒都嚴格遵循基督教的教義,那么在信奉基督教的個人之間、國家之間都將充滿完美的和諧與善意,今天的西方世界也會處處充滿博愛。但我們同樣可以說,如果每一位所謂的儒家信徒都遵循儒家學說行事,中國在好多個世紀之前早已經會建立起“仁政”的偉大目標,并且實現“王道”的崇高理想了。基督教沒有失敗是因為它尚未經過檢驗,如果說這種說法是合理的,那么,這一說法也同樣適用于儒學,以及其他幾種引領誤入歧途的人性,并使精神得以升華的偉大宗教倫理體系。我記得尼采曾說過,世界上有且只有一個耶穌,就是那個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那世界上是不是有不止一個儒學家呢?我們也許有理由懷疑世上是否有過一個儒學家。其實,理論和現實之間往往存在巨大的鴻溝,不論是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還是在信奉儒家思想的東方,都是如此。
前不久,在歷史不長的一個大國里,一位當代的智者稱,盡管中國的官場臭名昭著,但是比起其他任何國家來,中國人的“道德觀念也許更為牢固,這一事實也可以解釋為什么中國具有如此長久的生命力”。他接著說到,中華文明的確帶有許多嚴重的缺陷,但“很有可能在這種文明中蘊涵著某種神秘的力量,只要中國人牢牢抓住他們的‘領航員——儒學傳統中的精華,就不必懼怕來自西方的壓力”。這段話充滿了智慧,值得那些輕易就想拋棄自己精神源泉的中國人深思。
幾年前,一位名人也曾經在這個講座中講過同樣充滿智慧的話。亨利·紐伯特爵士在他的演講的開頭這樣說:“作為一個偉大的國家,必然有自己的領土,這塊土地邊界清晰但卻廣闊,經過長久的占有和耕耘,具有進一步開發和增產的潛力。這樣的國家可以安享自己的精神財富:作為其大眾生活之結晶的文化傳統,還有其獨特的文化成就的總和。……如果喪失掉自己的傳統,毀滅掉自己的文化,那就意味著其力量的衰退,最終可能會招致國家的崩潰。”他又補充說:“古希臘和古羅馬就是因為其傳統的消亡而衰亡的。”
亨利·紐伯特爵士演講的整個第一段,都值得我鄭重地推薦給那些傾向于低估儒學價值和意義的西方人還有中國人。雖然他的演講沒有涉及中國和儒學——他的演講主題是英國詩歌—— 但是,這絲毫無損其對中國人文化生活的針對性。
中國出現了一些蔑視嘲笑古老傳統的人(這并不僅僅是最近才出現的事情),這些人想要摧毀傳統的道德根基以及生活是一門藝術的古老觀念。《禮記》中有一篇有趣且恰當的篇章,題目叫“經解”,其中有一段如下:
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這段話雖寫于兩千多年以前,但是卻在過去二十年的中國得以應驗。
我們幸運地看到,儒學在現代中國的前景遠非毫無希望。不僅在散布各地的華人移民中間,而且在國家各地,有一些學者以及大量不以學者自詡的人們,他們都在守衛著那歷史悠久的火焰。W.R.英奇博士在談到新柏拉圖主義對基督教哲學的影響時,引用了一位新柏拉圖派弟子的一句話:普羅提諾的圣壇依舊溫暖。同樣,我們也可以說孔子的圣壇依舊溫暖。我認為我們還可以補充一句話,那就是:如果有朝一日孔子的圣壇變得不再溫暖,不僅對中國,而且對整個世界來說,那都是一個倒霉的日子。
(選自《儒學與近代中國》,天津人民出版社。標題為編者所擬)